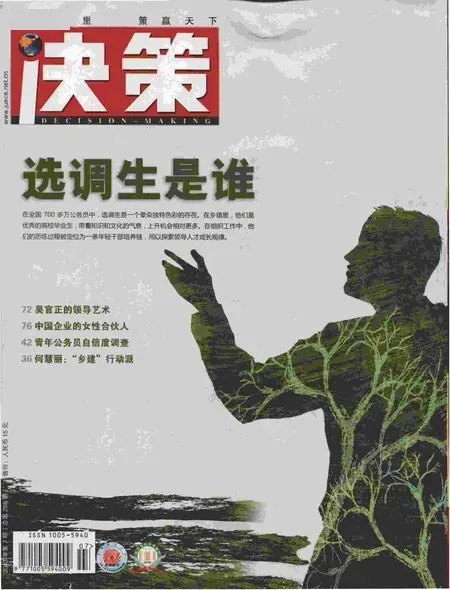“臨時工”魔咒求解
賀海峰
近來,在諸多公共事件中,“臨時工”頻頻被推向風口浪尖:“飛腿踏頭”的城管是臨時工,發飆砸人的警花也是臨時工;強拆民房的是臨時工,引發火災的也是臨時工……結果,臨時工往往被迅速辭退,相關領導卻仍屹然不倒。對此,臨時工自嘲為魔咒、宿命,輿論界則窮追猛打、質疑不斷。
是的,為什么總是臨時工?
長期以來,政府職能沒有轉變到位,公共管理事務有增無減。在機構改革、簡編定崗的大背景下,很多行政事業單位轉而聘用大量的臨時工。臨時工的艱辛勞動、重要貢獻自然不容否認,但也應當看到,由于制度設計上的先天缺陷,臨時工越來越被異化成為“替罪羊”。在部分官員的眼中,平時讓臨時工沖鋒陷陣,出事時祭出臨時工,成為了一種屢試不爽的“政治智慧”。
以延安城管暴力執法事件為例,被處理的最高領導只是監察支隊分管副支隊長,所謂的“處理”也只是停職待崗,市城管局領導層竟無一人站出來擔責。壞事是臨時工干的,都已經開除了,說明領導是重視的,臨時工的下場也很可憐,輿論又何必非要置人于死地?
如此“壁虎斷尾”之術,看似高明至極,既保全了自己的官位,又保全了職能部門的形象,實則嚴重透支了政府公信力,欠下了民眾的感情債、公平債,成為釀就更大矛盾的導火索。
從法理的角度看,臨時工不具有被授權或被委托實施行政執法權的資質和條件,不具有行政執法權。一旦在工作過程中造成損害,首先應當由其所在的行政機關承擔對應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行政機關擔責之后,方才進行內部追責。
不過,在實踐中,官員問責屢屢遭遇棘手難題。首先,“領導責任”到底應當如何界定?什么樣的事故可導致更高級別官員被問責?現有法律法規語焉不詳。在操作上,副職問責顯著多于正職問責,副職頂缸現象一點也不遜色于臨時工。但事實上,很多決策往往由“一把手”最終拍板。現代行政理論認為,有權必有責,權責要一致。何種情況只需分管副職官員辭職,何種情況主管正職官員也要辭職?至今仍無明文規定。
其次,潛規則仍時常興風作浪。比如,遼寧某縣委書記乘坐豪車,至少涉及兩大違規:一是車輛嚴重超標,二是套用警車牌照。事后,肇事官員回應,車輛是跟朋友借的,已經退還;軍牌是臨時工司機套用,司機已主動辭職。荒謬的是,監管部門居然默認結果,不再有問責下文。如此一來,臨時工豈止是被問責主體安排的卸責對象,更像是監管部門與被問責權力的公然合謀。而由于各種明規則與潛規則糾纏不清,對于地方陽奉陰違、違規提拔被問責官員等問題,甚至連中央部委也無可奈何。
顯然易見,非霹靂手段不足以服眾,也不足以震懾官員。在把權力關進籠子的過程中,必須切實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保障媒體、司法的相對獨立性。誰賦予臨時工行政執法權的?誰允許擅自聘用臨時工的?臨時工的工資福利從何而來?這些關鍵事實,都需要來自行政體系之外的獨立調查。
而全面清理規范臨時工,也已迫在眉睫。我國究竟有多少臨時工?迄今,尚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由此,可管窺編外人員管理的混亂。可喜的是,今年3月,《廣東省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明確要求,嚴格落實行政執法人員資格管理制度,杜絕合同工、臨時工等無執法資格人員上崗執法。6月,南京市政府也專門發文,規定行政機關編外人員不得超出行政編制的10%;編外人員實行公開招聘;公安、城管等部門必須實行實名制管理。
從更長遠來看,還應當啟動一場更深層面的“編制革命”。有關部門不僅應對每一起臨時工事件進行徹查問責,還應花大力氣健全勞動用工制度。質而言之,就是在更大范圍內實施聘任制、合同制,從而徹底打碎在編人員的“鐵飯碗”,徹底破除在編人員的“貴族化”。惟其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形成競爭壓力,做到能者上、庸者讓,誰用工、誰擔責,下屬違法、領導問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