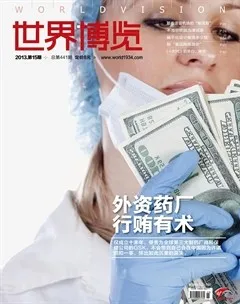如何形容美食?
(作者)(導(dǎo)語) 味道并不容易形容,古人提到美味,習(xí)慣說“妙”與“美”。
人的味覺與生俱來,老天爺最初的設(shè)計(jì)并不是要人品嘗美味,而是以資辨識采集的物品是否可食:有苦味的草根多不宜入口,甘甜的漿果顯然有益;再輔以嗅覺,可以辨別食物是否腐敗,飲食安全的第一道防衛(wèi)機(jī)制就是如此建立。
烹飪技術(shù)隨著文化開展而發(fā)達(dá),講究的是”具膳餐飯,適口充腸”,適口即可;過度講究美味,反而敗壞德行,甚至招來殺身之禍。齊桓公的御廚易牙煮了自己兒子讓齊桓公嘗嘗異味。管仲于是警告齊桓公:愛惜骨肉是人情之常,易牙能殺子以求寵,有何愛于君?齊桓公未納其言,親信易牙,終至招來大禍,身腐亦不得安葬。
古人活動范圍小,一輩子在家鄉(xiāng)過日子,除了逃難跑反,不會離鄉(xiāng)背井,所飲所食,大都代代相傳,各地也大同小異。桃花源記提到武陵漁人進(jìn)入山洞之中,發(fā)現(xiàn)一處新天地,當(dāng)?shù)厝穗m從秦代以后便遁居于此,與外界隔絕,卻仍是「男女衣著,悉如外人」,熱情款待誤入桃花源的不速之客。這雖是陶淵明的寓言,但也符合實(shí)情。近代以前,生活事物演變得速度緩慢,從秦末到東晉約五百年間,不僅衣著服裝依舊,食物也無差別,”設(shè)酒、殺雞、作食”多么自然,無須虛耗筆墨,多做描述。
的確,古人提到食物時(shí),多半只描述吃哪些東西,魯智深到了桃花村,太公給準(zhǔn)備了一只熟鵝,還有二、三十碗酒;劉唐專門拜訪宋江,轉(zhuǎn)交一百兩金子,宋江理應(yīng)請客,但也就是“大塊切一盤肉”加上菜蔬果子。古人不僅吃得簡單,肥鵝、雞鴨多半煮熟而已,也不說明味道如何,大概因?yàn)檫@些食材放諸四海皆準(zhǔn)。就連專講風(fēng)花雪月的《金瓶梅》也不特別說明食物的味道。第四回提到西門慶剛要勾搭潘金蓮,王婆居間,安排了肥鵝、燒鴨、熟肉、鮮鲊及細(xì)巧果子,笑笑生也認(rèn)定大家都知道這些食物的味道如何,不需要激發(fā)讀者的想象。
唐代以后,江南飲食中少不了“鲊”,將魚切片,用鹽及糟腌制,置入瓶罐中發(fā)酵,即可食用。宋代的蔡啟提到:“吳中做鲊,多就溪池中蓮葉包為之,后數(shù)日取食,比瓶中者氣味特妙”。這種巧思,就用“妙”來形容,足見古人形容食物味道的筆法相當(dāng)貧乏,這種情況不在少數(shù)。南宋浦江吳氏是烹飪專家,又能寫,她在《中饋錄》介紹腌鹽韭之法,說“腌一、二宿,翻數(shù)次,裝入瓷器內(nèi),用原鹵加香油少許,尤妙”;清代的朱彝尊講到自己制作糖姜的秘方是略加梅鹵,也是一個(gè)”妙”字總結(jié)。這妙字到底要形容怎樣的味道?還得各憑會心。
除了“妙”,另一個(gè)常用的形容詞是“美”。本草綱目形容獾肉“味甚甘美,啖之殺蛔蟲”;南宋的施宿在《會稽志》中提到“雞頭”,說“其柄可以為菹,甚美,芡實(shí)甘滑有佳味”。這兩個(gè)形食物味道的字,讀者難以意會,說了等于沒說。如果真有大家不清楚的味道,要如何描述?印象中,只有南朝梁劉峻(字孝標(biāo))的《送橘啟》形容味道時(shí),最為傳神。
劉峻生于五世紀(jì)中期,正逢亂世,年幼時(shí)便與家人失散,輾轉(zhuǎn)成了劉實(shí)的家仆。他努力好學(xué),頗有文名。后因北魏起兵,他又流落山西,在大同出家,并翻譯佛經(jīng),又注《世說新語》。劉孝標(biāo)學(xué)問好,書讀得多,說起味道,才能用各種方式形容。一回,他送幾個(gè)橘子給朋友,生怕別人不知道,還特別寫信說明:“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fēng)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脈不粘膚。食不留滓。甘逾萍實(shí)。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這位朋友大約住在長城以外,他特別問”氈鄉(xiāng)之果,寧有此耶?”其實(shí)這根本不是問句,就是瞧不起這些住帳棚的人,認(rèn)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橘子的味道,特別說明。
的確,味道并不容易形容,何況每個(gè)人的味覺發(fā)展不同,生理結(jié)構(gòu)不同,有人的味覺要比其他人敏銳,可以嘗出食材的差別,據(jù)說易牙就能將淄、澠之水的差異嘗出來。一般人想要以言語形容食物之精妙,斷非易事。現(xiàn)在泛濫的美食節(jié)目中,主持人動輒就是“彈牙”、口感和嚼勁”。這些形容,說了等于沒說。古人說“妙、美”,至少還有驚異之感,“口感不錯(cuò)”難道不能形容胡蘿卜或是脆黃瓜?橡皮筋不也挺有“嚼勁”,與好吃有啥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