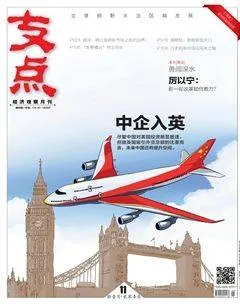“價稅財”聯動改革勢在必行
現在,雖然中國的一般商品市場化程度比較高,但資源品、基礎品的比價關系和價格嚴重扭曲。
從資源環境的制約來看,我國最基本的能源供給高度依賴進口,外向依存度高達60%。
中國油氣資源貧乏,讓我們不得不考慮如何更多地利用國內的煤炭資源。煤炭在能源供給中最集中的體現,就是提供了75%的火電的來源,而電力又在整個經濟社會運轉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生產生活能源供應最集中的體現。為了發電,我國基本的鐵路運輸運力有50%都在運煤,這個數值在用電高峰期可以達到80%。
然而,雖然電力資源如此寶貴,卻面臨著殘酷的現實:從生產者到消費者,誰也不把節電真的當一回事。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基本能源品的市場機制在推進過程中受到了阻礙,導致經濟利益無法驅動基本能源品的內在激勵機制。
打個比方,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的居民用電是一毛六分多,現在是四毛多,加上階梯電價也不過只有兩倍多的漲幅,但其他生活用品,包括食品在內,漲幅都達到了100倍以上,什么該精打細算,什么無所謂,一目了然。而對于生產型企業,其粗放型的生產特征也遲遲得不到改造。這些現象歸根結底都是因為沒有內在動因逼迫市場去開發節能降耗產品。
在這種資源環境圖景下,市場改革勢在必行。時值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要素市場推動的改革應該引起高速關注,或者更具體地說,是新一輪的“價稅財”聯動改革。
改革的契機在于,將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原來無關痛癢的從量征收,改為與市場價格波動狀態有機聯系的從價征收,按照這種改革邏輯,就可以消除電力部門過度壟斷,從而改造“從煤到電”的基礎資源品價格機制。這種實質性的激勵機制,能夠促進節能降耗,促進節約發展的有效供給。
現在的資源品稅賦,煤為一噸兩塊多,焦煤為一噸八塊多,對于企業和市場而言無關痛癢;如果變成5%的從價征收,那么在用電高峰期,煤的稅賦就會接近一噸一千多元,哪怕在平常,也會有幾百元。如果再配套電力競價入網、零售環節的改革,那么原來不良供給所形成的壓抑競爭、壓抑效益,就會迎刃而解,最終達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隨之而來的,是四萬多市場主體共同加入節能降耗、低碳發展的隊伍中來——因為他們在內生經濟效益的倒逼下無從選擇。企業要想在市場競爭中求發展,就必須千方百計節能降耗,千方百計地開發有利于節能降耗工藝的產品,繼而形成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這樣的稅收、定價機制,必然也會推導到最終消費品——水電會更貴,政府也需要及時適度提高低保標準,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中等收入階層則會相應改變消費模式,形成低碳化生活的習慣。如此,將會實質性推進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讓造福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得以實現。(支點雜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