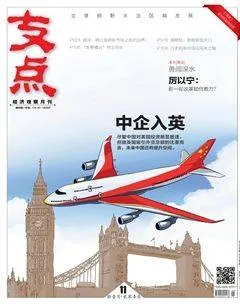剛?cè)嵯嗤粕兓?/h1>
2013-12-29 00:00:00于微
支點(diǎn) 2013年11期



凡有成就的書法家,都對傳統(tǒng)下過一番狠功夫,對硯耕有著堅(jiān)強(qiáng)的毅力。徐本一幼時(shí)便極富天資,受其曾祖徐庚福指導(dǎo)自幼臨帖,“從李北海得筆法,由此而上下窺探”。早年以李北海式的楷書和米芾式的行書屹立于書壇,作品有著流暢、疏朗的風(fēng)姿,唐人李北海的《岳麓山寺碑》是徐氏家族傳家之寶。
自李北海后,徐本一臨習(xí)歐、顏、蘇諸家,繼而專攻“二王”,兼習(xí)鐘太傅、李邕、黃山谷、米襄陽,上通秦漢魏晉,下悟唐宋明清,可謂篆、隸、正、草無不廣涉。參悟北碑意趣,力主情性,師法自然,所作或清真雅淡,或質(zhì)樸遒勁,各具風(fēng)姿。
隨著他對書法探求的不斷攀高,他又在立足于帖的基礎(chǔ)上,致力于碑的實(shí)踐。對于帖學(xué)、碑學(xué),徐本一認(rèn)為,碑學(xué),乾道也;帖學(xué),坤道也。碑學(xué),構(gòu)建陽剛之美的一極,帖學(xué),構(gòu)建陰柔之美的一極。兩極作為相互的參照,相摩相蕩,“剛?cè)嵯嗤贫兓保@是就大趨勢言之。
而徐本一的作品正如他對帖學(xué)、碑學(xué)的解釋,帖以精美為長,碑以渾樸為雄。其書風(fēng)當(dāng)屬陽剛之美的一類,但他并不排斥南帖秀麗的一面。精美之字如清水中觀魚,賞心悅目;渾樸之書似霧里看花,耐人尋味。將兩者完美結(jié)合,成為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biāo)。他從《岳麓山寺碑》上溯北碑,加強(qiáng)筆墨語言的錘煉,使自己的書風(fēng)逐漸轉(zhuǎn)變,化古為我,并讓以秀逸的“書卷氣”為主的書風(fēng)轉(zhuǎn)化成為蒼厚的“金石氣”為主的書風(fēng)。
徐本一的創(chuàng)作不僅敢于面對傳統(tǒng),而且善于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傳統(tǒng);他不僅從傳統(tǒng)中索取,而且更懂得怎樣去偏離。如果說行書《蘇東坡前后赤壁賦》是其碑帖結(jié)合的代表作的話,那么他的行書斗方作品則是融入現(xiàn)代意識(shí)的作品,從筆墨、字形上更注重視覺效果,更具視覺沖擊力。
正如三峽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院長周德聰所評(píng)價(jià)的那樣:“徐本一的筆墨,沉凝厚重與飄逸灑脫并舉,其用墨華滋與枯渴兼施,使得‘秀處如鐵,嫩處如金’、‘萬歲枯藤’之美,如金似鐵之重。”
“‘作字’雖是形學(xué),但仍應(yīng)向心學(xué)去探求。”徐本一說道,只有詩意與書意的完美結(jié)合,才會(huì)給書者提供更真實(shí)自然的情緒基調(diào)、才會(huì)給觀者提供更大的審美想象空間。
的確如此,徐本一先生在廣泛品賞、揣摩、領(lǐng)會(huì)和臨習(xí)的同時(shí),自覺把工力的磨煉上升到書情、書意、書境、書韻的層次上培育自己,就是在這樣的基點(diǎn)上不斷地超越自己。(支點(diǎn)雜志2013年11月刊)



凡有成就的書法家,都對傳統(tǒng)下過一番狠功夫,對硯耕有著堅(jiān)強(qiáng)的毅力。徐本一幼時(shí)便極富天資,受其曾祖徐庚福指導(dǎo)自幼臨帖,“從李北海得筆法,由此而上下窺探”。早年以李北海式的楷書和米芾式的行書屹立于書壇,作品有著流暢、疏朗的風(fēng)姿,唐人李北海的《岳麓山寺碑》是徐氏家族傳家之寶。
自李北海后,徐本一臨習(xí)歐、顏、蘇諸家,繼而專攻“二王”,兼習(xí)鐘太傅、李邕、黃山谷、米襄陽,上通秦漢魏晉,下悟唐宋明清,可謂篆、隸、正、草無不廣涉。參悟北碑意趣,力主情性,師法自然,所作或清真雅淡,或質(zhì)樸遒勁,各具風(fēng)姿。
隨著他對書法探求的不斷攀高,他又在立足于帖的基礎(chǔ)上,致力于碑的實(shí)踐。對于帖學(xué)、碑學(xué),徐本一認(rèn)為,碑學(xué),乾道也;帖學(xué),坤道也。碑學(xué),構(gòu)建陽剛之美的一極,帖學(xué),構(gòu)建陰柔之美的一極。兩極作為相互的參照,相摩相蕩,“剛?cè)嵯嗤贫兓保@是就大趨勢言之。
而徐本一的作品正如他對帖學(xué)、碑學(xué)的解釋,帖以精美為長,碑以渾樸為雄。其書風(fēng)當(dāng)屬陽剛之美的一類,但他并不排斥南帖秀麗的一面。精美之字如清水中觀魚,賞心悅目;渾樸之書似霧里看花,耐人尋味。將兩者完美結(jié)合,成為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biāo)。他從《岳麓山寺碑》上溯北碑,加強(qiáng)筆墨語言的錘煉,使自己的書風(fēng)逐漸轉(zhuǎn)變,化古為我,并讓以秀逸的“書卷氣”為主的書風(fēng)轉(zhuǎn)化成為蒼厚的“金石氣”為主的書風(fēng)。
徐本一的創(chuàng)作不僅敢于面對傳統(tǒng),而且善于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傳統(tǒng);他不僅從傳統(tǒng)中索取,而且更懂得怎樣去偏離。如果說行書《蘇東坡前后赤壁賦》是其碑帖結(jié)合的代表作的話,那么他的行書斗方作品則是融入現(xiàn)代意識(shí)的作品,從筆墨、字形上更注重視覺效果,更具視覺沖擊力。
正如三峽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院長周德聰所評(píng)價(jià)的那樣:“徐本一的筆墨,沉凝厚重與飄逸灑脫并舉,其用墨華滋與枯渴兼施,使得‘秀處如鐵,嫩處如金’、‘萬歲枯藤’之美,如金似鐵之重。”
“‘作字’雖是形學(xué),但仍應(yīng)向心學(xué)去探求。”徐本一說道,只有詩意與書意的完美結(jié)合,才會(huì)給書者提供更真實(shí)自然的情緒基調(diào)、才會(huì)給觀者提供更大的審美想象空間。
的確如此,徐本一先生在廣泛品賞、揣摩、領(lǐng)會(huì)和臨習(xí)的同時(shí),自覺把工力的磨煉上升到書情、書意、書境、書韻的層次上培育自己,就是在這樣的基點(diǎn)上不斷地超越自己。(支點(diǎn)雜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