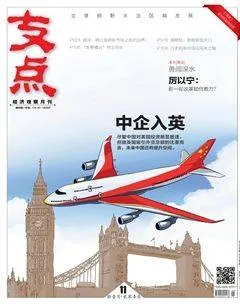銀行家的形象
前段時日,國務院發布相關政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行業,特別指出要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民營銀行由此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社會各界對此反響熱烈。
各地都有民營企業或機構積極向銀監會申辦民營銀行,其中不乏已在商業領域取得成功的知名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中關村等等。可以預見,在這個過程中將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銀行家,在為本企業創造利潤的同時,他們也將滿足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促進金融資源合理配置,推動我國經濟增長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在當代人的理解中,這群銀行家不僅僅是追逐財富的人,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人。
然而揆諸歷史,銀行家的形象有著令人玩味的轉換,作為其前身的放貸者在古代社會中名聲可不怎么好。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對“從作為交易中介的錢幣上取得私利”的放貸者們就沒有什么好感,認為其利潤來源“利息”,即“錢幣所生的錢幣”是不合乎自然的,從事這個行業當然就是“令人可憎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令人可憎的”行業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歷史長河中越來越耀眼。
在歐洲中世紀,由于基督教義的影響,這種“不自然”的經營行為在人們的觀念中升級為極為邪惡的活動。基督教會嚴禁放高利貸,那些從事高利貸職業的人,被視為邪惡之徒,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有意思的是,教會自己卻離不開銀行。在征收稅款、匯兌資金方面,教會必須依賴于銀行家們的幫助,到了后來更是需要銀行提供貸款。
與教會的官方腔調不同,銀行家特別是大銀行家實際上頗受照顧。1291年,法國國王菲力四世逮捕了境內所有的意大利商人,教皇立即進行干預,要求釋放幾名意大利商人,特別是來自錫耶納、佛羅倫薩和盧卡的幾名商人,因為他們同時也從事著教會已經不可或缺的銀行業務。甚至后來為了征稅方便,銀行家取得對教皇委任令的控制。教皇的委任令不是發給候選人,而是先交給銀行家。1448年,美第奇銀行布魯日分行致信約克大主教約翰·坎普,告知他美第奇銀行在羅馬的合伙人幫助約翰的侄子托馬斯·坎普戰勝英王亨利六世和威廉·波爾支持的候選人,謀得了倫敦主教的職位。他們在信中要求大主教在一個月內把其侄子的授職費支付給美第奇倫敦分行經理。否則,他們就不得不遺憾地把密封的教皇詔書發還羅馬。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即使處于充滿敵意的意識形態環境中,銀行家也混得風生水起,不僅推動著銀行業的茁壯發展,對社會也發揮著深層次的影響力。
自從亞當·斯密將對私利的追逐正當化為社會前進的動力以來,銀行業發展的意識形態障礙就化為了歷史的塵埃。在現代工商業需求的刺激下,銀行業取得了小農經濟下難以想象的成就,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現代社會中,銀行家已然華麗轉身,成為了社會中受人尊敬的人物,與古代逐利之徒的貪婪形象自是大異其趣。
1949年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在國家信用的保障下,我國銀行業安全性有余、靈活性不足,銀行家個人的發揮空間在制度的束縛下也著實有限,對當時銀行家的印象可能會覺得他們更類似于刻板的政府官員。
在當前經濟結構轉型中,經濟增長越來越寄望于中小企業充滿活力的創新,而中小企業細微的金融需求是大型國有銀行和商業銀行難以滿足的。當前民營銀行定位于服務三農、社區和小微企業,正是為了填補大型國有銀行和商業銀行所留下的市場空間。可以想象,銀行家的智慧與經驗、審慎與勇氣、堅持與創新在這個空間中必將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我們期待著更富人格魅力的銀行家形象。(支店雜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