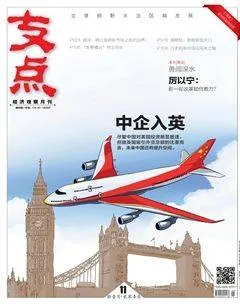新一輪改革如何著力?

在中國,多年以來形成了所謂的“投資沖動怪圈”——地方政府謀求經濟發展,增加投資、 擴大信貸,致使物價上漲太快,帶來通貨膨脹隱患,于是中央政府采取緊縮政策調控,卻又帶來地方發展的諸多難題,如此往復,經濟大起大落。
中國經濟出現的種種問題都和這個“怪圈”相關。這告訴我們:提高經濟總量的同時,更應該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只有在轉型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質量提升,經濟結構才能隨之優化。
尋找新一輪改革的著力點
中國的轉型不能夠照搬國外的增長模式。中國是一個雙重轉型的國家,第一重是發展轉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第二重是體制轉型,即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跟發展轉型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中國這種雙重轉型在全世界沒有先例,所以中國在改革初期只能邊探索邊前進,當時流行一句話,叫“摸著石頭過河”。這是對的,當時也只能這么做。
當前,改革終于取得了很大進展,進入了深水區,摸不著石頭了。如果河里的石頭分布不均勻,摸著摸著又摸回來了,那該怎么辦?這種情況下需要有頂層設計,用戰略家的眼光統籌安排,從戰略高度尋找新一輪改革的著力點。
宏觀調控不能替代改革
經濟如同人體,若要健康,就必須實現內在機制的完善,必要時“打針吃藥”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這只能屬于輔助,最重要的還是身體自身的完善。
宏觀調控好比外來力量,重要但卻是輔助。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出現了“宏觀調控依賴癥”,這種依賴性容易產生誤導:既然宏觀調控這么靈,還要改革干什么?實際上,這耽誤了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解決機制問題,若不依靠改革來健全內在機制,那么越拖到后來,代價會越大,成本會越高,難度也會越大。所以,在宏觀調控問題上,應該重在微調,重在預調,一般情況要避免采用。在政府調控與市場發展的關系上,應強調“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場”,各司其責,雙管齊下。
初次分配重在機會均等
中國現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強調機會均等——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差別則是市場調節的結果,即優勝劣汰。
在初次分配當中,首先要明確農民的產權,其次要重新分配教育資源,保證城鄉教育平等。
二次分配重點應放在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而非增稅,但要量力而行,因為其中存在福利剛性問題——福利能多不能減,有了就不能再取消了。中國要在量力而行的基礎上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
三次分配則要有制度配合。
城鎮化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
城鎮化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這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改革之一,其主要問題是農民的市民化。中國國情的城鎮化等于“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三部分所組成:老城區重在改造,新城區重在發展工業園區,而“新社區”的出發點則在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在“新社區”的建設中,需要注意五個方面的工作:注重建設的園林化;處理好垃圾回收使用、清潔生產、污染清理等循環發展問題;做好公共服務;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建設社區管委會,代替村委會。
“新社區”作為城鎮化的一部分,可以避免過多的人涌入老城區、新城區,達到“就地城鎮化”的效果。
城鎮化過程中,首先要解決城市建設經費中的土地財政和地方債務問題。可借鑒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模式,以城市為主體,發行公共建設投資基金券,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銀行存款高、比國庫券高,購買之后不僅有利息,還可以在項目盈利后分紅,對資金有很強的吸引力。
另外,解決城鎮化過程中房地產市場價格居高不下的問題,需要從兩頭入手,一方面土地招標采用“同等技術標準、質量下價格低者中標”的模式,另一方面房產不限購,而限轉賣。如此一來,才能將城鎮居民的居住問題徹底解決。
國企應成為真正獨立的企業
國企改革在最近20年內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并未到盡頭。
國企改革,應讓國企成為自主經營的國企,控股問題由法人治理結構決定,而后由相應的董事參加企業經營決策。在這個過程中,盡量避免一家獨大,形成董事會內“百家爭鳴”,從而推動企業效率的提升。
國企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企業,將會改變中國的面貌。在這個過程中,國企和民企成為競爭對手和合作伙伴,最終達成共贏。
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墨西哥、馬來西亞等國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進時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這些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無外乎遭遇了制度陷阱、社會危機和技術陷阱,而這些問題的根源來自于土地問題的持久不解決和國家創新能力的突破乏力。
對中國而言,正在進行的土地確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國有企業改革、民營企業轉型等,都表明中國完全可以避免陷入這種陷阱,這不僅包括“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包括了高收入階段可能出現的經濟停滯。
進入新時期,最大限度地調動民間積極性,讓中國掀起又一個創新和創業高潮,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支點雜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