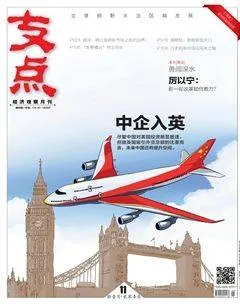生態新城探路“轉方式”



從武漢高鐵火車站出發,驅車上環城路后向東轉入花城大道,約7分鐘后就遠離了中心城市的喧囂,駛入山水相間的城郊。此時,便可看到在湖畔的一大片平地上,一座小鎮正在興建中,這就是“花山新城”。
新城是相對老城來說的。花山位于武漢市東郊,原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鄉鎮。1958年,花山鎮被列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發了“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的國家級獎狀。
歷史總有驚人的巧合。2007年底,在武漢城市圈獲批國家“兩型社會”(即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后,花山鎮又一次成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承擔起落實“兩型社會”先行先試重任,充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路先鋒。
也就從那時起,花山鎮開始重新規劃并興建,現通常稱為花山生態新城。
啟動“反規劃”設計
“以前,我們這里的人總羨慕城里生活,年輕人讀書或多或少,都不愿意留下。”36歲的李云是花山鎮順水口村村民,1996年讀完職高后,他跟村里其他同齡人一樣,離開家鄉到大城市打工。但在兩年前,他回到花山的生態藝術館從事安保工作,并在新城買了房,成了家。
不是一直都向往大城市嗎?為什么在大城市打拼10多年后反而回到了家鄉?李云笑了笑說,以前是因為家鄉窮,房子矮,黃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總覺得城里是另一片天地。但真的待久了,發現城市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人多,車多,天總是灰蒙蒙的,生存壓力也很大。”
兩年前,聽說花山正重新建設。李云回來一看,感覺處處生機盎然,置身其中,盡管有的地方還在建設中,但明顯可以感覺到與傳統大城市的區別,除了山水等自然資源受到嚴格保護外,中水循環、電瓶車、地源熱泵等節能設施也隨處可見。
最讓李云好奇的,還是還建社區的光伏發電功能。在小區的樓頂、綠化帶中間架著一排排光伏電池板,這些電池板接收的太陽能發電給小區路燈等公共設施供電,“也就是說,小區公共設施的照電可以不花錢。”當然, 光伏發電也可以與正常的電路并入國家電網使用。
花山新城規劃面積67平方公里,其中生態保育區就有約40平方公里,約占總面積的三分之二。生態保育區由湖泊、山體、林地組成,在城中形成一道道生態屏障。而建設區相對集中,6條寬敞的自然綠道有機分隔,公園、綠地穿插其中,綠化率高達60%。
花山生態新城前期規劃建設由湖北聯投集團負責,該集團花山公司總經理助理胡黎明向記者介紹,傳統城市規劃往往是優先布置道路和建設用地,然后零散布置一些公園綠地。這種理念往往會帶來擁堵、空氣質量不好等城市病。而花山生態新城則采用的是“反規劃”的設計理念,優先建立生態綠地網絡,用于為城市提供良好生態環境,支撐可持續發展,然后在生態綠地之間布置道路和建設用地。
花山新城的生態規劃也得到了專家們的普遍認可。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潘云鶴院士表示,花山生態新城將對中國新一輪城鎮建設產生深遠的示范影響。
破解二元難題
哪里是城市,哪里是農村,在花山生態新城已經很難分清了。
新中國成立以來,城市的發展速度遠遠快于農村,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工資待遇水平,還是公共服務的完善,農村與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使得中國很多地方出現城鄉二元結構的特殊境況。
盡管李云不太明白什么是城鄉二元結構,但他對城鄉之間的差異還是深有感觸。
“以前,在農村,基本上沒有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看病只能靠個人,壓力太大。”在花山新城還未興建的2008年,因家里拿不出足夠的錢,80多歲的奶奶得不到很好的治療,最后離開了人世。這件事對李云的打擊很大。
在舊城拆遷的時候,李云的心里還有些忐忑:對農民來講,以前有田地的時候雖然過得比城里要差一些,但起碼還有田地作為最低保障。現在要是沒有了田地,以后靠什么生活?
早在新城規劃之初,潘云鶴就提出,要特別重視“鄉城統籌,對失地農民做好安置工作”。
“實際上,在建設新城之前,如何安置失地農民的生活,是規劃的重中之重。”花山街道辦主任齊永強只有36歲,但已在基層政府部門工作14年,對農民的情況比較了解。
沒有了田地,首先要給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
66歲的李德勤是一位搬進還建小區的老人。他說,老鎮拆遷,全家搬進了還建樓,政府也幫他們辦理了社保,現在他和老伴每人每月可以領1000多元的保險費,基本夠兩人的日常開支。
現在,每天早晚,李德勤和老伴都會接送孫子上學。其余時間,他會到小區的健身場地去鍛煉,一切過得跟城里沒什么兩樣。
“城市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什么?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更幸福。”胡黎明說,花山生態新城從最初的規劃到興建,一直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的新型城鎮化之路,讓城鄉居民都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發展“可持續”產業
盡管農民有還建樓,有青苗費等補償款,還有養老、醫療等保險,但擺在全鎮農民面前更為嚴峻的問題是:補償款夠用一輩子嗎?沒有了田地,以后的日子怎么過?
北京大學城市規劃設計中心主任呂斌教授認為,生態新城建設最重要的,是要有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要用一種新的價值觀來看待人與環境的關系。
怎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認為,歸根結底,一座城鎮,要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就必須要有可持續發展的產業作為支撐。
“花山既然被稱為新城,在產業選擇上也必然要有新特色。”胡黎明說,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主要是依靠資源和人工等要素的低層次累積而成,但這種發展方式不僅嚴重浪費資源,還嚴重破壞環境,是不可持續的。花山既然要建新城,就必須要在產業結構轉型上有所突破。
優化產業結構,由二產領先向三產優先轉變,是花山生態新城的另一項重要任務。結合其定位,以及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的特點,花山生態新城將現代服務業放在突出位置,其產業布局最后確定以研發設計、港口物流和會展旅游三大產業為主,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向資本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轉變。
圍繞新城在產業上的定位,失地農民也在尋找與新產業的對接。齊永強介紹,在幫農民購買社保后,村集體將部分剩余款項按股份成立股份集團,每位村民都有股份,公司盈利后每年可按股分紅。目前,有的村股份集團成立了物業、保潔、綠化等公司。這些公司也吸納了部分就業人員。
“以前大家進城,主要是為了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為城里工作機會多,而家鄉要么只能種田,要么就做點小生意。”李云說,自從生態新城開建后,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年輕人都選擇回到家鄉,看中的就是在家門口也能從事跟城里一樣的工作,懂技術的可以進大公司,沒有手藝的也可以就地從事服務業。
記者到花山新城采訪當天,正好遇上一家即將開業的酒店對外招聘,包括經理、廚師、電器維修、服務員等有好幾十個崗位,而前來求職大多數都是原花山鎮的村民。
李云看到招聘廣告后,也給嬸嬸打了電話,問她想不想回來應聘,他的嬸嬸在武漢市內的一家酒店里打工。李云說,等軟件新城招聘的時候,他還會給在南京IT公司上班的表弟打電話,勸他也回到家鄉來,“以前親戚大多都分散在各地打工,平時很難見上面,以后家人聚的時候就多了。”
探路生態文明
花山生態新城,在許多人看來,或許只是從農村搬到了城市;對新城開發者而言,或許只是拆了舊鎮建了新城。但在華中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原院長曾菊新教授看來,生態新城建設有更深遠的意義。
在農業經濟時代,人們希望占有和開發土地,開始建立城市文明;在工業經濟時代,人們希望擁有資本和效率,享受近現代物質文明,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時,也產生了“城市綜合癥”,交通擁堵,空氣混濁,滿眼望去都是鋼筋水泥。
現在到了后工業時代,也被稱為知識經濟時代,我們需要怎樣的城市?曾菊新的回答很簡潔:“轉方式。”
在曾菊新看來,以前提得比較多的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現在更多說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前者側重于量的增加,后者不僅包含生產要素投入的變化,而且包括發展的動力、結構、質量、效率、就業、分配、消費、生態和環境等因素,涵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各個方面。
“站在全局視角,花山生態新城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導向價值和示范意義。”曾菊新說,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局勢面臨深刻調整,中國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擴內需,要走新型城鎮化之路,都需要有試點的樣本。湖北要構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就需要在轉方式上有所突破。武漢城市圈作為“兩型社會”配套試驗區,理應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具體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新城建設中的各項綠色指標,還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再或是城鄉一體化的綜合配套建設,花山生態新城都將在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進行有益的探索。(支點雜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