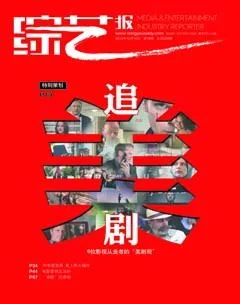影視聯動話劇
近年來,話劇舞臺呈現出一個新特點,即把一些當代作家的作品,或者已有的影視劇作品重新打造成話劇來吸引受眾,獲得電視、電影之外第三陣地的上座率、口碑和票房。這種深度解構、重建文藝作品,并以多種形態表現的做法,實際上是在最大化地挖掘作品的文藝潛力和經濟價值。
比如,2012年9月,孟京輝將余華的《活著》搬到國家大劇院演出;今年1月,郭寶昌從熒屏走向舞臺,以“白景琦和他的三個女人”為故事主線,將40集的《大宅門》電視劇縮減為3小時的話劇;9月,郭小男執導的《推拿》也剛剛落下帷幕。這些已有一定群眾基礎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在話劇舞臺上再度煥發新姿。
影視劇和話劇的互動是雙向的,例如,在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觀眾就能看出《雷雨》里的情節和人物關系;而一些深受年輕人喜愛,具有先鋒意識的話劇作品,也重新回爐制作成了影視劇作品,由舞臺登上熒幕。例如,林奕華導演、王紀堯編劇、張艾嘉和鄭元暢等人主演的《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自2008年首演至今,又被鼎龍達國際傳媒、北京體會影視和杭州文廣集團三家公司聯合拿下電視劇版權,投資5000多萬元打造為一部40集的職場大戲。

從某種意義上講,影視作品和話劇已經形成了互為反哺的關系,雙方相互輸入創作靈感和演員、制作團隊資源,影視劇依靠話劇開拓新疆場,話劇也借助影視劇的影響力來支撐話劇市場。
盡管隨著人們收入水平和審美趣味的提升,話劇市場正呈現出向好趨勢,尤其是價格公道、形式多樣的小劇場,更是迎來一派繁榮景象,但與影視劇市場相比,話劇市場的收益和觀眾群體的范圍仍可謂“小巫見大巫”。
話劇市場的現狀不容樂觀,目前話劇的盈利模式主要靠票房,也有一些靠植入,有的兩種情況同時存在。“舞臺劇演出,無論話劇還是音樂劇,只有形成駐場,才能真正有效益。”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話劇《推拿》運作人之一王一楠說。
北京、上海、廣州三地是中國目前最好的話劇市場,但若想實現“話劇市場的春天”,就必須發展二三線城市。很多話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北上廣的成功,而是源于二三線城市的成功。例如,話劇《武林外傳》曾在全國巡演,深入到中國各地的每一個角落,遍及幾十人到幾千人不等的場子,一次在鄂爾多斯的演出,只有200多人觀看,而且大多是當地牧民。“很多演員覺得人少就很傷心,但我跟他們說,一定得比任何演出都認真,因為他們可能一輩子就看過這么一部話劇。作為話劇工作者,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王一楠說,話劇更像是一股潛流,需要慢慢滲入人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話劇在口碑和經濟上的雙贏?經典劇目似乎更容易實現,原創劇目與之相比就非常困難,因為首先需要花費較長時間在劇本創作的磨合上,例如話劇《士兵突擊》,就是在舞臺上磨合了6年才生存下來,成為相對經典的劇目。
“國家大劇院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是兩家非常好的平臺,所以他們有勇氣去獨立投資被長期看好的劇目,也一直鼓勵原創。”王一楠介紹,以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為例,話劇從最小的藝術工坊開始培植,一直到可以搬上大舞臺,給了原創人才更多機會和表現才華的平臺;田沁鑫等話劇導演也一直策劃、培養原創劇目的編劇等活動。很多話劇都起用新人、年輕人來擔當導演、編劇,因為他們更懂得年輕人即主流觀眾群體的內心。如80后導演何念,創作并執導了話劇《武林外傳》《羅密歐與祝英臺》《21克拉》等17部舞臺劇作品,大部分都票房火爆,被譽為上海灘“票房小蜜糖”;青年編劇劉深也成為郭寶昌欽點的《大宅門》話劇編劇,郭寶昌說:“我就愛和年輕人合作,我永遠不能離開年輕人,時代的進步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上,你只有跟著他們,才能跟上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