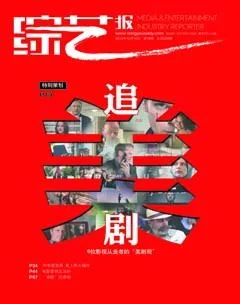終于《團(tuán)圓》專訪王全安
雖然王全安不怎么在媒體上針對他執(zhí)導(dǎo)的影片發(fā)聲,但他很能說,有點北京侃爺?shù)囊馑迹磉_(dá)欲強烈。對于拍攝完成數(shù)年后才登陸國內(nèi)大銀幕上的《團(tuán)圓》,王全安顯然“對影片和市場都很滿意”。該片早已在海外收回成本,也賣出很多版權(quán),三年后在國內(nèi)影院上映,“只不過是錦上添花,毫無票房壓力”,這種情形估計會讓很多“文藝片導(dǎo)演羨慕嫉妒恨”。
目前,王全安在籌備新片《外灘》,也是關(guān)于上海的電影。對此,王全安說北方人對南方人總有一種好奇,就好像中國文明的流向,也是從北向南。
《綜藝》:時隔三年之后,在國內(nèi)大銀幕上重看自己執(zhí)導(dǎo)的影片,感覺如何?
王全安:一般而言,回頭看自己執(zhí)導(dǎo)的電影時都會有些忐忑,但這次覺得還好,內(nèi)心比較踏實,沒有感到太大的落差。除了這部電影當(dāng)時完成的品質(zhì)比較高之外,和它選用的形式也有關(guān)系。這種簡練、緩慢的形式本身隨著時間產(chǎn)生變化的可能性不大。
《綜藝》:《團(tuán)圓》的敘事很精巧,故事結(jié)構(gòu)上前后都有對應(yīng)。
王全安:表面上看似隨意、自然的劇作,都經(jīng)過反復(fù)推敲精心編排,就像一棟大樓里面,每一個構(gòu)件的承重必須經(jīng)過精密計算。對一個好故事而言,結(jié)構(gòu)的力量很重要。這也許是柏林電影節(jié)對劇本會有一個褒獎和認(rèn)可的原因。
《綜藝》:《團(tuán)圓》表面上平淡,其實內(nèi)在沖突很激烈,就像一塊大石頭扔進(jìn)無風(fēng)的河面。
王全安:這屬于個人偏愛。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喜歡比較生活化的東西,表達(dá)大家在生活里很好理解事情;此外,我又很喜歡這種戲劇的爆發(fā)力。電影不可能是生活本身,它只能像生活,有生活的質(zhì)感,必須考慮戲劇沖突的質(zhì)量。
《綜藝》:這兩方面其實很難平衡。
王全安:做起來確實比較吃力。就像綁著手打架一樣,還要打贏,這需要有真材實料才能做得到。對生活的素材積累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對戲劇鋪排的功力,做到兩者相融是很現(xiàn)實也很苛刻的考驗,但我更愿意迎難而上。
《綜藝》:《團(tuán)圓》和《圖雅的婚事》《紡織姑娘》在故事上很相像,都是在講一個女人如何面對兩個男人的問題。
王全安:正常的一對一的男女戀情不足以引起沖突,沒有三角戀的故事,很難展開一段銀幕戲劇。多數(shù)情況下,當(dāng)我們寫男女感情時,基本會寫到三個人以上。電影總是有問題的,重要的是我們解決問題時付出的那些努力。

《綜藝》:《團(tuán)圓》主要靠上海方言對白推進(jìn)劇情,作為北方導(dǎo)演,你在把握上海文化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王全安:最重要的還是對人的理解——什么樣的人會想什么樣的事情,會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對話。這確實有地域上的差異。北方人可能心直口快,南方人則相對迂回含蓄。但這不足以成為一個問題,作為導(dǎo)演,我會通過各種途徑確立上海人的表達(dá)方式。作為北方人我可能看得更直觀更清楚。
《綜藝》:看完影片,《團(tuán)圓》的結(jié)局其實并不“團(tuán)圓”。
王全安:“團(tuán)圓”是中國人最愛念叨的一個詞,代表著我們文化和習(xí)慣里的一種精神追求以及對人生的理a5r4theq0PmAO18U0gnHIA==解。這與我們的情感表達(dá)方式和歷史上注重家庭穩(wěn)定都有很大關(guān)系。無論對人或事,團(tuán)圓是最大的事兒,雖然團(tuán)圓并不意味著快樂,往往矛盾爆發(fā)正是團(tuán)圓的時刻。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很認(rèn)同這種價值觀,人與人之間應(yīng)該有更多的交流。盡管多數(shù)時候,人生不會像我們期待的那般圓滿,但我們依然如此熱切地追求著團(tuán)圓的生活理念。只有這樣,人生才不會顯得那么孤獨。
當(dāng)我們團(tuán)聚的時候,所有的喜怒哀樂匯聚在一起,矛盾也會爆發(fā),但離散的時候又會去思念。這里面有一種很復(fù)雜的情感。
《綜藝》:“吃”,在你執(zhí)導(dǎo)的電影里很有意思,《白鹿原》中的“吃”,看起來很香,但在《團(tuán)圓》中,“吃”顯得很壓抑。
王全安:吃飯代表一種溝通途徑,我們的胃比我們的大腦更深刻,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齡。飲食習(xí)慣對人類的影響很大,臺灣和大陸長時間的分離造成的隔膜在飯桌上就會相對減緩,因為我們的胃口是那么地相似。至于壓抑,因為《團(tuán)圓》的故事背景比較沉重。
《綜藝》:你曾說中國導(dǎo)演對現(xiàn)實生活非常陌生,現(xiàn)在這種看法有變化嗎?
王全安:這是顯而易見的。現(xiàn)在導(dǎo)演和編劇更多在為制片公司創(chuàng)作,為商業(yè)創(chuàng)作,相對而言更自由。但一下子被徹底甩到商業(yè)市場里,我們又在不斷趨利,就會有一種挖空心思、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任何對生活的積累都需要成本,現(xiàn)在很多人顯然認(rèn)為這樣做成本太高,希望什么都不干還可以去賺錢,結(jié)果離生活更遠(yuǎn)了。很多導(dǎo)演有時候被這種劇烈的商業(yè)態(tài)勢逼得進(jìn)入到一種幻想、臆想的狀態(tài)。就像淘金熱時,人們必須千方百計不落人后地從沙里淘到金子。
《綜藝》:但類似《人再途之泰囧》這樣的影片,市場反饋很好,觀眾還是很買賬的。
王全安:我們不能用一種角度和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所有的影片。《人再囧途之泰囧》屬于商業(yè)產(chǎn)品,比較娛樂,承擔(dān)的功能是讓觀眾輕松。但《團(tuán)圓》是另外一種類型——希望觀眾在看的過程中和看后,還可以去反思我們的生活和我們自己。《人再囧途之泰囧》主要訴諸觀眾在觀看過程中的生理快感,不需要思考,就像坐過山車,停下來就沒意思了。
這是一個好現(xiàn)象。但最糟糕的是把二者攪在一起,讓一部影片既要承載娛樂,又要承載思考,什么都想要,最后必然是什么都得不到。
《綜藝》:你怎么看商業(yè)化對我國電影的作用?
王全安:對電影產(chǎn)業(yè)來說,商業(yè)化是一大進(jìn)步。我國電影必須在商業(yè)上達(dá)到一定規(guī)模的情形下,才能談得上其他類型電影的正常發(fā)展。從比重上來講,主流應(yīng)該是商業(yè)電影,有文化承載的藝術(shù)電影永遠(yuǎn)是少數(shù),這在世界范圍內(nèi)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