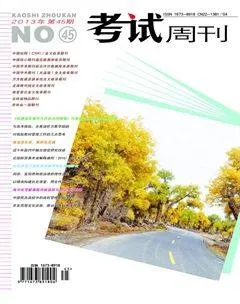古人之愁知多少
摘 要: 愁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情感,古代詩詞名家卻能以神奇之筆,將抽象之愁寫得形象生動,具體可感,使讀者受到極大感染。
關鍵詞: 古詩詞 “愁” 各向賞析
愁是人情之一種,它看不見摸不著,有幾多幾重,就更難衡量。而古代一些詩詞名家,卻往往善于通過修辭手法,將“愁”這種抽象的、難以言狀的心理活動化為形象生動的、具體可感的東西,不僅寫出自身的情感體驗,而且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自古以來,愁長而多者莫過于詩仙李白,他才高八斗,卻不見容于權貴,眼看人生將老而壯志難酬,于是便發出“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秋浦歌》)、“抽刀斷水水更流,舉酒澆愁愁更愁”(《宣州謝胱樓餞別校書叔云》)的驚世之嘆,以表達他“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無奈之感。
愁最多者當屬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這是因為他是一個昏庸無能的皇帝,一個亡國之君,但值得欣慰的是,他還是一個感情豐富細膩的詞人,因而將自己心靈深處的痛楚——亡國之痛,生動而細致入微地反映在詞作之中。可以說,李煜后期的詞作,就是用國仇家恨的經緯線交織而成的情感之網:“多少恨,昨夜夢魂中”(《望江南》),“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烏夜啼》),“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子夜歌》),“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正是這無窮無盡的國仇家恨構成了他后期作品的主要基調,打動了千百年來無數讀者的心,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尤其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兩句更是膾炙人口。清愈陛云說:“亡國之音,哀思之深耶!……《后山詩話》謂秦少游詞‘飛紅萬點愁如海’,出于后主‘一江春水’之句,《野客叢書》又謂李白之‘愁高滟滪堆’、劉禹錫之‘水流無限似儂愁’為后主詞所租但以水喻愁,詞家意所易到,屢見載籍,未必互相沿用。就詞而論,李、劉、秦諸家之以水喻愁,不若后主之春江九字,真傷心人語也。”(《南唐二主詞述評》)“一江春水”之喻,將詞人的亡國之痛寫得有聲勢、有氣勢,如江水,無窮無盡,滾滾而來,連綿不斷,很有藝術感染力。
宋代后期婉約派詞家秦觀的愁多又不同于李煜,他“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以奇妙的假設,將“韶華不為少年留”的傷春惜時的仇恨之淚化作春江,卻仍“流不盡,許多愁”。極盡夸飾之能事。此句,在李后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比喻基礎上,又翻出一層新意,以脫胎換骨,點鐵成金之法,將淚流、水流、恨流挽合做一江春水,滔滔不盡地向東奔去,使人沉浸在感情的洪流中,受到極強的感染。
愁多且久者為宋代又一詞人賀鑄:“試yRBXALaKkCnzizucDx0dDeTzi61ymTLUIRHXenW2+SY=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飛絮,梅子黃時雨”(《青玉案》),在前文“彩筆新題斷腸句”之后,以“試問閑愁都幾許”呼起,然后用“煙草、飛絮、梅雨”等三種景物來表現,煙草連天,喻愁之大;柳絮蒙蒙,喻愁之亂;梅子黃時雨,喻愁之綿綿不斷。連用三個比喻,將不可捉摸的虛的感情轉化為可見可感的實的景物,以景結情,以實見虛,亦虛亦實,只說愁而不說是什么愁,更不說是“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的離愁,不說愁多且久,而是融情入景,朦朧含蓄,將愁寫得鋪天蓋地,難以言說。正如梅堯臣所說:“含不盡之意,盡在言外。”令人回味無窮。
南宋學者羅大經《鶴林玉露》云:“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澒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閑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后主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賀鑄)云:‘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的離別之愁,多且婉曲纏綿,其極負盛名的《踏莎行·候館梅殘》一詞,極具代表性,這首詞寫于宋景佑初年,范仲淹以言事被貶,歐陽修因援助他也被貶于夷陵,這首詞看似寫閨中別情,實為抒己之離恨。其中“離恨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句,以水喻愁,即景設喻,即物生情,寫出了離愁隨著分別時間之久、相隔路程之長越積越多,就像眼前伴著自己的一溪春水一樣,來路無窮,去程不盡,把離人一路前行的感覺,形象而又生動的表現了出來。在這里,抽象的感情在詞人筆下,變成了具體的形象,自然貼切而又柔美含蓄。這兩句,雖然可以使人聯想到李煜《清平樂》:“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和《虞美人》中“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一些名句,但因作者善于變換句法,并且使這一生動比喻跟全詞離人、春草的整體形象,跟詞的春景離情的意境結合得十分緊密,故貌似仿效,而實則是創新,渾然天成,不露痕跡。
李清照的愁是重量級的,她晚年的詞,家國之變與身世之痛交織在一起,“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盡管“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但“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李清照另尋思路,說自己的愁重得連船都承載不動。以船來載愁,將愁物質化了,使詩人的愁苦有了重量,有了質地,變得可親,可感。
李清照是極愛游山玩水的。雙溪是浙江金華的名勝風景區,她想借游覽來排遣心中的凄慘心境,但實際上她的痛苦之大,哀愁之深,豈是泛舟一游所能消釋?所以在未游之前,就已經料到愁重而舟輕水淺,不能承擔了。與《西廂記》里的“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有異曲同工之妙。
縱觀古人之愁,愁因雖然不盡相同,或因國破家亡,或因離別相思,抑或由于懷才不遇、壯志難酬,感嘆時光易逝而功業難成,但大多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形象具體,給人以既多且重,又久又長之感,“剪不斷,理還亂”,這等辛酸與無奈,又“怎一個愁字了得”,只好“欲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