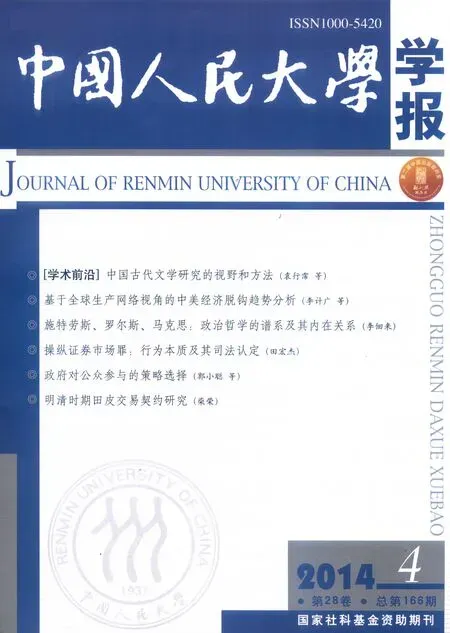金融理論的發展及其演變
吳曉求 許 榮
金融理論和金融市場在近百年中取得了迅猛發展,金融學成為經濟學這一社會科學 “皇冠”上最璀璨奪目的 “明珠”。然而,正當金融學者們陶醉于美妙壯觀的金融理論殿堂時,正當金融從業者們享受著令其他行業羨慕不已的高額股票期權收入時,2008年,起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發端于華爾街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了,并對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體系產生了巨大沖擊和深遠影響。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同時也給金融理論帶來了極大的挑戰,令金融研究者陷入深思,也引發我們重新探究金融理論的演變和發展歷程。
一、早期金融學的理論脈絡:從貨幣、信用到銀行與利率
早期金融理論的演變和研究重心的變化,根據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理解和概括,但圍繞價格決定及其波動因素的研究,無疑是金融理論研究的重點之一,也是推動金融理論演變的重要因素。實際上,在市場化金融結構出現之前,金融學研究演變的軸心是從關注商品價格波動即通貨膨脹規律逐漸過渡到研究資金價格即利率確定的影響因素。出于對商品價格的關注,早期金融學重點研究了貨幣的職能和貨幣的數量,從商品數量與貨幣數量對比的角度得出了物價變動的規律。對資金價格即利率的關注使早期的金融學開始分析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機制,并最終得出中央銀行通過調控貨幣供給進行宏觀調控的政策分析框架。
早期的金融學脫胎于古典經濟學家對貨幣問題的分析,尤其是貨幣本質與貨幣數量的問題。從被稱作 “英國政治經濟學之父”的威廉·配第到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他們都對貨幣的本質和起源、貨幣的職能、貨幣流通規律展開了深入探討,其理論探討的成果最終形成了古典的“貨幣數量論”。①關于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大衛·休謨、大衛·李嘉圖和魁奈在各自著作中均有不同的表述。在古典學派貨幣理論的基礎上,馬克思科學系統地論證了貨幣產生的必然性、本質、職能,以及流通中貨幣必要量的多少。
早期金融學的真正形成始于貨幣、信用與銀行之間的緊密關系及其對物價、利率和經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之時。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中,貨幣主要以金屬鑄幣的形態存在,貨幣與信用仍然保持著相互獨立的狀態。隨著銀行券的廣泛使用,貨幣與信用的聯系日益緊密。到20世紀3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實施了徹底不兌現的銀行券流通制度,貨幣流通與信用活動變成同一的過程,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范疇——金融學。凱恩斯納入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理論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的貨幣需求函數都是早期金融理論的重要內容。早期金融學的研究核心是基于銀行體系的信用貨幣創造機制。信用貨幣創造數量的多少相應地引起商品價格水平變動即通貨膨脹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會影響貨幣價格即利率的確定。因此,早期金融學通過研究貨幣供求的均衡關系,最終轉向貨幣對經濟的作用即貨幣政策的探討。
早期金融學研究的核心是信用貨幣的創造機制,集中體現為雙層次的存款貨幣創造。對這一機制的理論研究始于菲利普斯于1920年出版的《銀行信用》一書。在該書中,菲利普斯首次提出了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的概念,并對貨幣乘數機制進行了詳細分析。[1]1934年,米德在 《貨幣數量與銀行體系》一文中用正式的貨幣供給模型對貨幣供給機制和銀行系統的貨幣創造進行了系統研究。[2]中央銀行通過投入通貨及擴大信貸創造了基礎貨幣,基礎貨幣及其量的增減變化直接決定著存款貨幣銀行準備金的增減,從而決定著存款貨幣銀行創造存款貨幣的能力。眾多存款貨幣銀行則通過自我約束機制分散決策,根據安全、流動、盈利的原則,判斷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客戶的貨幣需求。
在早期金融學的理論研究中,人們最先關注的是商品價格決定及其波動的影響因素,在考慮了信用貨幣創造機制后,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的對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大約從19世紀末期開始,人們對商品價格形成原因的研究逐漸減少,進而轉向研究利率決定。如果說對商品價格的研究是對有形商品價格的研究,那么,對利率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對資金價格的研究。慢慢地,早期金融學開始全面、系統地研究利率,試圖找到是什么因素決定了利率的形成以及利率的高低,研究利率在經濟運行及經濟均衡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這一時期的經典著作是歐文·費雪于1930年出版的 《利息理論》。[3]費雪系統闡述了有關現值、利率和投資的理論,提出了定量的貨幣理論,被譽為中央銀行貨幣規則的創始人。顯然,從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看,從主要研究商品價格到逐步轉向主要研究資金價格即利率,是金融理論研究的一種深化,同時也表明經濟活動開始出現虛擬化的傾向。經濟的虛擬化實質上是經濟體系的進步。
早期金融學關于貨幣對經濟的作用以及貨幣政策調控的分析集中反映在IS—LM模型上。[4]LM曲線包括了所有滿足貨幣需求數量等于貨幣供給數量這一均衡條件的點,因此,貨幣供給的變動或者貨幣需求的自主性變動都會導致LM曲線的移動,相應地引起利率水平和總產出水平的變化。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操作正是基于這一機制,通過調控準備金率、再貼現率以及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影響貨幣供給,從而影響經濟體的總需求及總產出。
二、資本市場發展與現代金融學的理論演進
(一)資本市場發展對早期金融學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以后,作為較古老的一種金融中介,以經營傳統信貸業務為主的商業銀行在經濟生活中雖然依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其傳統的核心功能有衰退的跡象。[5]這從當時金融結構的市場化變化中可以略見端倪。金融結構市場化變革的推動力量來自于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也正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們開始越來越多地研究資本市場問題,特別是資產或風險的定價、風險管理技術以及高度市場化狀態中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資本市場的內容非常廣泛,它不僅是股票市場的問題,更不只是股票價格的波動。股票市場及其價格波動只是資本市場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金融結構的市場化導致金融理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實體經濟運行的角度來看,資本市場構造了經濟運行的新基礎、新平臺。這個新基礎、新平臺的出現,意味著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和運行軌跡都將發生重大變化。如果經濟主體不隨之進行調整,那就意味著會被新的規則拋棄。在沒有資本市場的情況下,經濟活動是相對規則化的,經濟活動的規律性看得相對比較清楚,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理論上也存在著相對的穩定性,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清楚的。在資本市場不斷發展特別是當資本市場成為全社會經濟運行的基礎之后,很多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就變得不那么直接,甚至不那么穩定了,它們之間需要有轉換的變量。也就是說,資本市場的發展將使全社會經濟運行的規則發生根本性的調整。在傳統商業銀行主導金融結構的時代,商業銀行制定的所有規則構成了社會的基本規則。如果不與它對接,就無法獲得銀行體系資金的支持。在金融制度相對單一的那個時代,沒有銀行體系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持續的發展,從而也就不可能有競爭力。在資本市場蓬勃發展之后,資本市場的規則也將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規則之一。[6]
資本市場的發展首先使貨幣的度量變得困難了。在資本市場發展之前,貨幣供給的計量標準主要指存款貨幣銀行中的存款貨幣和經濟體系中流通的現金通貨。但是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的開展,區分貨幣與非貨幣變得越來越困難,貨幣層次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了。以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為例,這類基金把資產投向貨幣市場,很大程度上與存款貨幣銀行的存款資產存在競爭性替代關系,在一些國家 (如美國),貨幣市場基金被計入廣義貨幣供應量 (M2),而在中國則尚未計入貨幣供應量。①盡管中國人民銀行尚未把貨幣市場基金納入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但近年來已經開始考慮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例如,自2001年起,央行把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納入廣義貨幣供應量,自2011年10月起,貨幣供應量已包括住房公積金中心存款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再如,日本央行公布四個口徑的貨幣供應量指標:M1、M2、M3和L,其中L口徑的貨幣供應量包括了投資信托、銀行債券、金融機構發行的融資券和政府債券、外國債券②根據日本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口徑的說明。參見http://www.boj.or.jp/en/statistics/outline/exp/exms.htm/。;韓國央行于2006年6月調整了廣義貨幣供應量M3的結構,并采用金融機構總體流動性 (Lf)作為最新的廣義流動性指標。[7]
資本市場的發展同時也使貨幣需求變得不再穩定,難以有效估計,這是由于資本市場的發展帶來一系列的金融創新,大量的證券化金融資產的涌現,使得這些金融資產和貨幣之間的替代性大大加強。20世紀70年代在金融體系出現了“脫媒”現象,即大量資金從商業銀行體系轉入資本市場。在貨幣估計的經驗研究中也出現了“失蹤貨幣”之謎[8],即根據傳統貨幣需求方程對貨幣需求進行的估計結果明顯大于實際的貨幣余額。
資本市場的發展為貨幣政策及宏觀調控帶來的最嚴峻挑戰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甚至貨幣政策的目標函數都在發生變化。在金融結構市場化變革之前,凱恩斯學派認為,貨幣政策通過利率途徑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這一機制通過IS—LM模型來表達,強調貨幣資金的價格——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然而,隨著資本市場的深化和發展,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變得更加復雜。格林斯潘指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應更多地考慮股票市場的因素。[9]資本市場中種類豐富的金融資產價格變動可能通過托賓Q效應、財富效應以及資產負債表效應對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實施傳導,這一傳導的結果是使貨幣政策的傳導鏈條更加復雜,同時也削弱了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效力。因此,一些發達國家放棄了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實施泰勒規則以利率為中介指標。關于貨幣政策是否應對金融資產價格變動做出反應尚存在爭論,部分學者如古德哈特認為,金融資產價格變動能夠準確反映未來消費物價的變化,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不應把目標只限定在通貨膨脹上,而應當構建包括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在內的廣義通貨膨脹指標。[10](P439—510)而曾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則表明,貨幣政策沒有必要對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做出反應。[11]在中國,亦存在類似的爭議和分歧。
(二)現代金融學的理論演進
伴隨著資本市場發展所推動的金融結構市場化變革趨勢的到來,現代金融學研究的軸心從資金價格逐漸過渡到金融資產價格,從股票、債券等基礎資產的定價理論逐漸發展到期貨、期權、互換等衍生品的定價理論。
20世紀50年代以后,經濟結構特別是金融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利率雖然仍是人們所關注的問題,但已經慢慢地不被經濟學界的主流所重視。人們開始將視野轉向更加復雜的價格理論,即資本市場資產價格的變化及其決定。經濟學家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與當時的經濟結構特別是金融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20世紀50年代以來,金融對經濟活動的作用急劇加大。如果說人們著力研究利率理論意味著貨幣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日益明顯,那么,價格理論的研究重心從較為虛擬化的資金價格即利率轉向更加虛擬化的資產價格,則表明以市場化金融結構為特征的現代金融已逐漸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馬克思曾指出:貨幣資本 “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12](P340)。延伸到今天,似乎也可以這樣認為:建立在金融結構市場化基礎上的現代金融是現代經濟的發動機。
現代金融學始于馬柯維茨1952年在 《金融學雜志》上發表的 《證券組合選擇》一文。[13]該文徹底改變了傳統金融學用描述性語言表達金融思想的方法①在馬柯維茨論文發表之前的 《金融學雜志》上的論文主要討論 “聯邦儲備政策、貨幣增減對于物價與企業活動的影響”等傳統金融學的研究主題,在1959年之前的論文幾乎都是敘述性的,“毫無數學公式的推演”。(參見Bernstein,Peter L.Capital Ideas:The Improbable Origins of Modern Wall Street.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92)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天的《金融學雜志》幾乎整頁都是數學公式的推導,而文字表達所占的篇幅很少。,把研究重點放在資本市場數以萬計證券資產的組合選擇上,分別以均值和方差衡量收益和風險,提出了期望均值—方差理論,即投資者對證券資產的選擇不僅取決于資產的收益均值,還取決于資產的收益方差。然而,當投資者面臨選擇的證券數量增加時,為了計算各種證券可能構成的證券組合,計算量將呈幾何級數增加。威廉·夏普發表于1964年 《金融學雜志》上的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風險狀態下的市場均衡理論》一文,在馬柯維茨資產選擇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了資本市場均衡條件下資產收益的確定,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下,推導出均衡狀態下投資者將只從無風險證券和市場證券組合中進行選擇,即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也被稱為 “單因素模型”。[14]林特納和莫辛分別于1965年和1966年獨立地提出了CAPM模型。[15]
1958年,米勒和莫迪利亞尼共同發表的論文 《資本成本、公司金融和投資理論》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即在完全市場條件下,公司資本結構不會影響公司價值。[16]這一理論不僅奠定了公司金融這門學科的基礎,并且首次明確運用了無套利分析方法。布萊克和斯克爾斯同樣使用了無套利分析方法,對股票價格變動的模型進行連續動態化分析,得到期權價格與股票價格之間的偏微分方程,并最終得出布萊克—斯克爾斯期權定價模型。[17]布萊克—斯克爾斯期權定價模型得到了羅伯特·默頓所做的一系列重要擴展,這些擴展后來被總結在 《連續時間金融學》一書中。[18]同樣使用無套利定價方法,羅斯提出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CAPM不可檢測問題的 “套利定價理論” (APT)。[19]APT實際上是一個多因素定價模型,揭示了均衡價格形成的套利驅動機制和均衡價格的決定因素。
尤金·法馬于1965年在其博士論文中正式提出的有效市場假說 (EMH)理論②EMH理論的正式發表是在1970年,參見Fama,E.F.“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0 (25):383—417。,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本市場資產價格確定的效率問題進行了總結。按照有效市場假說,資本市場具有根據新信息迅速調整證券價格的能力,因此,高度有效的資本市場可以迅速傳遞所有相關的真實信息,使價格反映其內在價值。
現代金融學的理論殿堂對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金融實踐產生了根本性甚至是革命性的影響。對金融資產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精確定價技術的發展,直接導致了金融產品交易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呈現爆炸式增長。對公司金融理論的研究進展以及金融契約理論的發展,使得各種規模的公司在金融市場上的籌資和融資活動變得更加頻繁。資產組合理論的發展和投資組合業績的科學評估,導致基金公司、保險公司和養老金等大型機構投資者積極參與資本市場投資活動,這導致了資本市場規模的空前膨脹。與此同時,原本提供專門化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并購浪潮,致使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的巨無霸式金融機構規模空前擴張,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界限變得模糊。金融活動跨越了國界,金融全球化不僅自身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時更直接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在現代金融理論徹底改變了金融實踐的同時,現代金融學的創立者們也幾乎都獲得了舉世矚目的諾貝爾經濟學獎。①均值方差理論的創立者馬柯維茨和CAPM模型的創立者夏普以及MM定理的創立者米勒共同獲得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MM定理的另一位創立者莫迪利亞尼獲得198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期權定價模型的創立者斯克爾斯和默頓獲得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布萊克于1995年逝世)。并且,不同于早期金融理論的研究者們長期坐守書齋,其理論貢獻對金融市場投融資活動影響有限,現代金融理論例如MM定理、CAPM模型、B-S期權定價模型等,在金融市場的參與者那里都耳熟能詳,并有重要的影響力,這決定了現代金融理論的研究者們在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普遍擁有很高的聲譽,他們幾乎都親身投入金融市場,實踐由他們所創立的金融理論。當然,這其中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敗的教訓。②馬柯維茨1968年即加入套利資產管理公司并創建了第一只通過計算機實施的套利對沖基金;夏普則于1998年創辦了成功的硅谷風險投資公司——財務引擎公司,為客戶提供投資組合規劃;斯克爾斯和默頓在他們擔任合伙人的對沖基金公司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后,斯克爾斯于1999年創辦了Platinum Grove對沖基金管理公司并獲得成功,默頓則為高盛等公司提供風險管理咨詢。
三、現代金融學面臨的挑戰與新金融經濟學的探索
(一)現代金融學面臨的挑戰
現代金融學輝煌的理論殿堂構筑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之上,其理論推導的前提假設之一是市場是完美的,因而并不存在交易成本;前提假設之二是市場參與者都是理性的,并且擁有完全的信息。因此,現代金融理論屬于新古典金融學的范疇,是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研究資本市場在不確定環境下對金融資產進行準確定價,從而對資源和風險進行跨期最優配置的理論體系。在方法上,現代金融學借助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優化分析和均衡分析等基本方法,同時也最大限度地使用了隨機過程理論等現代數學分析工具。
然而,真實的金融世界和現代金融學的理論殿堂是有差異的。一方面,市場并不是完美的,而是受到各種交易成本摩擦的影響。政治架構、稅收制度、監管體系、法律制度、新聞媒體、文化淵源甚至信仰習慣都會影響金融體系的效率。新制度經濟學在現代金融理論的模型基礎上開始考察種種制度因素對金融活動的影響,形成了“新制度金融學”系列研究文獻。[20]目前,這一方向的探索已經涌現出對金融研究影響深遠的兩類研究成果:一是從比較金融視角開展的對商業銀行主導和資本市場主導的比較金融體系的研究[21],另一類是從法律視角探索金融市場建立、運行和發展的制度基礎的研究[22]。
另一方面,市場參與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而在進行金融投融資決策時存在系統性的偏差。首先,現代金融學理論的分析基礎即經濟主體決策基于理性預期、風險回避和效用函數最大化等假設存在問題,例如投資者具有傾向于過分自信和樂觀的心理特征。此外,投資者會有回避損失和存在心理賬戶的系統性偏差。其次,無套利均衡是現代金融學理論分析的基礎,即使市場存在非理性的投資者,理性投資者的套利行為也會使資產價格回到均衡水平。然而,由于存在基本面風險和執行成本以及噪聲交易者風險[23],投資者至多只能進行有限套利。因此,現代金融理論面對一系列金融異象實證證據時并不能提供有力的理論解釋,這些金融異象包括:公司規模效應、日歷效應、市場過度反應、股價過度波動、股票收益的均值回歸以及新信息在股票價格中的反映不足等。
(二)新金融經濟學的探索
盡管現代金融理論遭遇到來自新制度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的挑戰,但是這些挑戰至多只能算是一種探索,還不足以構成一個新的金融經濟學理論體系。正如默頓和博迪所說,新制度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的理論探索只能是在現代金融理論基礎上的一種修訂,他們解釋的更多的是金融資產價格為何會出現對現代金融理論模型預測的偏離。因此,現代金融理論仍然為資本市場的資產定價和公司金融決策提供了基礎模型,類似于解釋了變量的一階效應,而新制度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這些新金融經濟學的探索則類似于解釋的是二階的乃至更高階的效應。
默頓和博迪對新制度金融學理論貢獻的解釋是,現代金融學把不同金融體系內部的特殊制度結構和組織形式視為外生給定的,由于不存在交易成本,不同金融制度和組織結構的選擇并不重要。而新制度金融學的核心思想是,只有金融活動的特定功能才是外生的,而金融制度結構和組織形式則是內生形成的,因此,在特定的經濟發展背景下,金融制度的選擇就顯得至關重要了。當然,默頓和博迪也承認,新制度金融學的發展并不是要替代現代金融理論,而僅僅是建立在現代金融理論基礎上的修訂,在發展良好的金融體系中,現代金融理論關于資產定價和公司金融的主要結論都是毋庸置疑的。
新金融經濟學在另一方向上的探索——行為金融學的理論基礎是有限套利理論和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又表現為非財富最大化行為和啟發式偏見以及定式心理誤會。行為金融學的探索同時還滲透到資產定價和公司金融這兩大金融研究的核心領域。行為金融學的研究者們針對CAPM提出了行為資產定價理論。[24]他們提出,市場上存在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也存在認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噪聲交易者,因此,當前者主導市場交易時,市場是有效的,而當噪聲交易者主導市場時,市場是無效的。此外,斯坦研究了投資者非理性,而公司管理層理性情況下的公司融資行為。[25]謝夫林的分析發現,公司管理者的認知不理性和情感影響容易導致決策失誤,而公司外部投資者和分析師的認知偏差則使公司股票偏離其基本價值。[26]盡管行為金融學在最近十多年里發展迅速,亦有行為金融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①例如,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恩曼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弗農·史密斯,以表彰他們在行為經濟學及行為金融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但是,行為金融學尚未發展出被普遍接受的完整理論框架。
四、金融學的未來
氣象學家洛倫茲于1963年提出著名的 “蝴蝶效應”:“一只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27]回顧金融發展的歷史,公元994年前后,我國宋朝四川商人發行自己的私人紙幣 “交子”時絕沒有想到,數百年后紙幣在全世界完全替代了金屬貨幣。②參見威廉·N·戈茲曼、K.哥特·羅文霍斯特:《價值起源》,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10。迄今為止,還沒有有力的證據來證實或證偽14世紀歐洲早期貨幣市場的發展是否應歸功于中國早期的紙幣模式。而1973年時的布萊克和斯克爾斯也沒有想到,他們對期權定價的研究[28]像颶風一樣引發了百萬億美元的衍生品交易,徹底改變了隨后的金融實踐和金融理論研究方向。展望未來的金融學研究,引發未來金融實踐 “龍卷風”事件的曲折微妙的 “蝴蝶翅膀”機制將在新一代金融學者手中如何飛舞呢?
首先,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現代金融理論體系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 “大致有效”。因此,在對任何金融現實問題的分析上,現代金融理論都將為金融學者提供一個好的出發點而不是終點。可以預見,現代金融理論和新制度金融學以及行為金融學將在理論互補的基礎上發展演進,暫時還不會出現一個全新的金融理論范式。正如博迪和默頓所說,現代金融理論將在資產定價、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上大致正確,而新制度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則將在金融制度演進、金融機構組織和金融工具開發等領域提供理論指導。
其次,金融功能視角,尤其是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金融功能觀,將在很大程度上指導未來的金融實踐和金融研究。從金融功能視角出發,金融制度設計、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定位以及金融產品的創新開發都將是內生決定的,都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企業和投資者特定金融功能而發展出來的。因此,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將處于靜態競爭和動態合作的創新螺旋之中。一般而言,這一創新螺旋表現在金融機構創新開發出新產品,一旦新產品擁有廣泛的市場,就將迅速地在資本市場上獲得推廣,資產證券化就是一個典型范例。
第三,對于中國學者而言,應將對金融理論的研究與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實踐聯系起來。不論是從現代金融理論演進的邏輯出發,還是從當前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看,都要把金融結構市場化、證券化作為影響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和穩定的至關重要的戰略目標,而金融結構市場化、證券化的主要推動力來源于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大發展。存量資源調整、風險流動和分散、經濟增長的財富分享機制是資本市場具有深厚生命力和強大競爭力的三大原動力,也是近幾十年來資本市場蓬勃發展的內在動力,是現代金融體系核心功能的體現。無論是風險分散還是資源配置,無論是增量資金需求還是存量資產流動,離開了資本市場,其效率都將大打折扣。綜觀美國、日本、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任何一個經濟體從小到大的迅速成長過程中,無不體現著資本市場這個存量資源配置和風險配置平臺的重要作用。金融結構的市場化、證券化強調的是有效的風險流動和釋放機制,通過它們,可以避免風險的不斷積聚和對經濟體系的巨大破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資本市場是中國金融政策的核心任務之一。
[1]Phillips.Bank Credit:A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and Factors Underlying Advances Made by Banks to Borrowers.New York:Arno Press,1980.
[2]Meade,J.E.“The Amount of Money and the Banking System”.Economic Journal,1934 (44):77-83.
[3]Irving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0.
[4]John Hicks.“Mr.Keynes and the Classics: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Econometrica,1937,5 (2):147-159.
[5]Allen,Franklin,and Anthony M.Santomero.“What do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Do?”.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1,25 (2):271-294.
[6]吳曉求:《金融的過去、今天和未來》,載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1);《夢想之路——吳曉求資本市場研究文集》,257-275頁,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
[7]The Bank of Korea.Monetary Policy in Korea (Second Edition),2008.
[8]Stephen M.Goldfeld.“The Case of the Missing Mone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76,3:683-730.
[9]Greenspan,A.“New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Opening remarks at a Symposium,Fed of Kansas City,1999.
[10]Goodhart,C.“Price Stability and Financial Fragility”.In K.Sawamoto,Z.Nakajima,and H.Taguchi(eds.).Financial Stabilit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
[11]Bernanke,B.,Gertler,M.,and S.Gilchrist.“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In J.Taylor,and M.Woodford(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Vol.1C.New York:North-Holland,1999:1341-1393;Bernanke,B.,and M.Gertler.“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2):253-257.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Markowitz,Harry.“Portfolio Selection”.The Journal of Finance,1952,7 (1):77-91.
[14]Sharpe,W.F.“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The Journal of Finance,1964,19 (3):425-442.
[15]Lintner,J.“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5,47 (1):13-37;Mossin,J.“Equilibrium in a Capital Asset Market”.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66:768-783.
[16]Modigliani,F.,and Miller,M.H.“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48 (3):261-297.
[17][28]Black,Fischer,and Myron S.Scholes.“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 (3):637-654.
[18]Merton,Robert C.Continuous-Time Finance.Cambridge,MA.:Basil Blackwell,1990.
[19]Ross,S.A.“The Arbitrage Theory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6,13(3):341-360.
[20]Merton,Robert C.,and Zvi Bodie.“Design of Financial Systems:Toward a Synthesis of Form and Structure”.Journal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2005,3 (1):1-25.
[21]Franklin Allen,and D.Gale.“A Welfare Comparison of Intermediar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Germany and the U.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179-209;Franklin Allen,and Douglas Gale.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Cambridge,MA.:MIT Press,2000.
[22]La Porta,Rafael,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and Robert Vishny.“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e,1997 (52):1131-1150;La Porta,Rafael,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and Robert Vishny.“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 (106):1113-1155.
[23]DeLong,J.Bradford,Andrei Shleifer,Lawrence H.Summers,and Robert J.Waldmann.“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4):703-738;Shleifer,Andrei,and Robert W.Vishny.“The Limits of Arbitrage”.Journal of Finance,1997,52(1):35-55.
[24]Sherfrin,H.,and M.Statman.“Behavi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Theory”.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1994 (29):323-349.
[25]Stein,J.“Ra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in an Irrational World”.Journal of Business,1996 (69):429-455.
[26]Shefrin,H.“Behavioral Corporate Finance”.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01 (14):113-124.
[27]Lorenz,Edward N.“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1963,20(2):13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