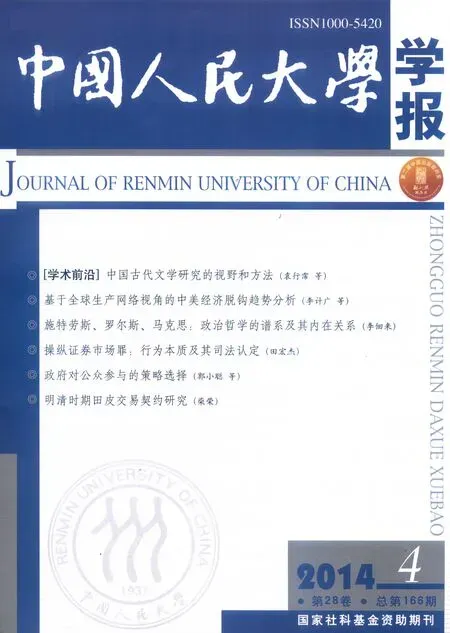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限的理論假說及其驗證
張培麗
中國經濟能否將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再延續20年,是決定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震蕩徘徊,2012年經濟增長率13年來首次低于8%,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有多長?中國經濟由高速經濟增長轉向中低速經濟增長的拐點究竟在哪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廣泛的解讀和爭論,概括起來主要有:
(1)崩潰說。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代已經結束,而且由于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積累的一些深層矛盾已經顯現和爆發,中國經濟即將硬著陸,并很快走向崩潰,特別是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呈下行之勢。保羅·克魯格曼在2011年年底預測指出,中國有可能成為歐債危機之后的下一個經濟危機發生地。[1]米歇爾·司谷曼也認為,中國的危機大約將出現在2014—2015年左右。[2]著名的對沖基金經理吉姆·查諾斯則直言中國的硬著陸已經開始。以2001年中國入世時出版 《中國即將崩潰》而聞名的美籍華人章家敦更是堅定地認為中國經濟必然崩潰,只是時間問題。最近,他將2014年確定為中國經濟崩潰的時間點。①2011年年底,章家敦在 《外交政策》上發文,明確指出2012年中國經濟將崩潰。2013年年底,他在福布斯網站發文,第13次預測中國經濟將崩潰,并認為時間是在2014年。很多研究機構也紛紛在研究中顯示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擔心。比如,魯比尼全球經濟咨詢公司就認為,中國經濟將在2013年后硬著陸;野村國際經濟研究部也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跌至4%以下。諾頓認為,從歷史上看,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臺灣地區的發展模式類似,都經歷了超高速增長,但這種超高速發展階段基本都在25~30年內終結了,他據此得出了中國高速經濟增長階段即將結束的結論。[3]郎咸平多次在演講中提到,中國經濟已陷入全面崩潰。與此同時,國內也有學者表示了同樣的擔心。李佐軍和牛刀明確提出,中國經濟將在2013年崩潰。崩潰說的最主要依據在于對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和寬松貨幣政策的擔憂。2013年6月國內出現的 “錢荒”,更是堅定了一些人對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認識。2013年7月,克魯格曼再次指出,中國經濟碰壁,遇上了大麻煩。[4]夏斌則直言,中國已經存在事實上的金融危機現象。[5]
(2)中低速說。持此種觀點的學者根據我國人口紅利將逐步減弱和消失、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儲蓄率下降、全球化紅利衰減、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全要素生產率難有大幅度提高等因素,通過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測算認為,我國經濟已經開始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階段轉換,或者說,中國經濟進入 “換擋期”。孫學工等指出,如果按照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2011—2020年經濟增長率將比2000—2010年下降2.9個百分點。[6]蔡昉預測,中國 “十二五”和 “十三五”時期GDP的年平均潛在增長率將分別降至7.2%和6.1%。[7]祁 京 梅 指 出,未 來 一 個 時 期我國將會維持6%~8%的中速增長。[8]余斌也認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接近尾聲,未來中長期潛在增長率在下降, “十二五”期間GDP增長將保持在7%~8%。[9]
(3)5年說。劉世錦指出,人均GDP在達到11 000國際元之后,會遇到 “高收入之墻”,增速下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很有可能在2013—2017年下臺階,增速下降30%左右,由10%降低到7%左右,如果應對得當可以持續10~20年。[10]王一鳴等測算指出,2011—2015年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8%~9%,2015—2020年將下降到7%~8%。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消費市場加速、人力資本提升空間大、科技創新能力增強、城市化推進、區域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條件,從而確保中期經濟增長高速度。[11]
(4)10年說。認為到2020年我國經濟增長將轉入中低速增長階段。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發布的 《春季經濟藍皮書》認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從目前的8%~9%下降到2020年的6%~7%左右,未來可能進一步降為5%。[12]
(5)20年說。林毅夫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僅相當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韓國和1975年的中國臺灣地區。在隨后20年中,這三個經濟體保持了9.2%、7.6% 和8.3%的增速。據此,中國未來20年也完全有可能持續8%的經濟增長速度。[13]劉偉在考慮了工業化因素以后也指出,日本及 “亞洲四小龍”完成經濟高速增長時基本都完成了工業化,我們離工業化還有二十幾年的時間,所以中國經濟還有保持20多年高速持續增長的潛在機會。[14]黃泰巖認為,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都是在進入發達經濟體前后結束經濟高速增長的,我國目前工業化仍處在中后期,城鎮化剛剛跨過50%的門檻,僅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區域發展存在嚴重不平衡,這都為未來20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提供了巨大空間。[15]
(6)不確定說。這主要是因為,實際經濟增長會受到眾多可計量和不可計量的非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如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管理改善、人力資本積累、國際環境等[16],其中,重點領域改革被認為是決定未來經濟走勢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張軍指出,在當前經濟因為外部沖擊而出現減速的關鍵時刻,啟動新一輪結構改革并順勢推進人口的城市化,將是未來10年全要素生產率得以維持年均3%的增長趨勢的重要機會,未來10年GDP的潛在增長率落在大約7%~8%范圍內就可以期待了。[17]彭文生則區分了基準情形和改革情形兩種情況,認為在基準情形下,“十二五”期間潛在增長率均值為8.0%左右,“十三五”期間為6.0%左右,2020年下降到5.5%;在改革情形下,“十二五”期間均值為9.0%左右,“十三五”期間為8.0%左右,2020年下降到7.5%。[18]因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改革框架明晰之后,國內外對中國未來經濟形勢的判斷出現向樂觀轉向的跡象。比如波士頓咨詢集團的米歇爾·希爾弗斯坦基于2013年底我國公布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描繪的改革情形,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做出了積極樂觀的預測。[19]
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之所以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前景如何,不僅決定著我國的命運,而且關乎世界的未來。就我國而言,從理論上說,如能再有10~20年的高速增長,打破韓國等經濟體的30年高速增長大限,無疑將證明 “中國模式”的生命力,進一步增強我們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從實踐上說,要達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就需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經濟發展不能滑出的 “下限”,關系到“中國夢”能否實現。就世界而言,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將結束美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霸主地位,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如果中國經濟崩潰,不僅會拖累世界經濟,更重要的是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的經濟和社會動蕩,必將對全球的經濟和社會構成巨大的沖擊。這就意味著,探討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絕不是學者們在書齋里的自娛自樂,而是關乎世界命運的大問題。
對于這樣一個關乎世界命運的大問題,為什么會產生如此之大的分歧和爭論?究其原因,是因為迄今理論界還沒有一個相對比較科學完整的判斷高速經濟增長拐點的理論依據或分析框架,大家只是依據各自的評判依據得出結論,這就難免會出現 “瞎子摸象”的圖景。因此,要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做出科學的研判,就需要建立一個較為科學的理論分析框架。
本文從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濟體的經驗總結提升和驗證的視角,構建出一個包含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三位一體的判斷經濟高速增長拐點的理論假說,解析經濟高速增長的密碼,從而為回答中國經濟能否繼續高速增長,如有,還有多長時間等問題提供理論分析框架。當然,本理論分析框架僅用于解釋像中國這樣的已實現高速增長的國家是否能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以及保持多長時間的高速增長。
一、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限的理論假說
依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二元經濟,即現代工業經濟和傳統農業經濟并存。經濟發展就是現代工業經濟部門的不斷擴大,以及用現代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改造傳統農業,使農業不斷工業化、現代化,“如果資本主義擴展速度足夠快的話,那么,它遲早會包容整個經濟”[20](P68),最終使整個經濟從二元經濟走向一元經濟,即實現工業化。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在于:他揭示了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并具有巨大優勢的支撐要素,即可以無限供給的低成本農村剩余勞動力。他認為,由于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工人的工資就不由勞動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而是由工人的生存決定,即生存工資,因而可以假定工人工資不變。“工人在擴大中所得到的全部好處只是他們之中有更多的人按高于維持生計部門收入的工資水平得到就業”[21](P18)。但由于工業部門的效率高于傳統農業,即使是生存工資,也高于農業收入。這樣,隨著工業部門的發展、擴張,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工業部門轉移,成為城市市民。因此,工業化的過程也就是城市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理論的兩個驅動力。反過來說,隨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的實現,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就沒有了,當然,經濟發展的任務也就完成了。因此,他認為,當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被吸干以后,勞動力市場會發生改變,勞動力的供給低于需求,工資不變假定改變,這時工業利潤下降,投資減弱,經濟擴張停滯或者萎縮,經濟進入比較穩定的正常發展階段,工業化至此基本結束。
從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發展中國家實現高速增長時限的理論假說,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可以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結束也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基本結束,經濟進入穩定的正常發展階段。這具體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工業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只有推進工業化,現代產業在城市集聚,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形成人口在城市的集聚;人口的集聚又會對產業的發展產生需求,進一步推動產業的集聚,形成人口集聚與產業集聚的良性互動;產業和人口的雙集聚,會推動城市的發展,形成產業集聚、人口集聚和城市發展的良性循環。沒有工業化,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就會出現過度城市化,這不僅不會促進經濟增長,反而會阻礙經濟增長,沒有產業和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城市就會成為 “空城”,出現房地產泡沫,毀掉經濟增長。因此,要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工業化是最重要的。只要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城市化就將繼續,經濟的高速增長就不會結束,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工業化不僅包括完成傳統工業化,而且還要實現新型工業化。這就意味著,僅僅以人口紅利是否消失來斷定經濟高速增長是否結束,依據是不充分的,甚至可以說丟掉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核心要素或者靈魂。
第二,城市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中,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否枯竭被看做是經濟能否保持高速增長的分水嶺,這也是許多學者判斷經濟高速增長是否結束的依據。實際上,這是陷入了劉易斯理論的誤區。在劉易斯的理論中,存在著幾個錯誤的或者被忽略了的重要假定。一是劉易斯忽略了農業的發展。費景漢和拉尼斯對其進行了修正,認為只有當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時候,勞動力無限供給才會持續。也就是說,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是不斷增加的。二是劉易斯忽略了城市需要就業人口的存在。托達羅對這一理論缺陷做出了修正,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會增加過剩人口。因此,不能簡單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多少來判斷剩余勞動力的多少。三是劉易斯的工業化是假定數量的擴張,而沒有技術的變化。實際上,在工業化進程中始終伴隨著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在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更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實施自主技術創新。技術進步一方面通過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減少對過剩勞動力的吸納,相對增加過剩勞動力;另一方面,會對勞動力的質量提出要求,因而人口紅利不一定繼續表現在簡單勞動力身上,而會表現在受過一定訓練的勞動力身上,也就是人口紅利的替代。四是劉易斯將工人工資的上升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吸干聯系起來,但忽略了還有許多因素會引起工人工資的上升,比如生活成本的上升,所以,不能看到工人工資上升就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吸干了。將以上這些因素納入劉易斯的理論框架,用擴展的劉易斯理論就不會僅僅根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靜態多少,甚至僅僅根據工資上升就得出高速增長已經結束的結論。
第三,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就是實現了現代化,進入發達經濟體。一國通過推進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就是要實現現代化,立于世界強國之林。因此,理應把是否進入發達經濟體也列入判斷一國是否還能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指標。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是否進入發達經濟體這個單一指標來判斷經濟高速增長是否結束,因為一國進入發達經濟體可以有多種原因,那種脫離工業化和城市化而進入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地位是不穩固的,如利比亞就是一個人均GDP過萬美元而出現社會動蕩的國家。這就是說,必須以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三位一體來判斷一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限。
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限的國際經驗驗證
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經濟體在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入發達經濟體的過程中,都經歷了20~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年均增長率均達到9%及以上,但在高速增長之后,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都出現了下滑,大約跌至高速經濟增長時期的一半左右。這被稱為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 “30年大限”。
日本從1956年到1973年的18年間,年均增長率超過9.2%,其中有7個年份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1967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國和法國,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為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人均GDP也迅速攀升,從1956年的1 558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7 785美元。但到1974—199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降為3.8%。1990年后的21年間,年均增長率跌至0.99%。韓國從1963年到1991年近30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6%,如果剔除因為國內政治動蕩導致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的1980年①1980年,由于爆發 “光州事件”,韓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當年經濟增長率為-1.9%。,年均增長率高達10.4%。1991年韓國名義GDP達到3 150億美元,是1963年的116.7倍,人均GDP達到7 288美元,是1963年的72.9倍。1992年后的20年間,韓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速降為5.2%。我國臺灣地區從1961年到1989年近30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從17.69億美元增長到1 527.4億美元。1990年以來的20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降為5.2%。新加坡從1965年到1994年的30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2%。其中從1965年到1973年,年均增長率超過12%,名義GDP從9.742億美元增長到42.275億美元。1995年至今,新加坡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速為5.9%。
從上述經濟體高速增長的時限來看,最長沒有超過30年的,似乎 “30年大限”是成立的。但是,當我們把這些經濟體高速增長的時限與它們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聯系起來考察時則會發現,它們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在時間上與其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進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說,它們經過20~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都在高速增長結束前后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邁入了發達經濟體的行列。
從工業化來看,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韓國1965年為21.3%,處在工業化啟動階段;到1975年提高到29.3%,進入加速工業化階段;1985年達到39.1%,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1991年達到高點的42.6%,韓國的高速增長也恰好在這一年結束,與工業化的完成非常吻合。①資料來源: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整理。日本的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55年為33%,處于工業化啟動階段;到1960年提高到40%,進入加速工業化階段,并一直維持在40%左右,到1970年達到最高值44%,1971—1973年均保持在43%,然后持續下降。1973年日本高速增長結束,也與工業化的完成非常一致。②資料來源:根據日本統計局數據整理。中國臺灣的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63年達到28.1%,首次超過農業,工業化進入起飛階段[22];1975年達到39.4%,工業化加速;1980年和1981年達到最高值,均為45.3%,此后幾年一直維持在41%~44%的高位,直到1989年,才首次下降至40%以下,恰恰是在這一年臺灣地區經濟高速增長結束,同樣表現出與工業化完成的高度吻合。[23]
從城市化來看,日本城市化率從1947年的33.1%提高到1965年的68.1%,年均提高1.94個百分點,到1970年,進一步提高到72.2%。韓國的城市化快速發展期是1961年到1987年,與韓國的高速增長階段完全重合,1985年的城市化率達到77.3%。到1990年高速經濟增長階段結束時,城市化率提高到82.7%。中國臺灣地區城市化水平從20世紀50年代的24.07%上升到1978年的63.8%,80年代達到70%的水平。如果以城市化率70%為城市化完成的標志,那么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在高速經濟增長階段結束之前均完成了城市化。劉易斯通過跨國實證研究也反證了以上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經驗。他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率達到60%之前,很少有國家的人均GDP能達到1萬美元。
從現代化來看,日本1978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1973年高速增長結束;韓國1995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1991年高速增長結束;中國臺灣地區1992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1989年高速增長結束;新加坡1989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1994年高速增長結束。高速經濟增長結束的時間與其進入發達經濟體的時間基本一致。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不是因為到了30年就結束的,而是因為他們經過20~30年的高速增長最終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實現了現代化,經濟增長的空間縮小了。這一結論驗證了 “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限的理論假說”。由此看來,“30年大限”的假說就成為似是而非的結論了。
此外,我們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后的經濟增長表現還可以發現以下兩個特征:(1)即使在它們結束經濟高速增長后,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高于同期的其他經濟體。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結束后的10年間,年均增長速度雖然僅有3.6%,但仍高于同期美國的1.8%、聯幫德國的1.6%、法國的2.3%和英國的1.0%。(2)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后都進入了一個較高速經濟增長階段,而且與先期的日本相比,這個階段持續的時間更長,經濟增長速度更快。日本在該階段共持續了17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為3.8%;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分別持續19年、21年和17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5.2%、5.2%和5.9%。
三、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限假說的內在機理
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高速增長階段與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高度吻合,說明工業化、城市化對經濟高速增長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其機理就在于工業化、城市化為投資和消費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同時城市化也為工業化提供了大規模的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
(一)工業化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機理
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推進工業化高速增長的階段,投資是重要的拉動力。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表現出明顯的投資主導特征。日本在1956—1964年圍繞重化工業化進行了大規模的設備投資和設備更新,相繼出現了“神武景氣”(1956—1957)和 “巖戶景氣”(1959—1961)兩次經濟發展高峰。1956年,日本的私人設備投資比1955年猛增54.6%,投資的70%集中在鋼鐵、機械、電力、化學等行業,使日本很快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重化工業體系,體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和工業化對投資的巨大推動作用。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日本耐用消費品逐漸普及的時期,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日本大量投資于電機、電子、汽車、合成纖維、合成樹脂、石油化學等新興工業部門,這些行業的快速發展反過來又帶動了為其提供機器設備和原料的機械、鋼鐵等基礎工業部門的投資。日本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在高速增長時期不斷提高,1961年超過30%,到1973年高速增長結束時,達到歷史最高,為36.4%,呈現出與高速增長階段的同步性。韓國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也是通過大規模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尤其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 “三五”(1972—1976)、“四五”(1977—1981)兩個五年計劃為中心,韓國實施“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加大對造船、鋼鐵、汽車、電子、石化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投資,這對當時韓國經濟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中國臺灣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推行了以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為標志的十個重大項目建設,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巨大動力。
上述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將投資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化工業的做法表明,重化工業的發展需要更大規模的投資,從而能夠帶動更快的經濟增長。韓國從20世紀70年代提出發展重化工業,到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大約有20年的高速增長期。日本從1963年開始重化工業化,到1973年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也有10年的發展期,占日本高速增長階段的一半時間。投資重化工業之所以能夠帶來較快的經濟增長,是因為重化工業具有產業鏈長、附加值大、技術含量高、消費升級周期長等產業特點。實際上,英國、法國、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在其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也都高于輕工業發展階段。根據霍夫曼、張培剛、鹽谷佑一、錢納里和泰勒等實證分析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產業演進的一般規律,重化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階段,就是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這就意味著:一國完成了重化工業化,也就實現了工業化,從而也標志著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
(二)城市化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機理
城市化推動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實現高速增長的機理在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一是為工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二是勞動力的低廉提高了企業利潤,為吸引大規模投資創造了條件。
韓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963年高達63.1%,1970年開始實施新村運動,1975年下降到37.1%,1985年下降到20.1%,向城市轉移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這個時期韓國的失業率也大幅降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韓國勞動力年均增長速度為3.2%,但失業率卻從1962年的8.2%峰值逐步下降到了1975年的4.1%。[24]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為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 “人口紅利”。
與其他國家相比,此間韓國工人的工資水平保持在較低水平。據統計,1964—1970年韓國的工業日工資水平,最低時為0.48美元,最高時也只有1.24美元。這一水平不僅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半導體工業為例,1970年美國工資是韓國的10.2倍,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的工資水平則是韓國的1.2倍。[25]
(三)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機理
城市化的進程,就是產業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過程,產業的集聚會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從而促進產業投資和進一步的產業集聚。產業的集聚會帶來人口的集聚,產業和人口的雙集聚就會帶來城市數量的增加和不同等級城市規模的擴大,從而帶動城市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這都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日本在城市化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國45%的人口和55%的工業生產,目前進一步提高到約2/3的全國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70%。韓國僅有4 800萬人口,但卻發展出277座城市,其中有7座城市的人口超過100萬人。首爾1960年城市化加速初期人口僅有200萬人,1970年達到400萬人,1980年超過800萬人,到1990年高速經濟增長階段結束時,人口已超過1 000萬人。目前首爾地區的人口占韓國總人口的50%以上,對持續GDP的貢獻率高達24%。
四、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限假說的中國價值
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經驗,我們可以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圖景做出如下描繪:
(一)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期還應持續20年左右,再創世界經濟發展的 “奇跡”
既然經濟高速增長的持續時間與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完成時間高度相關,那么按照世界銀行2011年的國家發展水平分類標準,我國2011年人均GDP為5 400美元,處在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按照世界銀行在 《2030年的中國》一書中的預測:中國有潛力到2030年成為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按此預測,我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入高收入社會大約還需要20年的時間。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也就是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根據有關測算,我國目前的工業化大約完成60%以上。按照發展規劃,到2020年才基本實現工業化。我國城市化率2011年為51.27%,這是按城鎮常住人口的統計,如果剔除在城鎮居住和工作但沒有城鎮戶口的農民工,城市化率還不到40%。按照發展規劃,我國到2030年城市化率將達到70%,即使按此計算,我國仍有4億人口在農村。根據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相對發展進程來看,兩者相差約10個百分點,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所以,未來10~20年,城市化將是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從三位一體的判斷依據來看,我國還應有潛力再來近20年的快速增長。如果再來20年的快速增長,我國就可以創造出無論是在高速增長持續時間上還是在國家類型上全面的世界經濟發展的 “奇跡”。
而且,根據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經濟發展的經驗,在結束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后,還將進入一個次高速經濟增長階段。所謂次高速經濟增長階段,是相對于高速增長階段而言的,如果相對于同時期的其他經濟體而言,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中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這個階段還要持續大約20年的時間。這就意味著:一個經濟體完成高速增長階段后,在不發生大的政治、軍事等突發事件的情況下,該經濟體的經濟突然減速甚至陷入崩潰是不現實的。依據這一歷史經驗,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趨勢就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斷:在保證社會政治穩定和不發生與他國大規模軍事沖突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還將快速發展,不可能崩潰!
(二)城市化將繼續創造 “人口紅利”,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和活力
加快推進城市化,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質量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繼續貢獻 “人口紅利”。國家統計局2012年統計公報顯示: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首次下降,但僅減少了345萬人,占總勞動人口93 727萬人很低的比例,而且這種下降趨勢到2030年前都是逐步的,這意味著我國人口紅利即使出現減少,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完全可以保證再有20年的高速增長。更應看到的是: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對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力將有越來越大的需求。我國現在每年有近700多萬大學生畢業,2013年內地大學生畢業人數達到699萬人的歷史最高水平,在學研究生172萬人。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的人力資本紅利開始出現增長,而且未來增長得會更快。人力資本紅利的增長,將為我國的經濟轉型,從而通過轉型促進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動力和活力。
(三)城市化將帶動投資和消費快速增長,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空間
基本實現城市化,我國至少將有3億~4億人口進入城市,這將對城市住房和城市基礎設施產生巨大的需求。同時,城市化也會因收入增長和商品化率提高而帶來居民消費的增長。根據馬曉河的測算,假定到2020年城市化率達到60%,將會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投資約20萬億元,增加消費5.3萬億元。[26]25.3萬億元的投資和消費將保持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有報告甚至認為,城鎮化將在未來10年拉動40萬億元的投資。[27]
(四)人口的集聚將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并推動中國經濟轉型
2008年,我國擁有地級及以上城市287座,但其中人口超過200萬人的城市僅有41座,人口集聚程度較低。因此,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將主要不是表現為城市數量的增多,而是既有城市規模的擴大。據預測,2025年,99座新城市有望躋身全世界最大600座城市行列,其中72座來自中國。[28]另據麥肯錫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經濟結構改變最明顯的證明將是城市的繁榮,尤其是目前人口少于150萬人的中小城市,它們將為中國城市貢獻40%的GDP。人口的集聚,不僅會促進中國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轉變,而且將有力地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馬曉河的研究發現:第三產業就業比率對城鎮化率的彈性為1.13,這意味著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三產業就業比率以遞增的速度增加。[29]
(五)人口的集聚要求產業的集聚,而產業的集聚將提高經濟的效率
與人口的集聚度不高相對應,我國的產業集聚度也較低,目前在全國GDP總量中,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經濟圈的貢獻還不到40%,與日本三大經濟圈70%和美國三大經濟圈68%的水平有很大差距。按照工業化和城市化相互促進的基本規律,我國的城市化必須以工業化為基礎和前提,因而人口的集聚必然要求產業的集聚。根據麥肯錫的預測,中國城市GDP占全國GDP的比重將由目前的75%增加到2025年的95%。這意味著產業越來越向城市集聚。產業在向城市集聚的過程中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向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集聚。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形成了三大經濟圈。有人考察了美國1900—1990年期間城市的變化,發現在此期間出現的新城市,如果鄰近其他城市,則發展較快,而且與相鄰城市的增長率緊密依存。二是產業的集聚有助于提高經濟效率。《1984年世界發展報告》認為,城鎮只有達到15萬人的規模才會出現集聚效益。著名城市經濟學家弗農·亨德森認為,如果中國一些地級城市的規模擴大1倍,可以使其單位勞動力的實際產出增長20%~35%。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這就要求產業將向幾大經濟圈集聚,并隨著產業的集聚,人口也將隨之集聚,形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最終打造出若干個經濟增長極,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1]Paul Krugman.“Will China Break?”.The New York Times,2011-12-18.
[2]Michael Schuman.“Why China will Have an Economic Crisis”.Time,2012-02-27.
[3]張軍:《鄧小平是對的: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載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
[4]Paul Krugman.“Hitting China's Wall?”.The New York Times,2013-01-18.
[5]夏斌:《當前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載 《京華時報》,2013-07-15。
[6][16]孫學工、劉雪燕:《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分析》,載 《經濟日報》,2011-12-12。
[7]《專家:2013年中國人口紅利或將消失 第二次人口紅利可能再來》,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824/c1001-18820528.html。
[8]祁京梅:《中國經濟發展新趨勢》,載 《中國金融》,2013(15)。
[9]《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載 《中國經濟時報》,2011-11-29。
[10]劉世錦、張軍擴、侯永志、劉培林:《陷阱還是高墻:中國經濟面臨的真實挑戰與戰略選擇》,載 《比較》,2011 (3)。
[11]《中國經濟告別兩位數增長了嗎?》,載 《人民日報》,2011-11-21。
[12]《中國社科院春季經濟藍皮書: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載 《21世紀經濟報道》,2012-04-25。
[13]林毅夫:《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http://www.ftchinese.com/story/1001052200?full=y。
[14]楊靜:《中國經濟增長能持續多少年——訪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劉偉》,載 《國際融資》,2008(1)。
[15]黃泰巖:《中國經濟還能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長嗎?》,載 《中國能源報》,2012-12-10。
[17]張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載 《深圳商報》,2013-11-04。
[18]彭文生:《中國經濟:改革驅動下的長周期》,載 《21世紀經濟報道》,2012-02-25。
[19]Michael J.Silverstein.“Ten Predictions for China's Economy in 2014”.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log Network,2013-11-21.
[20][21]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2]樓勇、閻桂蘭:《臺灣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載 《海峽科技與產業》,2013(8)。
[23]彭百崇:《臺灣經濟轉型與就業 M型化問題》,載 《臺灣勞工》,1997(13)。
[24]徐建平:《韓國的勞務市場》,載 《國際經濟合作》,1999(3)。
[25]張玉柯、馬文秀:《比較優勢原理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載 《太平洋學報》,2001(1)。
[26][29]馬曉河:《積極推進城鎮化釋放內需潛力》,載 《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報告 (2012)》(討論稿)。
[27]《“城鎮化”或將未來十年拉動40萬億投資》,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1226/c1004-20016174.html。
[28]《美媒:2005年全球最具活力城市四成在中國》,載 《環球時報》,2012-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