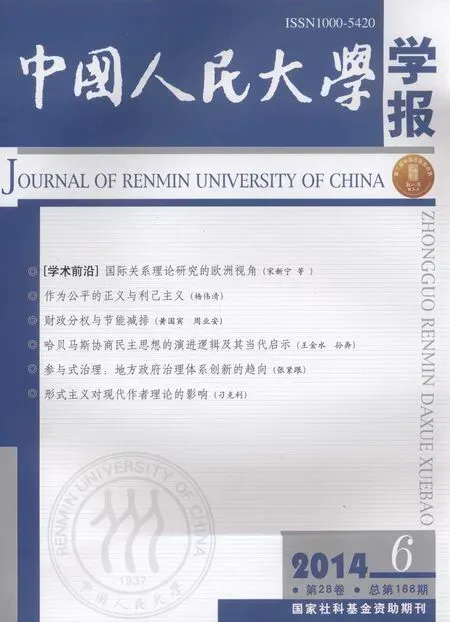理解自由的第三條道路
——論伯林的自由觀及其人性論基礎
賈麗民 孔 揚
理解自由的第三條道路
——論伯林的自由觀及其人性論基礎
賈麗民 孔 揚
伯林在后形而上學的視域中堅持對個人自由的捍衛。在他看來,自由即“消極的自由”而非積極的自由,也叫“政治的自由”,指一個人能夠不被別人阻礙行動的領域。伯林在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實現了辯證的融合,他拋棄了理性主義的決定論及一元論邏輯而繼承了其客觀性的思想(即承認自由的價值),拋棄了浪漫主義的唯意志論而繼承了其多元主義的積極遺產,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理解自由的第三條道路。
伯林;消極自由;浪漫主義;價值多元論
伴隨著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壟斷及世界化不同時期的發展,西方自由主義也經歷了古典、現代、冷戰和20世紀末幾個階段,但根據理論范式的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普遍主義范式和相對主義范式兩個總體階段。前者的思想基礎是古典理性主義,其主題在于探討市民社會中公共契約條件下的個人自由問題;后者的思想基礎是后現代主義,其主題在于探討資本同一性全面統御下的個人自由問題。伯林作為20世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對自由的理解既不同于康德、黑格爾等傳統理性主義思想家,也不同于羅蒂、福柯等后現代主義思想家。而是基于對人的偶然性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在自由問題上提供了一條既沒有陷入普遍主義、也避免了相對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他認為現實的自由即是“消極自由”,因為它回答了這個問題:“主體(一個人或人的群體)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愿意成為的人的那個領域是什么?”[1](P189)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對社會團結、穩定、共識的探討與論證都沒有超出伯林的理論關注,并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其展開對話。
一、從積極自由到消極自由:伯林在自由觀領域的哥白尼倒轉
在伯林看來,所有政治哲學家遲早都會提到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從別人?”[2](P56)這個問題又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兩個問題,即“我被誰統治”和“我被統治到何種程度”,前者是積極自由的問題,而后者是消極自由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看似差別不大,但在對答案的追問過程中,二者則顯示出了根本的對立。伯林正是在對積極自由內在本質的揭露和批判過程中,建立起了對消極自由的肯定,從而實現了自由觀領域的哥白尼倒轉。
在自由主義傳統觀念中,積極自由通過與形而上學的聯姻,獲得了大多數政治哲學家的肯定。經形而上學架構,人被劃分為經驗自我和理性自我(或真實自我),由于與世界本質直接相關,理性自我便成為自由的化身,自由就體現在真實自我對經驗自我的支配上。真實自我因洞察世界模式、掌握宇宙真理,因而擁有話語霸權,而個人或民族成員因受制于欲望或激情對真理一無所知,所以自由存在于真實自我對經驗自我的統治之中。并且,這個真實自我總是超越個體,化身為“國家”、“民族”、“階級”等實體,使自由學說逐漸演變成權威學說。由此,積極自由的“我被誰統治”的“誰”,顯然不可能是感性經驗的“我”,也不可能是外在的自然,而只能是理性的自我。在某種語境中,理性的自我與最高存在者的上帝是內在同一的。正是在形而上學的“自我”框架內,積極自由漠視現實個人的經驗性存在,導致自由走向其反面,這在歷史上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在伯林看來,近代的大多數集權主義統治者都利用了這套邏輯,因而積極自由往往成為奴役的代名詞。
在積極自由的理論視域中,人的選擇、動機等主觀性因素都是錯誤的根源,而伯林認為對于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把他們僅僅當做客體而不是其動機、觀點、意圖都具有內在價值的主體(通過摧毀他們擁有相關的觀點與觀念的可能性)——這乃是對人類選擇的可能性的否定,因而是根本無法忍受的”[3](P387)。因此,自由并不體現為對“模式”的服從,而是體現為康德所說的“選擇”,選擇意味著機會的多樣性,意味著“有多扇門對人是敞開的”,這就是所謂的“消極自由”。消極自由又稱為政治自由。“就沒有人或人的群體干涉我的活動而言,我是自由的。在這個意義上,政治自由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人能夠不被別人阻礙地行動的領域。”[4](P189)就政治是一個沖突與對抗的領域而言,伯林提出了一個傳統自由主義者未曾觸及的問題:在政治社會中,人們并非僅僅在善與惡之間進行選擇,而是更為根本性的在善與善之間進行抉擇。消極自由“關注的焦點不是‘善’與‘善’之間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約性”[5]。因為“好的事物”與“好的事物”之間可能存在著難以避免的沖突,如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內在矛盾。正是由于善的多樣性、不可通約性,消極自由才成為現實生活中的真正自由,其所蘊含的“選擇”才成為不可避免地帶有缺憾性和悲劇色彩的真實生活境況。基于此,伯林強調他關注的是政治自由而非精神的自由。因為自由(無論是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的首要特征是障礙之不存在,但通過否定人的現實需要而“退居內線的城堡”,即通過否定人的欲望使障礙失去對人的影響從而獲得的精神自由,并不是政治自由,而只是幸福或安寧。在實踐中,這種精神的自由有可能成為集權統治的根源,使人們失去生活的“現實感”。
伯林認為政治自由具有兩個根本特征:第一,自由是指個體行動的機會,而不是行動本身;第二,自由自身具有最高的價值而不能為其他東西所取代。所謂行動的機會,指的是沒有他人的故意干涉而能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動,這與純粹的沒有能力達到某種目標是不同的。伯林認為需要將二者區分開來。由于身體的缺陷或社會地位的低下而不能自由地去行動或實現自己的目標,并不能說個體缺乏政治自由,只能說缺少實現自由的條件。只有存在“人為”或“故意”的外在干涉,才能被稱為自由的缺乏。或許對乞丐來說,告訴他們有購買面包的自由無疑是對他們的嘲諷,但如果因此否定他們的自由,就將使特權者的統治合法化。因此,政治自由與自由實現條件之間是不能等同的,政治自由只與他人的故意相關。所謂自由的最高價值,是指政治自由或者說自己的領地即使再小也能自己做主,且不能以幸福、和平等名義而犧牲自己的自由。伯林指出:“自由之所失也許會為公正、幸福或和平之所得所補償,但是失去的仍舊失去了;說雖然我的‘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有可能失去,但某種其他的自由(‘社會的’或‘經濟的’)有可能增加,這是混淆了價值。”[6](P193)
當伯林將個人的消極自由作為最高價值的時候,他同時否認了自由與真理、正義等的內在一致性,因為這種觀念不過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烏托邦信念。伯林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各種終極價值多元同時又常常互不相容的世界中,這些互不相容的價值會發生不可避免的沖突,而我們又找不到一條普遍適用的標準來仲裁這些沖突,因為這些價值之間常常是不可公度(不可通約)、不可比較的。面對此種情形,自己必須進行選擇,并承擔自己自由選擇的后果。如果有人宣稱,他可以或已經找到一個唯一合理的解決價值沖突的答案,因而他也有權替別人進行選擇,那就根本不符合價值世界的本來面目,并且也剝奪了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7]由此看出,伯林的出發點始終是現實生活中的個人,一個不必聽命于任何外在“他者”的個體。
二、個體自由基于偶然性:伯林自由觀的人性論基礎
綜觀伯林的自由主義思想,最為關鍵的就是其人性論基礎,這恰好又是伯林未曾言明且最易被人誤解的地方。伯林的人性論與傳統的本質主義人性論有著重大區別,他“在對西方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假設或前提的批判過程中,提出了自己關于人的本質概念”[8]。他認為,真實存在的人永遠都是個體的、現實的人,而不是某種特定的本質或理性,后者只是形而上學的虛構。可以說,伯林對人性的這樣一種經驗主義的、個體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20世紀哲學思潮的基本理論訴求,無論是存在主義的“此在”、后哲學文化的“偶然性存在”,還是后現代主義的“邊緣”、“他者”的存在,無一不是以一種隱晦的方式為個體性的人的存在正名。正是在這種人性論基礎上,伯林大膽而充滿自信地向世界闡述其自由學說。
伯林指出,在談論個體自由之前必須追問一個問題:決定論是否正確?如果決定論正確,即無論是歷史還是個人都先天地被決定,那么個人自由就是無知的表現,個人的選擇就是一個幻象,道德評價也就顯得空洞而成為單純的“美學判斷”。但他認為決定論在理論和現實上都難以自圓其說:第一,因為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聲稱發現了歷史和人類發展的必然規律,但實際上它們很少能夠進行準確的“預測”,而且對于支撐決定論得以可能的力量、客觀規律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第二,如果決定論成立,我們的人生態度、世界觀及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道德詞匯都將發生根本的變化,由此,我們將失去理解自身及世界的能力。伯林得出結論:人的存在是偶然的,不是被決定的,而對偶然的承認正是自由得以可能的前提。“20世紀的重要哲學家們紛紛追隨浪漫主義詩人,試圖跟柏拉圖決裂,而認為自由就是承認偶然。這些哲學家都企圖把黑格爾對歷史性的堅持,從他的泛神主義觀念論中解脫出來……更普遍地來說,他們都極力避免哲學中冥想的氣味,避免哲學中把生命視為固定不變、視為整體的企圖。他們如此做,都是因為他們堅持個體存在的純粹的偶然性。”[9](P41)啟蒙大師康德雖然認為人不是一個完全由必然性統治的存在者,但人之為人在于人的普遍性,即人具有普遍的立法能力或者稱為自由,這與伯林對個體偶然性的強調南轅北轍。如果說在康德那里,自由是指意志的自我立法,而這種立法的真實性在于可普遍化;那么在伯林這里,自由則剛好相反,指的是個體的特殊性選擇。伯林對傳統的“揚棄”,正是“哲學的思維方式——反思”[10]的本質性體現。
“在本體論上拒絕一元論、堅持多元論是伯林哲學的邏輯結論。”[11]也正是基于人的偶然性存在的“本體論承諾”,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和對消極自由的強調才是合理的。他將偶然性“贊頌為道德自由的基石”[12](P26)。很顯然,這里的偶然不是任意的意思,否則就會陷入價值虛無主義,社會共同體就會瓦解。在“消極”的意義上說,伯林的偶然僅僅是一元主義的對立面——多元主義。由此,他開啟了當代哲學難以回避的核心問題:到底什么才是自由?個體性的消極自由到底是什么?它會導致什么后果?而消極自由或政治自由最為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個“界限”問題,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自主程度到底在哪里。這又涉及兩個問題:個體與國家之間的界限;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界限。
在個體與國家之間,由于伯林確立起了個體存在的最高價值,也就是確立起了個人權利的最高價值,因而國家以任何理由未經個人的同意而加以干涉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在伯林看來,人并不是一個原子式的存在者,而是一個文化的存在者,或者按照羅蒂的說法“人是一個由信念和愿望構成的無中心的網絡”[13](P178),因而個人對何謂善的判斷有著最終的依據。伯林認為,國家和政府并不比個人對何謂真理和善有著更好的判斷,阻止個體去選擇(即使后果證明為錯的道路)相比于讓個體去進行錯誤選擇,前者更令人感到痛恨。對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權利界限,伯林主要考察的是“教育”的合理性,即父母是否有權利“奴役”自己的子女,為其做出決定。如果說通過考察政府和個體之間的權利界限,伯林指出了權利或政治自由的通則,那么通過父子關系的權界思考,伯林指出了政治自由的例外。在伯林那里,“自由只能因自由的原因而被限制”。在西方思想史語境中,父子關系的隱喻一直被用來闡釋理性統治的合理性。但用這種關系來闡釋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則是十足的誤用。因為它建立在對自由的否定基礎上,而且父母對子女進行限制是一種必要的惡,即為了更好地實現子女未來的自由而做出了替代性選擇。“所有的‘捏制’都是邪惡的,如果人類天生擁有選擇能力與理解世界的手段,這樣做便是一種犯罪;既然他們沒有,我們只是暫時地奴役他們,因為我們擔心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會遭受來自自然與人類的更壞的命運,而這種‘暫時的奴役’在他們終于能夠自己做出選擇之前,便是必要的邪惡——‘奴役’的目的絕非反復灌輸服從,而是其反面,即發展自由判斷與選擇的能力;然而,如果必要,邪惡應得到保留。”[14](P389)
伯林認為,對于作為個體的人來說,自由選擇之所以有意義,并不是因為他選擇什么目標,而在于選擇本身,即由于是“我”自主做出的選擇,便是有意義的。而“我”顯然與康德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自我”決然相反,因為他的真實性在于自身存在的偶然性。因此,伯林的“我”既不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理性“我”,也不是純感性的“我”,而是一種現實的個體性的“我”,一種不可還原和規約于他者的個體性的存在者。這就是伯林人性論的核心所在。
三、包含矛盾的偏正結構:伯林自由觀對浪漫主義與理性主義的融合
伯林的消極自由立足于人的偶然性存在,這種理解繼承了與啟蒙世界觀對立的浪漫主義思想傳統。在他看來,傳統的啟蒙思想家大多持一元論邏輯,而一元論又與決定論密切相關,結果只能是消極自由的反面——積極自由導致的自由喪失。一元論的邏輯蘊含三個基本假設:“人們的核心問題,最終來看,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原則上,是可以解決的;結果就將是一個和諧的整體。”[15](P213)這個和諧的整體是一個絕對完美的烏托邦,是將所有好的東西(如真、善、美)結合在一起的理想國。但浪漫主義則對此做出了一個根本的顛倒,他們指出了人們不愿意面對的事實:價值之間不僅不相容,而且是相互對立和沖突的,因而人們不得不在多元且對立的價值之間進行選擇。伯林接受了浪漫主義的這種價值觀,但他的目的卻與浪漫主義完全不同,他是為了闡釋價值多元的事實而避免一元主義邏輯對消極自由的抹殺,而后者則證明人的價值在于自由創造。
傳統的一元主義邏輯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純粹的“事實”性存在,認為“美德”就是去探尋和發現“知識”。在這種邏輯的驅使下,理性主義將人推舉到“理性動物”的高度,實際上就是將知識看成人的本質。然而,正如康德所言,自由高于必然,道德高于知識,且二者之間并不是程度的差別而是質的差別。由此,人之為人的本質并不在于人的理性或知識(這只是必然性的領域),而在于自由意志,這才是人與其他存在者區別開來的根本性標志。為進一步澄清問題,伯林分析了浪漫主義的兩個基本特質:(1)“‘不屈的意志’的觀念:人們所要獲得的不是關于價值的知識,而是價值的創造……這個觀點的核心在于,在某種程度上,畢竟世界出自你的選擇、你的創造”;(2)“認為世界上并不存在事物的結構,不存在一個你必須適應的模式。只有一樣,那就是世界是永無止境的自我創新。”[16](P120)在此基礎上,他強調價值個體性(即真實的價值源自于自己的創造)的本真存在,承認價值多元論的事實。顯然,伯林以個體存在的“第一性”為基點,拋開普遍的、絕對的、終極的標準限制,肯定個體創造或選擇的價值所具有的根本性意義,為根治理性主義的痼疾提供了一個良方。
雖然伯林肯定價值的多元化存在,但與價值相對主義極力強調價值之間差異的做法不同,他并不認為每一種價值都是合理的。在他看來,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著一些作為行為判斷標準的最低“原則”,否則人的某些行為將變得不可理解,或者超出“人之為人的范圍”。“我們相信如下事實:當我們做出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的判斷時所訴諸的那些法則和原理,至少在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上,已經被大多數人接受……那些法則和原理,在我們看來,是不能被廢除的……對待它們,我們不是當做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祖先隨意選擇的東西,而是在根本上視為人之為人的前提條件,是與他人共存于一個共同的世界的前提,是識別同類、同時也是識別自身的前提。”[17](P206)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雖然存在著巨大差別,價值盡管是多元且不可公度的,但并不是任何價值和信念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人的直覺會告訴我們某些行為是非道德的。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伯林首先肯定了自由的重要性,這是他價值多元主義(而非相對主義)所暗含的一個標準,但這個自由是沒有形而上學基礎或者無需康德意義上的“自我”支撐的自由。可以看出,伯林雖然承認現實生活中人們面臨價值沖突,但他并沒有得出悲觀的結論,即人類社會是一個充滿敵意與戰爭的場所,畢竟在具體的情景中通過妥協與寬容總能就某些問題達成一致。在此意義上,伯林又使自己區別于激進的浪漫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
實際上,伯林在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實現了辯證的融合,他拋棄了理性主義的決定論及一元論邏輯而繼承了其客觀性思想(即承認自由的價值),拋棄了浪漫主義的唯意志論而繼承了其多元主義的積極遺產。不過,他的浪漫主義傾向比較明顯,因為他總是將啟蒙的理性主義等同于專制主義,并認為浪漫主義動搖了西方兩千多年的傳統。“浪漫主義主張價值多元論,反啟蒙理性的普遍主義,給予了專制制度的文化以致命打擊。有一次,伯林對傳媒說:‘浪漫主義運動帶給我們的多樣與變化,是新的典范’,‘要用高壓手段掃除異己分子,恐怕沒那么容易了’。”[18](P6364)也就是說,在伯林看來,浪漫主義所主張的價值多元論沖擊了一元主義,使人真正獲得了獨立性。但問題在于,理性主義真的就與專制主義等同嗎?浪漫主義真的能夠為啟蒙把脈嗎?對此,伯林顯然是低估了理性主義并誤讀了啟蒙。
伯林的價值多元論和對消極自由的捍衛明顯包含諸多矛盾。立足價值多元論,價值是多元且不可公度的,每一種價值都不能聲稱高于其他價值,然而,伯林捍衛消極自由、承認消極自由的首要性,豈不剛好是價值多元論的反面?另外,一方面,他認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總是在多元價值中進行取舍,并且一種價值的實現難免要以犧牲其他價值為基礎;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面對此種狀況我們需要進行選擇(或者抉擇),從而賦予消極自由以自由的真實內容。這樣,伯林將浪漫主義的革命性變革歸結為將事實與價值區分開的同時,又從“不得不如此”的事實推出了“應當進行選擇”的價值。這些矛盾表征著伯林思想中的內在困境,但必須看到:伯林的難題,即價值多元論所蘊含的社會團結的喪失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價值沖突,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后形而上學時代的現實問題。羅蒂以“同情心”、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羅爾斯以“公共理性”來解決這個難題。然而,無論他們的解決方法在理論上如何可行并具有合理性,恐怕在伯林看來都不可避免地蘊含某種形而上學的承諾,即對統一、一致的渴望,這無疑會導致集權主義與人的(消極)自由的喪失。在伯林眼中,既然價值之間的不可公度或沖突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現實,那么選擇就是人類的必然命運,而選擇必然是不完美的,選擇一種價值意味著放棄另一種價值。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都是“善”,但二者并不是一致統一,而是相互沖突的。如果要求個體自由,那么社會團結就很難保證,而這正是個體自由的必然代價與人類生活的必然命運。
綜上,伯林從偶然性出發來理解人性,對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辯證融合,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理解自由的第三條道路。與此同時,其價值多元論的思想顯然傾向于浪漫主義,并且“這種自由主義理念也同其他自由主義一樣,潛含著抽象的形而上‘自我觀’,它總是撇開具體的社會關系與歷史條件去探討人的自由問題”[19]。這就意味著他對自由的理解又存在著內在的思想裂痕。不過,這種裂痕并不全然是思想家個人的邏輯混亂使然,毋寧說是復雜的現實境遇向當代人類的智力提出了深沉難解的課題。因此,伯林思想的獨創性與矛盾性,都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
[1][3][4][6][14] 以賽亞·伯林:《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2] 以賽亞·伯林:《自由及其背叛》,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5][11] 張國清:《在善與善之間:伯林的價值多元論難題及其批判》,載《哲學研究》,2004(7)。
[7] 馬德普:《價值多元論與自由主義》,載《政治學研究》,2012(3)。
[8] 郝立新:《伊賽爾·伯林與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載《哲學動態》,1998(1)。
[9] 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0] 賈麗民:《反思達致真理》,載《學習與實踐》,2013(4)。
[12] 馬克·里拉、羅納德·德沃金、羅伯特·西爾維斯編:《以賽亞·伯林的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3] 理查德·羅蒂:《后哲學文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15][17] 以賽亞·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16] 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18] 劉小楓:《施特勞斯的路標》,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19] 張文喜:《自我的幻像——對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的批評》,載《東南學術》,2002(3)。
The Third Way of Understanding Freedom——On Berlin's Idea of Freedom and Human Nature Theory Basis
JIA Li-min1,KONG Yang2
(1.School of Marxism,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 2.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ir Force Aviatio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22)
Berlin persisted in defending individual freedom from the horizon of post-metaphysics.In his view,freedom is Negative Freedom rather than Positive Freedom.Freedom,which is also called political freedom,refers to a state of being allowed to behave without obstruction.Berlin combined romanticism and rationalism dialectically.Discarding determinism and Monism logic of rationalism,he inherited its objective ideas which acknowledge the value of freedom.Discarding romanticism's voluntarism, Berlin inherited its pluralism.All these provide the third way to understand Freedom.
Berlin;negative freedom;romanticism;value-pluralism
賈麗民:哲學博士,哈爾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黑龍江哈爾濱150080);孔揚:哲學博士,空軍航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吉林長春130022)
(責任編輯 李 理)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馬克思資本雙重性思想及當代價值研究”(14BZX01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資本邏輯批判及當代價值研究”(13 YJC7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