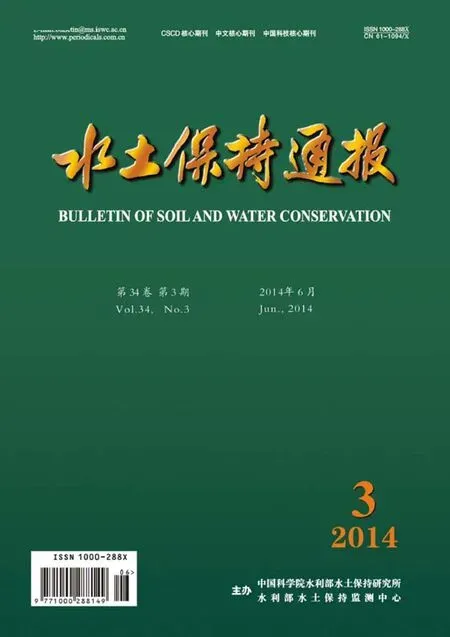新疆策勒縣新開墾農田地表蝕積變化
毛東雷,雷加強,龐營軍,王 翠,周 杰,再努拉·熱和木吐拉
(1.中國科學院 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新疆 烏魯木齊830011;2.新疆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830054;3.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100049;4.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新疆 策勒848300;5.中國科學院 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甘肅 蘭州730000)
土壤風蝕是導致環境惡化與土地生產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干旱半干旱區的防護林體系是用以改善沙區生產生活環境、農田小氣候,防止地表風蝕及其對農作物生長的危害的生態林分[1]。在干旱半干旱風沙區,綠洲外圍的天然和人工防護林的主要功能是防風阻沙,減少風蝕,為綠洲的生態安全提供保護屏障。
據測算,中國沙區因風蝕沙化每年損失土壤有機質、氮素和磷素高達5.598×107t,西北地區許多農田因風沙毀種,“三刮四種”現象十分嚴重[2]。植被覆蓋在風蝕過程中可通過多種途徑對地表土壤形成保護,減少風蝕輸沙量[3-4]。幼苗極易被風沙擊打受傷而影響正常生長以至死亡,有些地塊常因風蝕被迫改種或重播,甚至屢種屢敗,造成絕產[5]。
針對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西南緣和田地區嚴重的風沙危害和近年來綠洲—沙漠過渡帶的沙地被大面積墾荒等問題,選擇策勒縣開墾年限分別為1和2a的農田進行野外地表蝕積變化試驗觀測,為綠洲—沙漠過渡帶自然植被的恢復和防止新開墾農田地地表遭受嚴重風蝕,保護綠洲農業生態安全提供理論依據和支撐。
1 研究區概況
策勒縣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與昆侖山北麓之間,地理坐標為80°03′24″—82°10′34″E,35°17′55″—39°30′00″N,屬典型內陸暖溫帶荒漠氣候,夏季炎熱,干旱少雨,光熱充足,日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極端最高氣溫41.9℃,極端最低氣溫-23.9℃。多年平均降水量35.1mm,年潛在蒸發量2 600mm。
由于地處塔里木盆地兩大主導風向(NW,NE)的下風區域,風沙災害頻繁,多年平均沙塵日數25.2d,最多年高達59d,每年8級以上大風3~9次[6]。研究區風向以 WNW,W 風為主,頻率占62.43%~76.25%,NW 風次之,占17.75%[7],和田地區由于絕大部分綠洲邊緣都與大沙漠接壤,風沙災害極為嚴重[8]。風沙災害天氣嚴重制約著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隨著綠洲—沙漠過渡帶大面積的墾荒種植,在春夏大風頻發季節,許多新種植的防護林和農田幼苗被連根拔起,造成了嚴重的地表土壤風蝕和農業經濟損失。
2 野外試驗設計及研究方法
2010年5—10月選取策勒縣熱瓦克開墾年限2a的紅棗農田采用插釬法觀測地表蝕積變化,同時用小氣象站觀測氣象數據,觀測指標有風速、風向等,風速觀測高度為0.5,1,3m。
農田內自西向東分布有3條新疆楊防護林帶,每條防護林帶內株行距為1m×1m,每條帶種植5行,平均樹高3.1m,疏透度50%~60%。農田外圍西側為天然過渡帶荒漠區,防護林布置方向為南北向,基本垂直于年主風向。
自西向東在3個防護林內小網格農田地表進行插釬,紅棗平均高40~50cm,株行距1m×2m,風蝕釬都插在2行紅棗行的中間。最西面的田埂距第一道防護林54m,田埂堆積干駱駝刺和鹽生草等枝條并埋上沙土,第1個網格內插2道每道27根風蝕釬;中部第2個網格內防護林間距112m,內插3道每道56根風蝕釬。
小麥行寬10cm,高約5~15cm,與紅棗根部間距10cm,風蝕釬布置選擇中區的中間的紅棗、小麥行,自兩行紅棗的中間開始,然后自西向東每隔20cm插1根風蝕釬,小麥行前后每隔5cm插1根風蝕釬,每道選擇5行紅棗樹插30根風蝕釬,取3個重復共90根風蝕釬,每相鄰兩列間隔為50cm。東面第3個網格內防護林帶間距54m,內插有3道每道27根風蝕釬,西區、中區、東區每相鄰兩道風蝕釬間距都為2m,插釬時地表地勢較為平坦規整。
2012年5—10月選取當年新開墾未種植裸沙地和不同蓋度的自然過渡帶下墊面,采用插釬法觀測地表蝕積變化,選取5個輸沙階段進行同步觀測。地表安裝有HOBO小氣象站,觀測指標有風速、風向等項目。風杯安裝高度分為4層:0.5,1,2,3m,所有氣象數據1s自動記錄1次,間隔1min采集1次。
所有氣象數據及地表蝕積變化數據采用Excel 2003,Surfer 8.0等軟件分析并繪制相關圖件。
3 結果與分析
3.1 新開墾2a農田地表風蝕風積變化
3.1.1 蝕積空間變化 4塊插釬試驗地分為西區、中區、東區、小麥地。2010年野外觀測共分為4個階段:5月17日至6月4日,6月4日至7月24日,7月24日至8月25日,8月25日至10月5日。西區試驗地由于外圍沒有防護林的阻擋,地表主要以風蝕為主,最大風蝕深度8.2cm,在沙堤后或第1條防護林帶前風力較弱時出現風積,風力較大且遭受風蝕時間最長的6月4日至7月24日階段地表風蝕量表現最大,且越靠近第1條防護林帶地表風積量也變得越大(圖1),8月25日至10月5日西區內修筑了漫灌田埂和由于平均風力最小(圖2),地表主要以輕微的風蝕風積為主同時局部風積量較大(圖3)。
2個防護林帶之間的中區試驗地地表在沿主風向林后0—3H(H為樹高)出現風積,在第2條防護林林前0—5H以風積為主,最大風積深度7cm,在林后3—32H地表以風蝕為主,最大風蝕深度4.7cm,由于微地形的變化和紅棗、冬小麥根冠的影響,地表局部出現風積。風力遇到第1條防護林帶后開始減速在林后短距離的堆積,然后風速逐漸恢復,林帶之間中部地表主要以風蝕為主,在離第2條防護林帶前5H處地表風速又開始減弱并被迫抬升,在林前出現堆積情況,離林帶越近風速消減的愈多,地表風積的深度也會越大。
東區紅棗地地表在第2條林帶后和第3條林帶前也是以地表風積為主,最大風積深度8.6cm,出現在第3條林帶林前3H范圍內,林帶之間中部主要以風蝕為主,受局部微地形影響出現風積,所不同的是第2條林帶后和第3條林帶前地表風積的深度和寬度都大于中區紅棗地地表,這是由于經過二道防護林帶的防風阻沙作用,東區地表風動力進一步減弱,還有林間距的縮小也會導致林間中部地表風蝕深度減少,林帶兩側地表風積深度和寬度有所增加(圖1)。

圖1 2010年5月17日至7月24日2個觀測階段熱瓦克4個觀測小區蝕積深度
總體看來,小麥地的防護效果依次大于東區、中區、西區地表的防護效果,離荒漠區越近、防護林帶越少和防護林之間的間距越寬,其防沙效應就會變得相對越差。
3.1.2 蝕積時間變化 按時間順序從春夏季到秋季4個觀測階段的平均風速逐漸降低,秋季風力最小(圖2)。4個階段西區最西面草質沙梗后和第1條帶防護林前地表主要以風積為主,且林前的風積量明顯大于草質沙梗背后的風積量,中部主要表現為地表風蝕,風力較大且持續時間最長和植被的生長旺季6月4日至7月24日階段地表的風蝕量和風積量都表現出最大(圖1),秋季由于風力最弱,西區表面為輕微的風蝕或風積,受灌溉沙梗的影響局部風積量較大,說明新開墾農田田間的沙梗有助于增加地表粗糙度,從而有利于局部風沙的堆積(圖3)。

圖2 2010年熱瓦克農田不同輸沙階段3個高度平均風速廓線

圖3 2010年7月24日至10月5日2個觀測階段熱瓦克4個觀測小區蝕積深度
2條防護林帶之間的中區在林后、林前0—3H范圍內主要表現為地表風積,且第2條帶防護林林前風積量明顯大于第1條帶防護林林后的風積量,中部主要表現為地表風蝕,6月4日至7月24日階段的風積量都是最大,其表現出輕微的地表風蝕。說明在生長旺季,防護林和農作物具有較好的防護效果(圖1)。東區在5月17日至6月4日階段林后和林前都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風蝕,說明林帶間距過大的防護林在春季防護效果較差,其余3個階段都表現出林前林后0—3H范圍為風積區,2林帶之間的中部主要為風蝕區,秋季觀測階段的林前風積量明顯大于林后風積量,中部的風蝕風積量都很小。整個觀測階段也表現出林前的風積量明顯大于林后的風積量(圖4)。

圖4 2010年5月17日至10月5日熱瓦克4個觀測小區蝕積深度
4個輸沙階段的0.5m高的平均風速隨時間依次降低,但在春夏季前面兩個輸沙階段1m高的平均風速均小于0.5m高平均風速,3m高平均風速最大(圖2),表明在防護林和紅棗生長初期,防護林疏透度較大,對農田地表防護能力不強。由于新疆楊是上密下疏型結構,造成春夏初期枝葉稀疏的地表層風速較大,而中上層風速相差不多并且防護林高度的中部位置風速消減的最多。在7月24日至8月25日和8月25日至10月5日兩個輸沙階段,由于防護林和紅棗生長達到旺盛期和風動力條件有所減弱,近地表平均風速隨高度增加逐漸增加,但是3m高平均風速小于或接近于1.5m高平均風速,說明夏秋季枝葉茂密的防護林和冬小麥對紅棗根部的防護作用較為有效,因為在保護性耕作地表的殘茬高度內,風速隨高度的減小而急劇減小[9]。但在春季由于風力強勁和新開墾農田地表防護能力較差,容易引起大面積的地表風蝕。因此做好新開墾農田春季和夏季初的地表有效防護措施,對于減少因地表風蝕造成幼苗大量連根拔起和沙打破壞幼苗機械組織而引起減產的破壞至關重要。
3.2 冬小麥對紅棗根部蝕積影響
第二輸沙階段小麥行前后地表以風蝕為主,其余3個輸沙階段地表都以風積為主,風積最大深度接近4cm,從2個紅棗行的中部到紅棗行的根部一般是地表風積量先減小然后再增大,在小麥行的前后5cm處容易達到最大(圖1,圖3),在6月4日至7月24日風力較強勁且起沙時間較長,地表主要以風蝕為主,小麥生長緩慢且高度低對紅棗根部起不到很好的保護作用,而在其他3個輸沙階段,小麥行前后地表以風積為主,對于減少紅棗根部的風蝕和沙打等能起到較好的保護作用。干枯的小麥相當于地表留茬,留茬不僅增加了地表粗糙度,增大了地表對氣流運動的摩擦阻力[10]。冬小麥由于離滴灌管道20cm吸收水分不充分和春夏季生長緩慢且容易干枯,需要進一步采取合理的種植方式和灌溉模式才能更好地發揮春夏頻繁風季對新開墾農田紅棗根部的防護作用。
3.3 新開墾裸荒地地表風蝕對比
圖5中分別代表新開墾未種植裸荒地、蓋度5.05%自然植被帶、新開墾中保留未開墾的蓋度為36.12%自然植被帶和蓋度33.9%自然植被帶4個樣地,地表植被主要為駱駝刺和花花柴,新開墾中保留地植株平均高度64.45cm,蓋度33.9%自然植被帶植株平均高度54.53cm。

圖5 新開墾地及周邊4個下墊面樣方DEM和等蝕線疊加
新開墾裸荒地及其周邊4個下墊面在2012年5月13日至10月20日同步觀測期間,新開墾裸荒地地表風蝕量最大,最大風蝕深度可達13cm(圖5a),植被蓋度為5.05%的自然植被區植被根部前后積沙量大且根后部積沙量大于根前積沙量,整體地表風蝕量和風積量不大,最大風積和風蝕深度分別為4.3和5.3cm(圖5b)。新開墾地中間的自然保留地由于植被蓋度和高度相對較大,在植被根部前后主要以風積為主,最大風積深度可達17.5cm,灌叢沙堆的兩側裸沙地地表風蝕程度中等(圖5c),大于蓋度33.9%自然植被帶地表沙堆間裸沙地表風蝕量,說明了墾荒可造成自然保留帶內裸露地表風速和風蝕量的加劇。風力由天然過渡帶吹經裸露農田時,處于不飽合狀態的起沙風就會導致農田風蝕的發生,這就是在草地中開墾農田易發生風蝕的原因。觀測期內蓋度33.9%自然植被樣地地表灌叢沙堆背風坡和迎風坡以風積為主,背風坡風積量明顯大于迎風坡風積量,最大堆積深度5.6cm,灌叢沙堆間地勢較低的裸沙地以輕微風蝕為主,整體風蝕量不大(圖5d)。
在5個輸沙階段中,植被蓋度為33.9%和36.12%的樣地前3次輸沙階段整體表現為風積,且植被蓋度為33.9%的樣地整體凈蝕積量(風積量加風蝕量)大于蓋度為36.12%的樣地,這是由于被開墾地中間的未開墾保留樣地內植株平均高度高、地表疏松、沙源豐富導致地表阻沙、積沙能力更強些,平均風速越大,其地表的凈積沙量也就越大(表1)。植被蓋度為5.05%的樣地在平均風速最大的6月3日至6月11日和6月11日至8月14日兩個輸沙階段表現為整體輕微地表風蝕,其余3個階段均表現為輕微的地表風積。新開墾裸露平沙地地表除了在8月14日至8月29日階段也就是新開墾地樣方周邊地表自然植被恢復最大的時候地表表現出整體的輕微風積,其余階段均表現為較強烈的地表風蝕,在平均風速最大的第二個輸沙階段,新開墾裸露平沙地地表單位面積凈風蝕量是天然植被蓋度為5.05%樣方地表風蝕量的5.64倍,其地表風蝕量達37.796kg/m2。同一輸沙階段不同植被蓋度下的單位面積凈蝕積量并不與植被蓋度呈指數關系變化,這說明了除了植被蓋度以外,地表植被的高度及灌叢沙堆地貌形態、風向等都對地表蝕積變化產生一定影響[11-12]。

表1 2012年5個輸沙階段不同下墊面地表蝕積變化
因地表蝕積量變化與近地表風速有很大的關系,所以選擇近地表平均風速廓線做對比研究,初步揭示新開墾裸荒地地表風場的變化。2012年6月11日后由于新開墾保留地氣象數據部分缺失,故未進行分析。從平均風速廓線可以看出(圖6),2次輸沙階段新開墾裸荒地0.5,1,2,3m高平均風速均大于相同時間段內相同高度的開墾保留地和自然植被帶地表平均風速,特別是3個下墊面近地表0.5和1m高平均風速相差較大,新開墾裸荒地2和3m高平均風速均比其余2個下墊面的大很多。自然植被帶和開墾保留地2m高及以上平均風速相差不大比較接近,這是由于2及2m以上高度平均風速幾乎不受地表植被的影響。開墾保留地上風向由于保留了高大的駱駝刺和花花柴灌叢沙堆,其近地表平均風速比地勢相對平坦和植被蓋度較低的自然植被帶的要低。由于沒有地表植被的阻攔和地形(上風向有公路)的影響使地表平均風速增加許多,2m高平均風速小于低層1m高平均風速,且各高度之間的平均風速差表現出最小。新開墾的裸沙地由于沒有植被的防護作用和地表沙土疏松,地表的風場發生了改變,使外圍自然植被帶吹過來的風得到加速,加劇了地表風蝕過程,相應地增加了向綠洲內部輸送的輸沙量和大氣降塵量。
5月13日至6月3日階段,新開墾裸沙地地表0.5,1,2m高平均風速分別比自然植被帶、開墾保留地相應高度平均風速增加了21.88%,122.64%,24.82%和46.58%,6.96%,3.09%,6月3日至6月11日輸沙階段,新開墾裸沙地地表0.5,1,2m高平均風速分別比自然植被帶、開墾保留地相應高度平均風速增加了31.5%,130.95%,35.43%,66.12%和12.64%,13.84%。后2個輸沙階段平均風速逐漸降低,隨高度增加自然植被帶地表平均風速逐漸增加,除了在0.5m高度上新開墾裸荒地平均風速小于自然植被帶平均風速外,其余高度上新開墾裸荒地近地表平均風速大于自然植被帶地表平均風速。新開墾裸荒地0.5m高平均風速始終大于1m高平均風速,地表無植被覆蓋,近地表湍流加強使近地表風速較大,同時也增加了地表風蝕量。

圖6 2012年新開墾地及周邊3個下墊面地表平均風速廓線
4 結論
(1)新開墾2a的農田春季和夏季初由于風沙活動頻繁和防護林枝葉疏松,地表風蝕量較大,夏秋季防護林具有較好防護作用,林內農田地表風蝕量明顯降低,在防護林帶前后0—3H易出現風沙堆積且越靠近防護林風積量越大,沿主風向林前風積量明顯大于林后風積量。
(2)防護林帶之間的3—32H特別是中部地表易出現風蝕,冬小麥對于紅棗根部有一定的風沙防護作用,但春季防護效果不是很理想,田內的沙質田埂也有助于減少地表風蝕。
(3)新開墾裸荒地地表由于沒有植被覆蓋,地表風速得到明顯加強,改變了地表風速流場,使地表風沙活動頻率大大增加,地表風蝕強烈,植被覆蓋度越大,地表風積能力愈強,同時植被越高,其地表積沙能力就越強,地表蝕積變化與植被高度和地形也有一定關系。
(4)做好新開墾地的春季和夏季初的防風蝕措施對于保護農田地表作物免受風沙危害至關重要,同時過渡帶天然植被具有良好的防風阻沙效應,應合理保護過渡帶的天然植被,避免過度墾荒和撂荒。
新開墾農田地表蝕積變化不僅與地表植被覆蓋度、防護林結構、高度等有關外,還與農田地表的土壤含水率、微地形等變化有關,因此以后試驗中應盡量減少新開墾農田人為的干擾,同時對地表土壤含水率、微地形的差異、不同季節地表植被蓋度的變化進行同步觀測,以提高對野外實驗控制的精確性。植被蓋度是影響土壤風蝕的最敏感的自然因素.植被覆蓋可通過多種途徑對地表土壤形成保護[13],所以增加春夏主要風季新開墾農田地表植被的覆蓋度是防治嚴重風蝕的主要措施。農田地表的風蝕量隨地表作物殘茬蓋度的增大而減小,在高風速下抑制風蝕效果愈加顯著[14]。在新開墾農田內在不影響紅棗正常出苗、生長的前提下可適度恢復和保留地表駱駝刺和苜蓿的覆蓋度,減少對農作物的風沙危害。實行新開墾農田棗農兼作、立體種植可有效減少地表風蝕。同時加強新開墾農田防護林網的更新完善,林帶疏透度越小,林帶平均防風效應越大[15],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防護林結構體系是十分必要的。
[1] 段玉璽,丁國棟,張進虎.鹽池縣旱作農田防護林結構及防風阻沙效能研究[J].內蒙古林業科技,2008,34(2):6-9.
[2] 潘迎珍,代德祥,劉冰.試論防護林在我國防沙治沙中的地位和作用[J].防護林科技,2006(4):41-43.
[3] Wolfe S A,Nickling W G.The protective role of sparse vegetation in wind erosion[J].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1993,17(1):50-68.
[4] Wolfe S A,Nickling W G.Shear stress partitioning in sparsely vegetated desert canopies[J].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1996,21(7):607-619.
[5] 蔣學瑋,吳發啟,馮建菊,等.新疆南疆綠洲區土壤風蝕現狀及其防治[J].水土保持通報,2003,23(1):62-65.
[6] 張鶴年.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綠洲過渡帶生態環境區綜合治理技術與試驗示范研究[J].干旱區研究,1995,12(4):1-9.
[7] 楊佐濤.戈壁與綠洲內的風向風速關系:以新疆策勒縣為例[J].中國沙漠,1990,10(3):33-39.
[8] 劉銘庭.新疆策勒縣綠洲外圍固沙植物帶的建設[J].中國沙漠,1994,14(2):74-77.
[9] 陳智,麻碩士,趙永來,等.保護性耕作農田地表風沙流特性[J].農業工程學報,2010,26(1):118-121.
[10] 劉目興,劉連友.農田休閑期作物留茬對近地表風場的影響[J].農業工程學報,2009,25(9):295-299.
[11] 趙哈林,趙學勇,張銅會.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沙漠化的成因、過程和防治對策[J].中國沙漠,2000,20(S):22-28.
[12] 張春民,吳文奇,奈民夫.半干旱區沙質農田土壤風蝕防治的效應研究[J].內蒙古林業科技,2009,35(1):9-12.
[13] 何文清,趙彩霞,高旺盛,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風蝕主要影響因子研究:以內蒙古武川縣為例[J].應用生態學報,2005,16(11):2092-2096.
[14] 趙永來,陳智,孫越超,等.作物殘茬覆蓋農田地表土壤抗風蝕效應實驗[J].農業機械學報,2011,42(6):38-42.
[15] 唐玉龍,安志山,張克存,等.不同結構單排林帶防風效應的風洞模擬[J].中國沙漠,2012,32(3):647-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