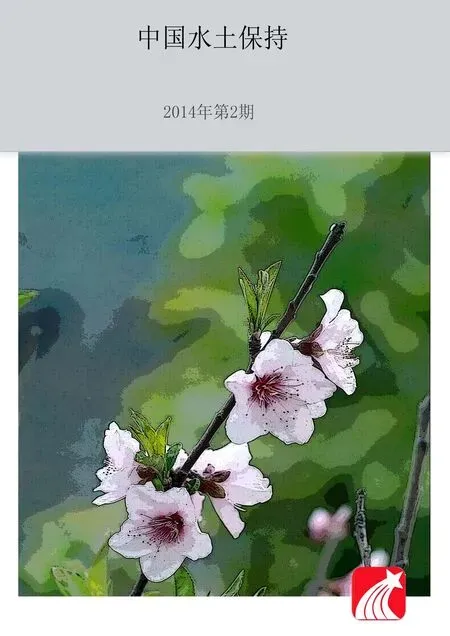景觀格局-生態過程理論在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地整治中的應用
——以延安市寶塔區羊圈溝為例
韓霽昌,王 晶,馬增輝
(1.國土資源部 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重點實驗室,陜西 西安710075;2.陜西省土地工程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陜西 西安710075;3.陜西省土地整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710075)
土地整治是增加耕地面積和提高耕地質量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重要保障。在黃土丘陵溝壑區,開展土地整治對改善當地農業生產條件、提高糧食產量及土地利用率、解決水資源與土地資源的矛盾、增加農民收入及保持社會安定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黃土高原地處我國干旱半干旱地區,降水少而蒸發強烈,土壤具有易侵蝕的特點,加上受人類過度開發利用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成為我國生態環境最為脆弱的地區之一。這一地區的土地整治面臨著擾動土壤、加劇水土流失[1]、破壞生態系統穩定性[2-3]、缺少生態景觀建設[4]等問題,解決其開發整治和生態保護并重的難題就成為目前的迫切需求。
土地利用/景觀格局對水土生態過程具有顯著的影響,通過土地利用/景觀格局優化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發生[5]。目前,景觀格局理論在土地整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經受到重視,不少學者運用景觀格局指數進行土地整治景觀生態評價研究[6-8],但在黃土丘陵溝壑區類似的實際應用還較少。因此,應用景觀格局-生態過程的相互關系,研究和探討在土地整治過程中如何盡可能地減少水土流失,改善和優化區域的土地利用,保護生態環境,不僅是促進土地整治工程健康發展的保障,而且也是保證當地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關鍵。
1 土地整治中景觀格局-生態過程相關理論研究
空間格局對過程(能流、物流、信息流)具有重要的影響,格局決定著過程,同時過程也會促進格局的改變[9]。土地利用作為人類利用土地進行各種活動的綜合反映,是景觀格局時空演變和水土生態過程的直接驅動,研究表明以土壤侵蝕產沙及泥沙輸移為主要特征的水土流失過程與流域土地利用時空格局密切相關。土地整治工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土地利用方式和景觀格局,會導致降雨、地形、土壤等因子的空間分布變化,由此也會引起地表許多生態過程的演變[5,10]。因此,通過土地利用/景觀格局優化控制生態過程,可以有效地緩解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地整治中水土流失嚴重和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保證新增耕地的可持續利用。
1.1 “源-匯”景觀理論
在景觀生態學中,“源”景觀是指在格局與過程研究中,能促進生態過程發展的景觀類型;“匯”景觀是指能阻止延緩生態過程發展的景觀類型[11]。在針對黃土丘陵溝壑區水土流失這一生態過程研究中,可以將增加土壤侵蝕的農田、道路看成是“源”景觀,將有助于減少土壤侵蝕的林地、草地、壩系等看成是“匯”景觀。如果流域中“源-匯”景觀在空間分布上達到了平衡狀態,形成合理的空間分布格局,流域就會產生較少的水、沙輸出,反之如果流域景觀格局分布不合理,并有較多的“源”集中分布,而缺乏“匯”的滯蓄作用,流域將會有較多的水、沙輸出[9]。因此,流域的“源-匯”景觀格局的合理性對于其生態過程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優化“源-匯”景觀格局,為控制土地整治區域水土流失提供了有效方法。
1.2 “斑塊-廊道-基質”景觀結構理論
景觀生態學提出的“斑塊-廊道-基質”景觀結構理論,揭示了農村景觀中田塊、林地、道路等要素重要的生態學意義。農田景觀是以林地、草地、水域、居民點和工礦企業等為鑲嵌體,以道路、河流和田坎等為廊道,以耕地為基質的網格化景觀體系[12]。“斑塊”的大小、形狀等影響著農田生產效率、生態涵養功能、景觀和物種多樣性;“廊道”的數量、構成、寬度、質量及連續性決定了斑塊之間物質與能量流的運送效率、野生動物遷移效率和景觀美學等[13]。基于“斑塊-廊道-基質”景觀結構理論,通過保護和設計“斑塊”控制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通過增加“廊道”類型提高景觀功能連通性,通過改變斑塊、廊道、基質的空間配置提高景觀空間異質性和多樣性,最終構建整體性與和諧性相統一的黃土丘陵溝壑區農村景觀。
1.3 景觀安全格局理論
景觀安全格局是基于景觀過程和格局的關系,通過景觀過程的分析和模擬,來判別對這些過程的健康與安全具有關鍵意義的景觀格局[14]。生態安全的景觀格局包含源地、緩沖區、源間聯結、輻射道和戰略點幾個組分,將各種存在的和潛在的景觀結構組分進行疊加組合,就形成某一安全水平上的生態保護安全格局;通過不同層次、不同要素的景觀安全格局組合,就能對景觀空間結構進行有效控制[15]。因此,該理論在黃土區土地整治中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李紅舉等[12]在黃土區土地整治項目實施中,從影響耕地生產的因素著手,分析主要因子——水體的特點,并基于水土安全分析結果,確定土地利用主要方向和區域,劃定土地平整的重點區域,擬定土地整治工程方案,調整不合理的基質和斑塊;從維護區域內農田景觀安全格局出發,修建灌溉、排水和防洪基礎設施及必要的水土保持設施,為景觀安全格局理論在黃土區土地整治中的應用提供了實例。
2 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地整治實施途徑
在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地整治中,制定景觀生態規劃、優化土地利用格局是生態化土地整治的重中之重。在黃土高原生態系統中,林草是徑流的滯納區,是“匯”景觀,而耕地、道路邊坡等是徑流產生區,是“源”景觀。如果通過合理的規劃布局,讓“源-匯”景觀在流域空間上合理布局,生態系統之間產流與截流兩種作用相互平衡,就可以有效控制流域水土流失。如在坡面上部增加耕地,在坡面下部可增設排洪溝、壩系等水土保持措施;在流域上游增加耕地、道路等“源”景觀,在流域下游或流域出口環境條件較好的地方新增草地或林網等“匯”景觀。另外,通過合理布局耕地、道路、林網、壩系等“源-匯”景觀,優化土地利用格局,可以使植物群落結構多樣化,提高景觀空間異質性和景觀多樣性,改善生態系統結構簡單、生態系統脆弱的狀況,提高黃土丘陵溝壑區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同時,在土地工程實施的各個環節中,也應充分利用景觀格局-生態過程相互關系,重視生態化設計。
2.1 土地平整工程
不論是土地平整過程中形成的裸露土地還是平整后開發的耕地,都是對區域水土流失貢獻較大的“源”景觀。為了使“源”景觀在降雨徑流過程發生時產生最小程度的水土流失,在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地平整過程中,坡度較大的坡耕地應設計合理的坡比,改坡為梯,田邊修筑埂坎,攔蓄部分地面徑流和泥沙,有效減少農田土壤侵蝕;對于坡高在5 m以上的邊坡,宜采用臺階式坡型設計,臺階式坡型形成斜坡和平臺交替分布的“階坡式”布局,有利于提高斜坡段的安全坡度和坡比,減輕邊坡土體對坡腳的壓力,增強邊坡穩定性。
2.2 田間道路工程
道路是農田景觀中的廊道,具有維護基質安全、斑塊穩定、物種交流的功能。在黃土丘陵溝壑區道路工程中,田間路和生產路承擔著生物遷徙的功能,應生態化而非過度硬化,可設計為泥結碎石路面或土路;而為運輸石油等修建的車行主干道則應采取硬化措施,確保道路使用壽命,并可減少道路水土流失,避免揚塵對空氣的污染。道路兩旁宜種植一定寬度的生境斑塊帶,構成黃土丘陵溝壑區的道路生態防護系統。
2.3 農田水利工程
黃土高原水資源極度匱乏,而土地整治增加了耕地面積及糧食產出,這相應地會提高水資源需求量,因此農田水利工程是優化水資源配置和水土保持的必要措施。在土地整治中,對于匯水面積較大的坡面,可因地制宜地布設一定數量的蓄水池、水窖等,田間宜采用自流灌溉或噴灌,田塊兩側布設排洪渠或溢洪道,這樣不僅可以攔蓄地表徑流、提高水資源的有效利用,還可減少漫灌對耕地侵蝕的影響,防止坡面發生嚴重的水土流失。同時,將農田水利工程與林草工程相結合,如可在渠道周圍規劃林草植物以形成蔭蔽環境,避免日光直接照射,緩和水溫的變化,營造野生動植物棲息的有利環境。
2.4 林草措施與工程措施
林草措施在生態環境脆弱、水土流失嚴重地區的土地整治中顯得尤為重要,它可增加地表植被的覆蓋度,涵養水源、防風固土。傳統的林草措施較多地考慮開挖面、道路溝渠的植物防護,而在黃土丘陵溝壑區,還應全面考慮溝頭、壩坡、埂坎、道路邊坡等易發生水土流失區域的林草建設。林草措施應根據黃土丘陵溝壑區自然條件,構建喬灌草相結合、針闊葉混交的植物群落和防護林,樹種喬木以刺槐、楊樹,灌木以沙棘、檸條等地帶性優勢種、鄉土樹種和低耗水率的樹種為主,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林草植被的成活率,而且能夠增加區域內物種種類和數量,健全區域生態系統。另外,應考慮修筑谷坊、溝頭防護、淤地壩等工程,以抬高溝底侵蝕基準點,攔蓄泥沙,防止溝頭前進、溝底下切和溝岸擴張。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與林草措施相結合,可層層攔蓄與防控并舉,充分發揮較強的削峰、滯洪能力和“上攔下保”的作用,從而有效地防范洪水和泥沙災害。
3 延安市寶塔區羊圈溝土地整治工程
本研究以延安市寶塔區羊圈溝土地整治工程為例,說明景觀格局-生態過程理論在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地整治中的應用。
羊圈溝為延河左岸的二級支溝,系碾莊溝的一級支流,流域面積2.02 km2,屬黃土丘陵溝壑區第二副區,年日照時數2 528.8 h,年均氣溫 9.4 ℃,氣溫年較差29.4 ℃,≥10 ℃的活動積溫2 500~3 400 ℃,年無霜期140~165 d,為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多年平均降水量535 mm,降水多集中在 7—9月,年際變化大。區域地貌類型為黃土梁和黃土溝,海拔1 050—1 295 m,溝谷密度為2.74 km/km2。流域內有1條主溝和3條較大的支溝,主溝為由北到南走向,主溝道長約2.7 km,高差245 m。流域最大坡度72.6°,平均坡度為29.5°。植被多為人工種植而成的次生植被,喬木主要有刺槐、柳和楊等。項目區除少部分居民點外,絕大部分為耕種的坡旱地,田塊較為凌亂,田坎過多、道路溝渠不規整、農田基礎設施不完善,水土流失嚴重,土地產出率低下。
項目總規劃田塊建設規模27.84 hm2,其中新增田塊面積為4.88 hm2,原有耕地治理面積為22.96 hm2。
3.1 土地平整工程
項目區地形狹長、高低起伏且極不規則,田塊的布局必然受到地形的限制,田塊劃分以現狀符合要求的田坎、排水溝、可利用的原有道路及新規劃道路為骨架,面積大小不等。田塊布設順山坡地形,大彎就勢,小彎取直,耕作田塊為長方形或帶形,田塊長邊與等高線平行。
項目區內耕地全部整理為水平梯田,位于河谷川臺地上的緩坡耕地(坡度一般在3°以下,少數為5°~8°)按緩坡梯田標準進行規劃設計,梯田田面寬20~50 m,田塊長200~400 m,田坎高度小于3 m;位于梁、峁坡上的坡耕地(坡度一般為8°~15°)按陡坡梯田標準進行規劃設計,田面寬10~20 m,田塊長100~200 m,田坎高度小于5 m;同時結合梯田現狀,對不規整、面積小、田面窄、田坎多而低且布置凌亂的田塊進行合并平整,對田面坡度不符合設計要求且田面較寬的寬幅梯田在單塊田內進行土方平衡,對梯田較規則、田面坡度符合設計要求的予以保留,只在田邊修蓄水埂。梯田田面坡度設計標準為:水澆地順灌水方向田面坡度為1/500~1/800;旱地橫向坡度<1/30以滿足蓄水保墑和機耕要求,縱向坡度根據地形情況<1/300。田邊設蓄水埂,埂高0.4 m、頂寬0.3 m,內外坡比為1 ∶0.5;田坎統一為土坎,外側坡為76°(坡比1 ∶0.25)。
3.2 田間道路工程
田間道路的設置結合地形、村莊布局,盡量與村莊、管道相鄰,并與項目區內外已有的道路相連接。項目區內道路規劃主要是新增田間道和生產路,從公路、農村道路延伸至田間或河堤,以便小型農機具通行。田間道或生產路通達每一地塊,道路過河時設交通橋。
本項目新增田間道路8條,為泥結碎石路面,合計長度為1 367 m,路面寬3.0 m;新增生產路2條,為素土壓實路面,合計長度為114 m,路面寬2.0 m;設3座交通橋(防洪石拱橋),橋基置于堅硬的基巖內。
3.3 農田水利工程
根據項目區水文條件、水資源量和水質情況,采用羊圈溝流域地表水,通過泵站引水,田間采用低壓管道灌溉。管道分干管和支管二級,一般支管垂直于干管布置,呈梳子形或“豐”字狀。根據設施農業灌溉要求,結合地形,在河岸附近設置4臺潛水泵站,建漿砌塊石高位蓄水池1座、集水坑1座、水壩3座,出水口設螺桿壓蓋型給水栓,管道末端設泄水井。
3.4 水土保持工程
3.4.1 農田防護林
項目區保持原林地、果園不變,結合河道、道路和項目區外植被情況,按照因害設防的原則,建立河堤防沖林、農田防護林和護路林相結合的林網體系。以“林隨水走”,在田塊和河道之間的溝岸邊坡上栽植兩排河道防沖林;以“林隨路走”,在公路兩側、田間道一側栽植一排護路林,樹種均為旱柳。樹苗選用一級苗,采用穴狀整地栽植,規格0.4 m×0.4 m×0.4 m,行距1.5 m,株距2.0 m。項目區共植樹2萬棵。
3.4.2 排水溝和渠道
項目區內已有多條小型水溝,本次設計在原水溝基礎上整修利用,以增加排水能力和耕地面積。排水溝行洪斷面為梯形,邊坡坡比為1 ∶1.25,設計溝道長度1 935 m。項目區設計渠道長度1 703 m。
4 展 望
(1)黃土丘陵溝壑區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近些年國家十分重視這一地區的生態建設,實施了退耕還林還草建設項目。黃土丘陵溝壑區的土地整治工程要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保護生態環境、緩解建設與保護的矛盾,促進補充耕地數量、質量和生態協調統一,需要加強土地整治工程的生態景觀建設,同時保證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問題也成為土地整治研究的重點和難點。
(2)將景觀格局-生態過程的理論與方法引入黃土丘陵溝壑區的土地整治中,為土地整治制定科學的景觀生態規劃設計、確定合理的工程技術模式提供了新的途徑。同時,這一地區未來的土地整治景觀生態研究重點也必然會圍繞景觀格局和水土生態過程在以上幾方面開展。
[參考文獻]
[1] 王晶,韓霽昌.黃土高原土地整治中的生態問題及對策[J].中國土地,2013(7):55-56.
[2] 葉艷妹,吳次芳,黃鴻鴻.農地整理工程對農田生態的影響及其生態環境保育型模式設計[J].農業工程學報, 2001,17(5):167-171.
[3] 魏秀菊,胡振琪,何蔓.土地整理可能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及宏觀管理對策[J].農業工程學報,2005,21(z1):127-130.
[4] 鄖文聚,宇振榮.土地整治加強生態景觀建設理論、方法和技術應用對策[J].中國土地科學,2011,25(6):4-9,19.
[5] 王計平,楊磊,衛偉,等.黃土丘陵區景觀格局對水土流失過程的影響——景觀水平與多尺度比較[J].生態學報,2011,3l(19):5531-5541.
[6] 曹順愛,余萬軍,吳次芳,等.農地整理對土地景觀格局影響的定量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06,20(5):32-37.
[7] 王軍,邱揚,楊磊,等.基于GIS的土地整理景觀效應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2):258-264.
[8] 谷曉坤,陳百明.土地整理景觀生態評價方法及應用——以江漢平原土地整理項目為例[J].中國土地科學,2008,22(12):58-62.
[9] 陳利頂,傅伯杰,徐建英,等.基于“源-匯”生態過程的景觀格局識別方法——景觀空間負荷對比指數[J].生態學報,2003,23(11):2406-2413.
[10] Fu B J, Wang Y F, Lu Y H, et al.The effects of land-use combinations on soil erosion: a case study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J].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2009,33(6):793-804.
[11] 陳利頂,傅伯杰,趙文武.“源”“匯”景觀理論及其生態學意義[J].生態學報,2006,26(5):1444-1449.
[12] 李紅舉,林堅,閻紅梅.基于農田景觀安全格局的土地整理項目規劃[J].農業工程學報,2009,25(5):217-222.
[13] 付梅臣,陳秋計,米靜,等.農田景觀規劃設計及3S技術應用[J].農業工程學報,2003,19(1):196-199.
[14] 俞孔堅.生物保護的景觀生態安全格局[J].生態學報,1999,19(1):8-11.
[15] Yu K J.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planning:with a case In south China[D].Harvard University,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