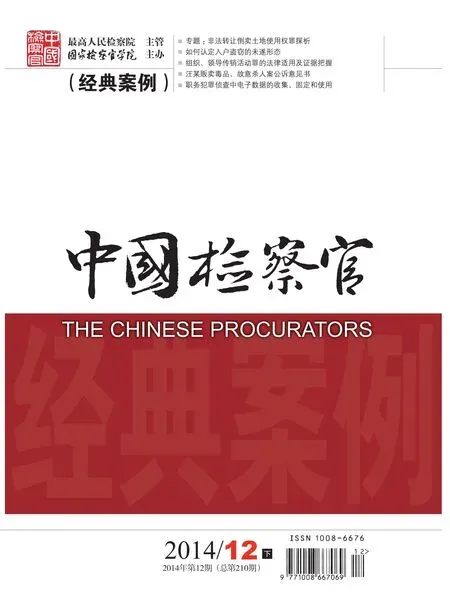“偽基站”刑事案件若干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文◎王永兵洪永新
“偽基站”刑事案件若干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文◎王永兵*洪永新**
本文案例啟示:行為人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的數量或數額達到非法經營罪起刑標準的,應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尚未達到非法經營罪的起刑標準,但相關設備經鑒定屬于專用間諜器材的,應認定為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發送廣告短信,造成嚴重后果的,應以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追究刑事責任。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康彥某、康鑫某等人自2013年3月以來,以經營的上海某營銷策劃有限公司的名義,先后指使該公司員工康海某、黎某、付某等人,通過分工負責“一條龍服務”的形式(康海某、康彥某、黎某負責招攬客戶,付某負責購買獲取公民信息及數據庫更新維護、發送,康鑫某負責“偽基站”設備操作以及群發短信),多次向上海市多家房產銷售公司承接移動基站定點短信廣告發送業務,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向不特定手機用戶發送廣告短信41萬余條,造成周邊手機用戶41萬余人次脫網,累計影響用戶通信時長達13萬余分鐘。
一、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行為的認定
根據2014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聯合出臺的《關于依法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偽基站設備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非法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1)個人非法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三套以上,或者非法經營數額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二萬元以上的;(2)單位非法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十套以上,或者非法經營數額十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五萬元以上的;(3)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兩年內因非法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受過兩次以上行政處罰,又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的。此外,生產、銷售的“偽基站”設備經鑒定為專用間諜器材的,以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追究刑事責任,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的,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
所謂非法經營罪,是指行為人違反國家的法律、法規規定,非法進行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根據我國《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違反國家規定,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應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而根據我國《無線電管理條例》規定,研制、生產、設立無線電臺,都須經過國家或地方無線電管理機構的審批。作為具有發射手機通訊信號功能的儀器設備,“偽基站”設備在功能上屬于無線電臺的一種,因此,對其的研發、生產、銷售、設立及其運營,都應經過無線電管理部門的批準;而目前網絡上所銷售的“偽基站”設備,大多由地下黑工廠或個人私自生產和銷售,自然沒有經過相關管理機構的審批,故行為人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的行為如果在數量或數額上達到了《意見》規定的標準,當屬“情節嚴重”,應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對于行為人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的數量或數額尚未達到非法經營罪的起刑標準,但相關設備經鑒定屬于專用間諜器材的,應以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而對于行為人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的數量或數額已達到非法經營罪的起刑標準,且相關設備經鑒定又屬于專用間諜器材的,則屬于一行為同時觸犯兩罪之情形,應按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即以非法經營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二、使用“偽基站”設備行為的認定
根據《意見》規定,行為人非法使用“偽基站”干擾公用電信網絡信號,危害公共安全的,以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追究刑事責任;同時構成虛假廣告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擾亂無線電通信管理秩序罪的,以處罰較重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除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利用“偽基站”設備實施詐騙等其他犯罪行為,同時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司法實踐中,人們對于行為人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發送廣告短信的行為應如何定性,一直存在較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該行為使用戶手機脫離正常通信網絡,造成通信中斷,危害公共安全,應以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前提在于行為人故意破壞了正在使用中的公用電信設施,而在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的案件中,行為人只是中斷了用戶手機與公用電信基站的聯系,并沒有對基站等公用電信設施造成實質性損害,故不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如果行為人違反國家規定擅自使用“偽基站”設備,占用了正常通信頻率,干擾了無線電通訊正常進行,并造成嚴重后果的,應以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是指行為人故意破壞正在使用中的公用電信設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根據我國《刑法》第124條的規定,該罪的構成要件為: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主觀方面為故意犯罪,客觀方面則表現為“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的行為。所謂“破壞”,既包括物理性破壞,即通過對公用電信設施施加物理性影響,使其受到物理上的毀損,如截斷通信線路、損毀通信設備等;也包括功能性破壞,即通過一定方法使公用電信設施喪失其應有的通信和信息傳播等功能,使其不能正常工作等,如采用刪除、修改、增加電信網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處理或者傳輸的數據和應用程序等手段破壞正在使用的公用電信設施的。只要符合上述兩種情況之一的,即為對公用電信設施造成了“破壞”。根據上述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人在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時,強行切斷了用戶手機與運營商基站的網絡聯系,使得運營商基站在一定范圍內瞬間失去作用,基本功能喪失,故已對公用電信設施造成了功能性破壞,其行為應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
而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是指行為人違反國家規定,擅自設置、使用無線電臺(站),或者擅自占用頻率,經責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擾無線電通訊正常進行,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根據我國《刑法》第288條的規定,該罪的構成要件為:侵犯的客體是社會公共秩序,主觀方面為故意犯罪,客觀方面表現為“擾亂”,即擅自設置、使用無線電臺(站),或者擅自占用頻率。從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案件看,行為人使用“偽基站”設備顯然都沒有經過主管部門的審批,屬于擅自使用無線電臺設備,且其在使用中是用大功率無線信號覆蓋正規基站信號,迫使用戶手機與其進行鏈接,因而干擾了正規基站的通訊工作,擾亂了無線電管理秩序,如其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則應構成擾亂無線電管理秩序罪。
由上可見,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發送廣告短信,危害結果達到一定程度的,其行為既觸犯了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又觸犯了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屬于一行為同時觸犯兩罪名之情形,系想象競合犯,依法應擇一重罪處罰。按照《刑法》規定對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的行為應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對構成擾亂無線電管理秩序罪的行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故應以法定刑更高之罪,即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定罪處罰。
三、共犯的認定
根據《意見》規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非法生產、銷售“偽基站”設備,或者非法使用“偽基站”實施干擾公用電信網絡信號等犯罪,為其提供資金、場所、技術、設備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司法實踐中,犯罪分子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大多是為了替客戶發送廣告短信。而在此類案件中,很多客戶也是在明知犯罪分子將使用“偽基站”設備的情況下,仍雇傭其為自己發送廣告短信的。對于這部分客戶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也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客戶雖明知犯罪分子將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但仍出資支持其活動,其行為符合《意見》中關于“明知他人非法使用‘偽基站’實施干擾公用電信網絡信號犯罪而提供資金幫助”之情形,應以共同犯罪論處;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客戶沒有直接具體參與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的犯罪活動,向犯罪分子支付錢款的目的是對其廣告服務的對等報酬而非給予資金支持,且交付錢款的行為也往往發生在犯罪完成之后而非犯罪過程之中,故客戶與犯罪分子既無共同犯罪的故意,也未共同實施過任何的犯罪行為,其行為不能以共犯論處。
我們認為,客戶在明知犯罪分子將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的情況下,仍要求其為自己或本人所在單位發送廣告短信,屬于主觀上對犯罪分子將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有明確的認知,且對犯罪結果的發生持積極希望的心理態度;客觀上表現為事前已與犯罪分子就犯罪方式(即利用“偽基站”設備發送廣告短信)、犯罪內容(即發送短信的內容、數量和價格等)以及犯罪報酬(即使用“偽基站”設備后支付的錢款)等進行了協商,事后也向犯罪分子支付了犯罪報酬,因此,其既有共謀、又有提供資金支持的行為完全符合《意見》中“明知他人非法使用‘偽基站’實施干擾公用電信網絡信號等犯罪而提供資金幫助”之情形,應以共同犯罪論處。至于客戶支付的錢款是業務款還是資助款,支付行為是發生在事前還是事后,都不能影響其在明知他人將實施犯罪的情況下向他人提供資金幫助的犯罪性質,也不影響對其行為的認定。當然,如果客戶對于犯罪分子將使用“偽基站”設備為自己或本人所在單位發送短信是不知情的(如犯罪分子謊稱其已經電信部門審批并具有群發廣告短信的資質等),則因其缺乏主觀故意而不構成犯罪。此外,對于此類案件中已達到相應構罪標準的共犯,應區別不同情況予以認定不同的罪名,如該客戶系個人,其行為應與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的犯罪分子均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如該客戶是單位,鑒于單位尚不能成為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而只能成為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的主體,因此,應認定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的犯罪分子的行為構成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該客戶的行為構成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
四、鑒定的相關問題
準確評估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是認定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因此,在辦理此類案件中,公安機關需請有關部門對涉案“偽基站”發送的短信總數、造成的脫網用戶數和阻塞的通信時長等進行鑒定。根據《意見》規定,相關鑒定工作應由國家安全機關負責進行。但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一般是先請無線電管理部門對“偽基站”的性質(即其工作頻率是否屬于正規基站工作頻率范圍,信號是否能夠覆蓋正規基站信號)進行鑒定,再請受害的運營商對“偽基站”的損害結果,包括發送的短信數量、造成的脫網用戶數及阻塞的通信時長等作出評估鑒定。由此產生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受害運營商作為鑒定人是否適格的問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及31條的規定,如鑒定人是該案當事人的,應當予以回避,即案件的當事人不能同時作為該案的鑒定人。故在非法使用“偽基站”設備發送廣告短信的案件中,受害運營商只能作為受害人,而不能作為鑒定人。我們認為,相關運營商可以向公安機關提供自己受損的證據,但其本身不能作為案件的鑒定人,其提供的證據材料必須經過其他中立的、有資質的鑒定機構鑒定后,才能作為《鑒定意見》予以使用。鑒于無線電管理部門有進行鑒定的技術設備和專業知識人員,故可以考慮由其作為鑒定人,并出具專業的《鑒定意見》,以使鑒定結果更加客觀、公正。而《意見》雖規定相關鑒定工作應由國家安全機關負責進行,但從《意見》的整體內容看,我們認為,國家安全機關主要是負責對“偽基站”的相關設備是否屬于專用間諜器材進行鑒定。
第二,鑒定結果是否準確的問題。在具體鑒定過程中,運營商主要是根據公安機關提供的涉案人員作案時間、地點、路線軌跡等時空要素,再比照自己公司核心網交換機中所顯示的位置異常更新的手機號,從而計算出“偽基站”設備的短信發送量和手機用戶受影響的情況。但從估算原理分析,如果當時該區域內有兩臺以上“偽基站”設備正在同時運行,那么運營商所進行的估算以及得出的結論就是所有“偽基站”設備共同造成的損害結果,故其評估鑒定結果存在著不確定性。為之,我們建議,對“偽基站”設備損害結果的鑒定,應重點從“偽基站”設備本身入手,在查獲相關“偽基站”設備后,應先對“偽基站”軟件中的相關數據進行恢復,再由鑒定部門將恢復后的數據與運營商所查出的相應時段內發生位置更新的手機號碼進行比對,而兩者相互吻合的便是受涉案“偽基站”設備干擾的手機號,同時亦應綜合其他證據材料一并予以評估鑒定,以確保相關鑒定結果更加準確。
*國家檢察官學院上海分院院長[200025]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20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