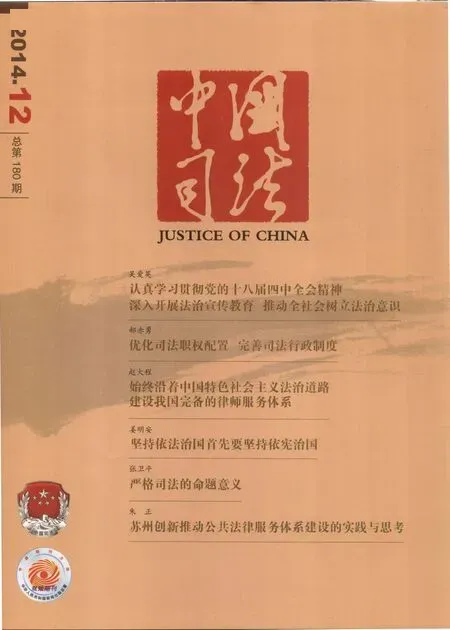刑事強制醫療程序適用條件解析
張偉東(山東省莒南縣人民檢察院)
王迎龍(北京工商大學)
刑事強制醫療程序適用條件解析
張偉東(山東省莒南縣人民檢察院)
王迎龍(北京工商大學)
修改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規定:“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關于強制醫療程序的適用條件,世界各個國家規定也不同,但是綜合起來,筆者將刑事強制醫療的適用條件歸納為三個條件:行為要件、疾病要件以及危險性要件。
一、行為條件——行為達到犯罪的程度
刑事強制醫療適用的首要前提是被強制醫療人實施了危害行為,且該行為比較嚴重,達到犯罪的程度。行為條件需要明確“違法性”和“嚴重性”兩個方面。首先,“違法性”要求精神障礙者實施的行為必須觸犯刑法,構成了犯罪。我國《刑法》第18條籠統地規定了“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說明精神障礙者行為已經達到了犯罪程度,只是因為患有精神障礙而不負刑事責任。其次,因為強制住院治療涉及到人身自由的剝奪,如果能以較小干預的手段來排除危險時,即應當盡量不用強制住院治療的方式來解決,故強制入院以“嚴重病人”為限①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頁。。然而,新法卻沒有對“嚴重性”作出具體的界定,僅是籠統的概括為“(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這不利于刑事強制醫療程序在實踐中的操作。
刑事強制醫療行為條件規定的過于模糊容易導致實踐中強制醫療適用的不統一,給辦案機關留有過大裁量空間,容易導致“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亂收治”的現象。因此,對于強制醫療適用對象行為要件的設置必須在有效控制“武瘋子”與防衛社會的目的之間保持平衡。筆者認為,由于強制醫療措施相當于完全剝奪人身自由,因此,行為人行為的危害程度應當與最低限度的監禁刑所針對的對象相對應。只有如此,才能對行為人比較公平。就此而言,行為要件除了達到犯罪程度外,還應對其可能判處的刑罰作出明確的界定。在規定了保安處分或強制醫療的一些國家,就采取了此種立法例。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98條規定,“因精神障礙而沒有第十六條第一項(責任能力)所規定的能力或者該能力明顯減低的人,實施了符合禁錮以上刑罰行為,如果不加以治療和看護將來可能再次實施符合禁錮以上刑罰的行為,在保安上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做出附治療處分旨意的宜告”②轉引自李娜玲:《刑事強制醫療程序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頁。,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可判處禁錮以上刑罰行為,那么就可以對其采取強制醫療。筆者建議,將我國刑事強制醫療適用的行為條件以刑罰進行限制,明確規定如果精神病人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可能判處徒刑以上,仍然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可以對其采取強制醫療。
二、疾病要件——仍然患有精神障礙
在決定是否對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醫療時,法院必須證明其仍然患有精神障礙才能對其進行強制醫療,否則強制醫療就失去了意義,變質為對正常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無論是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所實施的危害行為還是法院對其不負刑事責任的判決,都不能直接證明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在判決時仍然患有精神障礙③Warren J. Ingber, Rules For An Exceptional Class: The Commitment And Release of persons Acquitted of Violent Offenses By Reason of Insanity 57 N.Y.U.L. Rev. 281(1982).。雖然在關于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的法庭審判中,判定的是被告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患有精神障礙,但是一般情況下精神障礙具有持續性的特點④參見Commitment Following Acquittal by Reason of Inanity and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116 U. Pa L. Rev. 935.。但是我們是否因此就能依此推定被告人在強制醫療程序中也患有精神障礙,值得商榷。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等相關規定,在刑事強制醫療程序中,法院需要判定的僅是依據司法鑒定行為人是否是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即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是否患有精神障礙而導致其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能力,而對于刑事強制醫療程序進行時是否患有精神障礙并沒有特別說明。如《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提出的強制醫療申請,人民法院應當審查的內容主要是否附有法醫精神病鑒定意見和其他證明被申請人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材料”,《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542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強制醫療申請中應當主要包括涉案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的依據,包括有關鑒定意見和其他證據材料”。可見,目前我國的刑事強制醫療注重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而忽視在刑事強制醫療程序中被申請強制醫療人的精神狀態,對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采取了推定的態度。筆者認為,刑事強制醫療程序同普通訴訟程序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程序,在普通訴訟程序中如果被告人被判定為不負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在刑事強制醫療程序中沒有必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審查確定,重點應當在于對被申請強制醫療人在強制醫療聽審程序中的精神狀態的審查判定。
三、危險性要件——具有人身危險性
《刑事訴訟法》將具有“危險性”作為適用強制醫療的前提條件之一,即“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才能予以強制醫療,僅實施了危害行為但是不存在人身危險性者,不能科以強制醫療處分。在保安處分的理論和制度上,人身危險性占據核心地位。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保安處分理論中,‘危險性’的概念是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其重要性可與傳統刑法中犯罪構成的概念相比”⑤陳嘯平:《保安處分的誘惑與風險》,《法學評論》,1989年第5期。。強制醫療中的“危險性”是指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在被釋放之后,有可能繼續對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人身傷害的可能性。許多法治國家在規定強制醫療時也將“危險性”作為一個重要條件,比如《德國》刑法第63條規定:“當行為人在無刑事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狀態下實施不法行為時,如果對行為人及其所犯罪行的全面評估表明,在目前狀態下,行為人可能實施更嚴重的不法行為而對公眾造成威脅,法院應當判令將其收容于精神病院”⑥韓旭:《論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序的構建》,《中國刑事法雜志》,2007年第6期。。
我國全面開展司法精神病醫學鑒定有近30年,但始終無危險性評估之一鑒定項目。如何評估強制醫療程序中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的“危險性”,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第一,要考慮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實施的危害行為是否嚴重侵害公民合法權益。實施過危害行為,尤其是達到犯罪程度的危害行為的精神病人,相對于普通精神病人,往往更具有人身危險性。一般的情況下,精神病人實施的危害行為可以作為一個基礎要素來衡量其的人身危險性,危害行為越嚴重就說明其人身危險性越大,相反,危害行為越輕微人身危險性就越小。但是,除了危害行為外,人身危險性還會受到其他因素所影響,比如實施危害行為的方法、時間、地點、手段等,還會受到行為人的家庭環境、行為人性格、動機、有無犯罪前科、悔罪態度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在對行為人危險性進行評定時,除了考慮其危害行為性質惡劣與否,還要綜合考慮其他因素,將其危害行為與其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行為方式結合在一起進行綜合考量,如果認為行為人行為一貫惡劣,就表明此人人身危險性比較高,需要接受強制醫療。
第二,考慮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的病情、主觀情況、人格特征等情況。一個人在一定的生活環境下成長,就會形成某種特定的人格特征,這種人格特征就會指導他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就會貫徹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這種人格特征反映出來具有犯罪傾向的話,就說明其在日常生活中就會具有危險性,可能造成危害后果。經過精神醫學證明,反社會人格、沖動型人格障礙、分裂性人格障礙、邊緣性人格障礙和精神病后的人格改變,這些人的危險性高。
對于“危險性”,究竟是否需要經過精神病專家的專業鑒定?還是僅依賴法官的個人經驗抑或猜測?筆者認為,對于是否“具有危險性”,首先要經過司法精神病鑒定,以此為基礎,由法官通過庭審上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質證來自由裁量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人是否具有“危險性”。
(見習編輯 朱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