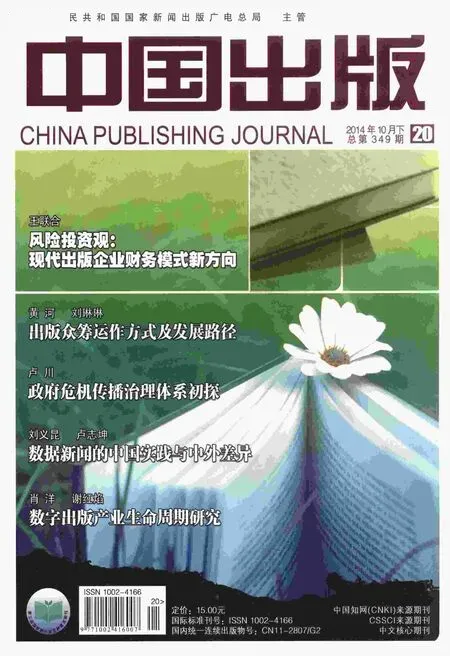中國唐宋時期與日本平安時代典籍裝幀比較*
文/ 王 曄 過偉敏
人類社會自從出現文字后,便出現了承載文字的書寫材料。書寫材料的變化,影響了裝幀方式的演變與更新。[1]中國早在殷商時期便出現甲骨文,使用龜甲獸骨作為書寫材料,春秋戰國,著書立言大都使用竹木簡,每寫完一篇,便用絲、麻或皮繩等材料,將“簡”綴編成一長幅,這是我國早期書籍的基本形制。[2]隋唐時期,造紙術的改進推動了中國書籍裝幀形式的發展與演變。而日本從公元600年遣隋使訪隋開始,歷經飛鳥(593-694)與奈良時代(710-794),唐滅隋后,日本又先后組織十幾次遣唐使團,[3]大規模地學習并引入唐朝各行業的知識及技藝,從而促進了當時日本社會的發展。至奈良時代為止,此階段文化主要移植唐文化,故被譽為“唐風文化”。奈良時代之后的平安時代(794-1185)橫跨中國唐、五代、兩宋時期,在唐風文化的基礎上,逐漸萌生出具有日本特色的“國風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
唐末至兩宋時期為中國書籍裝幀方式從卷軸裝發展至冊頁裝的重要變革期,[4]據敦煌遺書考證,在此時期內曾出現過被視為兩宋時期冊頁裝的原型、雛形或折中樣式,但因使用時間短故尚未普及,現在無法對其進行客觀描述與定義。這段變革期正處于日本的平安時代,當時日本學者大量學習及效仿從我國帶回的諸多典籍。因此,本文考察日本平安時期典籍裝幀方式后,對照唐末五代、兩宋時期裝幀方法式樣以此明確兩者的異同,關注和比較這段時期日本典籍的裝幀方法,能夠為我國古籍裝幀研究提供有意義的參考價值。
一、中國典籍裝幀的主流演變及宋版裝幀的方式特點
中國典籍裝幀歷史悠長,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裝、梵夾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多元化的裝幀方式。其中包含有本土演變而成的類型,也包含少數經外來文化融合產生的類型,兩者共同構建了我國古代豐富且具有特色的裝幀文化。
1.卷軸裝的概述及其裝幀特點
中國的書寫材料發展至竹木簡后,出現了與之并行的材料——縑帛。帛書的裝幀方法可以理解為與簡策書相似,稱為“卷軸裝”,唐與唐之前的典籍主要為這種裝幀形式。帛書上下設有邊欄,模仿簡策書的編繩,兩行文字之間繪有豎線,類似于兩簡之間的間隔縫。卷軸裝在書尾裝一木軸,以軸為中心,從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繩帶防止散開。造紙術的發明與運用逐漸取代了竹木簡和縑帛,但傳統的手寫方式及卷軸裝裝幀方式仍然盛行。
2.卷軸裝至冊頁裝的過渡
唐末期,由于雕版印刷的出現及普及引發了卷軸裝向冊頁裝的過渡,以經折裝、旋風裝為代表裝幀方式,而后,冊頁裝又演變出為梵夾裝、蝴蝶裝、包背裝及線裝等形式。旋風裝產生于唐中期,唐王仁煦撰寫的《刊謬補缺切韻》為旋風裝的典型代表。旋風裝將首頁固定在比書頁略寬的底卷上,第二頁接首頁,再將剩余頁面右側空白處粘裱于首頁左側的底卷上。收藏時由首往尾卷起,外表與卷軸裝類似,但優點在于縮短了紙幅長度,又便于逐頁翻閱。因此,旋風裝不僅保留了卷軸裝的式樣,而且具有冊頁裝的裝裱特點。經折裝的出現緣于隋唐時期佛教盛行,從國外譯回的經典數量勝多,考慮到誦讀方便,故將經典按一定的行寬數,左右反復折疊成長條形的折子,在首頁和尾頁又施加硬質材料作為封皮,以便閱讀、收藏,[5]展開后仍保留卷軸裝的形態。
此外,梵夾裝不屬于中國本土產生的裝幀形式,它將佛經寫于貝葉上,按順序排列后,再用竹木板置于經書上下,夾好后在中間穿洞系繩。[6]由于梵夾裝屬于疊葉式裝幀,閱讀時需逐頁取下,因此,這種裝幀并未成為當時典籍的主流形式。[7]
3.冊頁裝與宋版裝幀
雕版印刷的運用是中國產生冊頁裝裝幀形制的主要條件之一,[8]北宋統一政權后,雕版印刷得到飛速發展。印刷時需將書分成若干版面進行制版印刷,書籍最初呈現單頁的狀態,蝴蝶裝由此產生。具體將單頁印字面為上,紙張兩側向內對折,集數頁為一疊并戳齊后,印字頁反面的折口為版心,在此處用糨糊逐頁粘裱,再用硬紙粘于書脊處以作封皮,最后將書頁上、下、左側多出部分裁齊。
南宋盛行的包背裝與蝴蝶裝相似,不同之處在于包背裝的印字面朝外,折口為書口也朝外,集數頁戳齊后,不用糨糊,而在版心余幅空白處用紙捻穿訂并砸平,再用硬紙粘于書脊并包起書背,故稱為包背裝。
二、日本平安時代的典籍裝幀歷史及其形式
平安時代主要包含“唐風文化”“國風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種文化類型。在裝幀歷史方面,因不同階段文化的影響,出現了卷軸裝、粘葉裝、綴葉裝、大和綴等主要裝幀方式,這四種裝幀方式同為日本裝幀史從卷軸裝向冊頁裝轉變的重要代表。
1.卷軸裝的傳入與粘葉裝的普及
平安時代初期,普及的裝幀形式為卷軸裝。發展至平安中期,出現冊頁裝,多為使用寫經體字樣雙面書寫的手寫本,具體將書頁對折,在折口處施加糨糊制作而成,這種裝幀方式被稱為粘葉裝。而粘葉裝一詞由江戶時代(1603-1868)的藤原貞許命名。目前,在日本國內保留最古老的粘葉裝手抄本為空海于公元806年從長安帶回的《三十帖策子》,公元858年入唐返日的天臺宗円珍和尚也使用此種裝幀方法編寫了《円珍入唐求法目錄》。公元986年從宋朝返日的奝然帶回的《系念人交名帳》以及《金剛界儀軌》《顯密二教論》以及比叡山延歷寺留存的《傳述一心戒文》同樣也是粘葉裝的手寫本。當時,除粘葉裝之外,隨后還出現了使用線繩裝幀的縫綴法,縫綴又包括綴葉裝以及大和綴。
2.平安中后期的綴葉裝與大和綴
綴葉裝也稱列帖裝,綴葉裝是二戰前由日本書志學會命名的新造詞。與粘葉裝一樣,為雙面書寫,具體將多張紙重疊對折后成一帖,集數帖后用線繩固定折口,附上封皮將帖裝訂成冊。現留最古老的綴葉裝寫本為1120年的《古今和歌集》,還有《金剛般若集驗記》以及12世紀初的《日本靈異記》,后兩本皆為天臺宗大原來迎院所傳的手寫本。另一種用線繩裝訂的裝幀方法為大和綴。大和綴為單頁書,將每張書頁對折戳齊,首尾頁附上封面封底后,在書頁的右側靠近折口處從上至下打4眼,兩眼為一組,每組穿綴線或綴帶后再打成平結。從《紫式部日記》中查閱當時有關手寫本裝訂的篇幅可以推測,大和綴的裝幀方式在平安中期已經出現。
三、從裝幀形式、歷史淵源探究兩國典籍裝幀方式的異同
兩國歷史社會發展狀況存有不同,這種不同具體從裝幀步驟、裝幀材料、文書版式等裝幀形式方面得以體現。然而,探究兩國裝幀方式的相似之處存在的原因,需厘清平安時代日本代表性的裝幀方式的原型,并考察它與唐宋文化之間存在的繼承發展脈絡。
1.“唐風文化”影響下的卷軸裝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學、繪畫、佛典等以卷軸裝為主,日語稱“卷物”“卷子本”,施有繪畫的稱為“繪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繪卷物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語繪卷》,因文字與繪畫兩者交叉式出現于同一卷軸內,也被稱為“交互繪卷”。參閱時,繪畫從右向左、文字也從右向左展開,具有良好的時空表現。比較兩國的卷軸裝,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響,平安初期尚屬于唐風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軸裝為模板學習其裝幀方式。但因現存遺物有限、裝幀方式相似度較高,所以關于卷軸裝,該時期兩國的差異難以斷定。即使至桃山、江戶時代,卷軸裝改為冊頁裝的事例也不為多見,卷軸裝一直使用至19世紀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風葉、經折裝不如卷軸裝普及度高,在日本,經折裝主要用于石碑的摹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習字的寫本,與我國在使用領域略有不同。
2.雕版印刷的普及影響兩國裝幀方式
比較蝴蝶裝與粘葉裝的版式及歷史背景,可以發現,首先,兩者的不同之處體現在蝴蝶裝為單頁印刷,相反粘葉裝為雙面且采用手寫制書。進入北宋后,中國將雕版印刷作為官刊,其中以蜀地雕版發展較成熟,蝴蝶裝也由此產生。宋版蝴蝶裝為先印刷后裝訂,且為單頁印刷,因此,裝訂成冊后每頁都留有空白,閱讀時需連續翻過兩次空白面,印字頁不連續造成一定的閱讀不便。而粘葉裝在制書先后順序上,先裝訂后書寫,與蝴蝶裝截然不同。由于先裝訂的關系,無需考慮書頁間的排列順序,所以粘葉裝呈現雙面頁的特點,比起蝴蝶裝更易于閱讀。其次,雖然蝴蝶裝與粘葉裝同為使用糨糊作為粘接材料,但粘接位置上略有不同。與前者僅粘接折口處相比,粘葉裝因使用雁皮、黃瑞香等樹皮制作成厚紙,所以粘接位置為折口的外側,書頁軟度上遠不如蝶裝書頁輕薄。第三,日本粘葉裝書籍與蝴蝶裝乃至包背裝的不同之處還體現在字體方面,宋朝雕版印刷體的字體方正、橫細豎粗且棱角分明。但在平安初中期,日本未流行印刷術,典籍主要仍為手寫本,采用字體為寫經體,字體相對比較柔軟。
至于“縫綴”一詞,來源可追考《王氏談錄》,同時北宋藏書家王洙也將其定為“縫綴”,而《墨莊漫錄》中將此又記為“縫繢”。《墨莊漫錄》中并未提及它的裝幀方法,但在《紫式部日記》中卻有記載,縫綴為“綴集”,指使用線繩縫之而成,此點與使用糨糊粘接的粘葉裝、蝴蝶裝不同。屬于縫綴之一的綴葉裝除了粘接材料、集數帖為一冊裝訂法外,其裝幀位置與粘葉裝、蝴蝶裝類似,都為中縫裝訂。然而平安中期出現的另一縫綴形式——大和綴雖與宋版包背裝的右側裝訂方式相似,但在裝訂材料和封面封底處理上卻截然不同,包背裝使用的為紙捻,但大和綴則為線繩。對于封面封底,包背裝使用一張整紙,但大和綴卻使用兩張單獨裱紙。據前文所述,日本縫綴的大和綴屬于單頁書且印字面外折,折口即為書口,與其相對處縫綴。這說明,由于平安中期日本上流社會仍熱衷收集宋版圖書及效仿其裝幀方法,因此類似蝴蝶裝的單頁印刷及包背裝書頁外折的裝幀方式逐漸滲入日本社會,大和綴正是宋朝雕版印刷冊頁裝傳入日本的映射。為此,可以推斷,大和綴效仿了宋版裝幀包背裝之后,逐漸在國風文化的影響下,采用和紙作為封面并使用組紐系結固定,由此大和綴才算真正定型并得到推廣。
另外,關于版式書頁,兩國也存在較大差異。中國典籍無論是卷軸裝、蝴蝶裝或包背裝,大都設有邊欄框格,段落間不設空欄,但日本的典籍原則上不設框格,段落間設置空欄且文字連綿。關于這點,可從文字、語言等方面得到啟示。中國使用象形、表意的漢字,使用句讀段文因此無需設空欄,日本平安時期使用手寫制書,除表意文字外,還混合表音文字,所以段落間必須空欄。
四、從敦煌遺書看粘葉裝、縫綴與宋版裝幀的淵源
為考證日本平安時期出現的粘葉裝、縫綴是否源于我國的裝幀方式以及判斷這兩者的固有文化屬性,因此作者將5~11世紀敦煌遺書中所出的寫本、印本作為主要參考對象,比較其裝幀方式,明確兩國裝幀方式的內在聯系。
在敦煌遺書中發現唐末五代時期粘葉裝的《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9]因此,學術界也有粘葉裝為蝴蝶裝的原型這一說法。根據敦煌遺書得知,對粘葉裝的裝幀方法可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單面寫字,印字面內折,按書序集為一疊,空白面相對涂抹糨糊裝訂,與北宋時期的蝴蝶裝裝幀方法相仿,因此可以認為,粘葉裝為蝴蝶裝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另一種將紙張對折形成四個頁面,除首尾頁外,每一頁面均寫字,最后按序排列后在折口兩側涂抹上糨糊,這種方式與日本粘葉裝十分相似。而這兩種裝幀方法的不同或許緣于書頁紙張質地厚薄的不同。前者為單面書寫,所以可選擇質地較軟薄的紙張,印字背面經粘接后能夠提高書頁的硬度和強度。后者選用較厚硬的紙張,考慮到書寫利用率的關系,故采用雙面書寫并且僅在折口處施用糨糊以作固定之用。
由此可見,平安初中期盛行的粘葉裝受到唐末五代時期冊頁裝的影響,所以產生出與中國粘葉裝、蝴蝶裝在粘接方面相類似的裝幀特征,但由于兩國社會發展程度不同,導致制書的先后順序、紙張、字體上萌發出具有日本特點的裝幀風格。此外,粘葉裝一詞并非出現于平安時代,早期被稱為“胡蝶裝”“綴葉裝”(“列帖裝”)。幕府末期及明治時期,這種混亂局面達到頂峰。但明代辭書《通雅》中解釋,“粘”與“糊”同義,因此排除了粘葉裝為綴葉裝的說法。而后,日本學者也因粘葉裝與宋版蝴蝶裝存有不同,故采用此名。
對于縫綴的裝幀,在敦煌遺書中發現其方式不止一種。其一,書頁對折且雙面書寫,在折口處采用粘葉裝的方法先用糨糊固定書冊,然后使用繩線將整個書背縫住;其二,將單頁印字面內折,折口為書口,書口相對側打3眼穿縫線,此類書籍已具備線裝書的特點;第三,將書頁集數張為一疊對折成一帖,集數帖后縫合折口作為書背,用線繩反復縫綴,由此可見,也就是這種手法與日本縫綴之一的綴葉裝相似度較高。
此外,敦煌遺書中發現了蜀地印刷的唐代雕版刊物以及翻寫蜀版佛典的卷軸書,也存在采用綴葉裝與包背裝混合型裝幀方法的五代寫本,從中可以推測當時蜀地與敦煌之間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交流,這也是蜀地寫本裝幀方法傳入敦煌地區的有力證據。因此,可以斷定,五代時期蜀版裝幀方式傳入北宋后逐步演變成為宋版包背裝,這種裝幀方式進而影響了周邊國家的書籍裝幀。
綜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時期的典籍并學習效仿其裝幀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現普及,仍為以手寫本為主的昌盛期,這一點是影響兩國裝幀方式不同的關鍵原因。比較敦煌遺書的裝幀方式后可以斷定,日本冊頁裝幀方式的粘葉裝、綴葉裝及大和綴,毫無例外是以唐、五代時期的手寫本和宋版裝幀為基準發展而成的產物,并非日本原創的裝幀方式。
縱觀典籍裝幀的歷史,唐末雕版印刷開始出現,因而相繼取代了寫本的卷軸式裝幀法,而后進入印刷時期,典籍裝幀方式由蝴蝶裝向包背裝演變,發展脈絡按時代特征、印刷術及造紙術的更新而變化。不同歷史時期存在具有代表性的裝幀方式,總體而言,裝幀方式演變呈現規格化、標準化的發展特征。另一方面,日本的裝幀方式轉變相對平穩,同一歷史時期內,多種裝幀方法共同使用,不具備明顯的更替特點。這是因為比起我國,日本進入雕版印刷時代較遲緩,平安初期至中期,卷軸裝以及寫本未被完全取代。由此可見,平安時期的日本裝幀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歷史特征,因而導致該時代對于冊頁裝典籍的裝訂以及文書形態并沒有嚴格定義和區分,裝幀名稱相對籠統、混亂,存在不明確的稱呼,以至于在近代才被具體定義。
五、結語
唐、五代、兩宋是中國的書籍裝幀方式發展與變革的關鍵時期,其中,兩宋時期在雕版印刷的影響下,蝴蝶裝與包背裝先后成為當時裝幀的主流方式,但兩者的源頭還需追溯至唐末五代時期以前,或是同時期的周邊國家。然而源于國情、社會發展狀況及語言構成、閱讀習慣等方面的不同,從中國傳入的裝幀方式在異國被保留并普及,更有甚者更演變為具有異國特色的裝幀方式。這種演變發展方式充分彰顯了我國書籍裝幀史深厚的文化內涵,因此,比較分析這些裝幀方式,不僅是為了促進我國書籍研究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推廣,為當代書籍裝幀提供設計參考,開拓設計思維,實現傳統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注釋:
[1]張光華.中國古籍裝幀形式演變論述[J].河池學院學報,2006(4)
[2]何卜吉.中國圖書知識[M].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8
[3]唐朝主要派遣遣唐使的年代(公元紀年)為:630,653,654,659,665,669,701,717,733,752,759,761,762,777,779,804,838,894
[4]方俊琦.淺說古籍裝幀形態框架結構[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9(6)
[5]李致忠.中國書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古書經折裝、梵夾裝、旋風裝考辯[J].1986(2)
[6]葉筠筠.梵夾裝對中國冊葉裝書籍形制的影響[J].裝飾,2009(1)
[7]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552
[8]劉國鈞,鄭如斯.中國書的故事[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87
[9]李致忠.敦煌遺書中的裝幀形式與書史研究中的裝幀形制[J].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