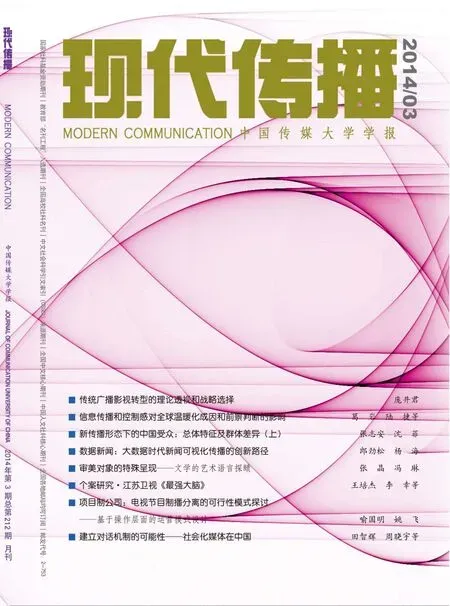信息傳播和控制感對全球溫暖化成因和前景判斷的影響
■ 葛 巖 陸 捷 秦裕林 何俊濤
信息傳播和控制感對全球溫暖化成因和前景判斷的影響
■ 葛 巖 陸 捷 秦裕林 何俊濤
觀察外部信息與內在控制感對于全球溫暖化歸因和解決前景判斷的影響,本研究發現,溫暖化成因的信息會影響歸因,但對前景判斷影響不顯著;個體控制感對歸因和前景判斷均有顯著影響。回歸檢驗表明,比之外部信息,內在控制感對歸因和前景判斷有更強預測力。本研究的發現支持傳播效果研究從強調外部信息到重視受眾內在特征的轉向,并為理解對全球溫暖化一類復雜問題的判斷機制,提供了經驗化解釋和傳播策略。
全球溫暖化;控制感;歸因;判斷
一、背景與問題
看過天氣預報,我們會不假思索地決定出門該穿多少衣服;目擊有人動手打人,我們立刻知道那是錯誤的行為。然而,當有人說轉基因食品無害,我們相信嗎?當有人說昂貴的護膚品能夠讓我們返老還童,我們相信嗎?很可能有人信,有人不信。信或不信,是由于接受的相關信息不同,抑或,還有其他原因?
認知科學研究表明,形成判斷時的信息加工過程是雙向的: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約翰·安德森,2012)。通過感官,外部信息進入大腦,形成知覺供進一步加工,曰自下而上。與此同時,腦中儲存的相關信息也會被提取,滲入知覺、推理、判斷等一系列環節,曰自上而下。最終的判斷既不完全由外部信息所決定,也不純粹受控于腦中已有信息。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中,理解判斷的形成,須考慮外部信息傳播的影響,也須考慮記憶、預設態度和判斷者個性特征,還須考慮外部信息、內在因素與判斷對象本身的性質(如穿什么衣服,或轉基因是否導致斷子絕孫)之間復雜的交互關系。循此思路,本研究欲考察信息傳播和內在心理特質——具體言之,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對理解全球溫暖化問題的影響。
全球溫暖化被視為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它不但是環境問題,更由于關涉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國家利益糾紛,也成為國際和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在各國首腦的峰會上,在主要國家的政治選舉中,政客、專家、選民爭論不休。大聲呼吁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的環保主義者,似乎已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然而,另一群人卻視溫暖化威脅為故弄玄虛。在科學家中也不乏有人相信,溫暖化是大自然周期變化的結果,是難以避免的自然過程,與備受抨擊的人類生活方式并無必然聯系。那么,究竟孰是孰非?
如同轉基因食品究竟有沒有危害,高級護膚品有沒有作用,中國房市泡沫何時將破裂,美國經濟哪天會復蘇一樣,全球溫暖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判斷這類問題時,或因信息不完備,或因信息體量巨大難以處理,我們,甚至那些專家或自詡是專家的人們,都很難做出準確并令人信服的判斷。我們因此推測,面對溫暖化問題,除外部信息之外,內在心理特征也會干預判斷的形成。本研究欲觀察彼此對立的信息和被試主觀控制感各自對溫暖化歸因和解決前景預期的影響,也觀察二者可能產生的交互作用。
二、研究設計、假說與實驗程序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定兩個自變量和兩個因變量,自變量為(1)有關溫暖化成因不同觀點的信息,(2)被試的自我控制感;因變量為(1)被試的溫暖化歸因,(2)被試對解決前景的判斷。
1.自變量
溫暖化成因信息類型:無論是依據傳播學或心理學研究傳統,外部信息都被看作影響認知與判斷的重要變量。我們因此設定有關溫暖化成因不同觀點的外部信息為自變量,分為強調人為因素和強調自然因素兩種類型(表1)。
個體控制感:社會認知心理學一直強調個體心理特征在認知和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廣為關注的心理特征之一是控制感。依據懷特的定義,控制感指個體對周圍世界可控制性的一種主觀信念——感知或感受。它源于個體應對環境時所需的對行為結果的可預期性,與人類進化過程有關(R.White,1959)。

表1 外部信息類型示例
對控制感研究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但研究者們對之的稱呼不盡相同。班杜拉所謂“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A.Bandura,1986),羅特筆下的“內部控制源”(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J.Rotter,1971),道尼使用的“個體效能感”(the sense of personal efficacy)(G.Downey,et.al,1987),都與控制感密切相關,可視為同一概念的不同稱謂。在班杜拉看來,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們對影響自己的事件的控制能力的自我知覺,是個體在行動前對自身完成該活動有效性的一種主觀評估,從而是人們行動的重要基礎(A.Bandura,1989)。過往研究發現,在沒有接受特別培訓或者引導的情況下,個體的控制感會比較穩定。通過干預認知、動機、情感和決策過程,控制感對個體行為與選擇產生調節作用(A.Bandura,2001)。
有理由假定,由于信息之間的沖突,也由于相關信息的高度專業化,普通被試很難對溫暖化這樣的復雜問題做出理性判斷。當外部信息和個體知識不足做出有把握的判斷時,判斷者的心理特征——如控制感——便可能顯著干預判斷的形成過程。本研究因此將控制感作為另一個自變量。
2.因變量
溫暖化歸因和解決前景判斷:面對不同觀點的信息,受不同程度控制感的影響,被試對溫暖化的歸因,對解決前景的判斷應會有所變化,故設定溫暖化歸因和解決前景判斷為因變量。歸因有“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兩種選擇;前景判斷測量使用5級量表(1=“肯定無法解決”~5=“肯定有辦法解決”)。
(二)研究假說
延續過往研究肯定外部信息影響的思路,我們推測有關溫暖化成因的不同觀點會影響被試歸因,故有假說:
H1.比之閱讀強調溫暖化主要成因為自然因素的信息,閱讀強調溫暖化主要成因為人為因素的信息,被試更可能做出人為因素歸因。
我們還推測,如果閱讀強調溫暖化主要成因是自然因素的信息,視溫暖化為自然過程,被試更可能相信改變溫暖化的努力將無濟于事,故有假說:
H2.比之閱讀強調溫暖化主要成因為人為因素的信息,閱讀強調溫暖化主要成因為自然因素信息,被試更可能做出溫暖化難以通過努力來解決的判斷。
由于溫暖化屬于難以依賴外部信息作出判斷的復雜問題,個體內在心理特征應會顯著影響判斷結果。又由于控制感強者通常更相信行為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力量,該類被試可能相信人類行為對于溫暖化成因和解決的作用。我們假定:
H3.比之弱控制感被試,強控制感被試更可能相信溫暖化主要成因為人為因素。
H4.比之弱控制感被試,強控制感被試更可能相信溫暖化能夠通過努力解決。
至于外部信息和控制感對溫暖化歸因和前景判斷影響力量的孰輕孰重,我們很難做出事前評判。因此,實驗使用不代表我們預設觀點,僅供檢驗使用的工作假說:
H5.比之閱讀信息,控制感對被試的溫暖化歸因的影響更為顯著。
H6.比之閱讀信息,控制感對被試的前景判斷的影響更為顯著。
(三)實驗程序
1.問卷
實驗使用兩種閱讀信息:(1)引用相關數據和專家言論,清晰表述溫暖化成因主要是人為因素的觀點;(2)引用相關數據和專家言論,清晰表述溫暖化成因主要是自然因素的觀點。閱讀信息從大眾媒體中擇選而來。初稿完成后進行了兩次預測(N=40x2),確定預期被試群體能夠準確無誤地理解不同的論據和觀點。
兩組被試在閱讀不同信息后須作出判斷:(1)溫暖化(a)主要是人為因素所致,(b)主要是自然因素所致;(2)“通過共同努力是否可以解決全球變暖問題?”(5級量表)。
2.量表
使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王才康等,2001),通過對10個問題的5級測量獲得每位被試控制感強度的均值。在對預定被試群體中所做的前測(N=60)中,量表通過Cronbach可信度測量(ɑ=0.887)。正式測試(N=110)所獲控制感數據也通過了該測量(ɑ=0.946)。
3.測試
2013年7月到9月,我們在上海四所高校招募在校專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被試共110人。其中,男性64人,女性46人,男女比例58.2%:41.8%;年齡在18至29歲之間,平均年齡22.518歲(SD=2.38)。測試中,被試隨機分為兩組,每組55人。一組被試閱讀強調人為因素的問卷,稱人為組;另一組閱讀強調自然因素的問卷,稱自然組。閱讀后,被試先回答問卷中的問題,再填寫自我效能量表。
三、發現
(一)發現一
人為組被試中,40人做出人為歸因,15人做出自然歸因;自然組被試中,24人做出人為歸因,31人做出自然歸因(圖1-A)。χ2檢驗顯示,二者差別十分顯著,χ2=9.567,df=1,p=0.002。發現支持H1,說明外部信息類型對歸因影響顯著。

圖1 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二)發現二
人為組被試中,認為“比較不可能”解決溫暖化問題者17人,“不確定”者14人,“比較可能者”18人,“非常可能”者6人;自然組被試中,持上述選擇的被試分別為21、15、17和2人(圖1-C)。兩組均無人選擇“肯定不可能”。χ2檢驗顯示,兩組之間差別不顯著,χ2=2.481,df=3,p=0.478。發現拒絕H2,說明外部信息類型對前景判斷無顯著影響。
(三)發現三
以5級量表的中值3為界,依每被試控制感均值將其劃入強與弱控制感兩組,強控制感被試59人,控制感均值3.746,弱控制感被試51人,均值2.306。二組控制感差別顯著,t=23.886,df=104.87,p=0.000,說明控制感組劃分合理。人為組中,強控制感者29人,弱控制感者26人,自然組中,強控制感者30人,弱控制感者25人。控制感人群在兩組間分布無顯著差別,χ2=0.037,df=1,p=0.848。人為組控制感均值為3.136,自然組為3.020,二者亦無顯著差別,t=0.775,df=106.88,p=0.440,說明控制感在不同信息組間均勻分布,允許直接觀察控制感對歸因的作用。
v2檢驗顯示,比之弱控制感組,強控制感組做出更多人為因素歸因(圖1-B),χ2=52.388,df=1,p=0.000。發現支持H3,說明控制感強度對歸因影響明顯。
(四)發現四
對控制感與前景判斷間關系的檢驗顯示,強控制感被試更可能對前景持較樂觀預期,弱控制感被試則相反,但兩組中均無人做出“肯定不可能”的選擇(圖1-D),二組差別十分顯著,χ2=76.965,df=3,p=0.000。發現支持H4,說明控制感強度對溫暖化解決前景判斷影響明顯。
(五)發現五
為比較兩自變量對因變量影響力差別,我們為分類變量外部信息類型和溫暖化歸因賦值,令人為成因信息=1.00,自然成因信息=2.00;人為因素歸因=1.00,自然因素歸因=2.00。使用這些賦值的線性回歸檢驗顯示,控制感系數(-0.438)的絕對值大于外部信息系數(0.240),說明控制感對歸因有更強預測力(表2)。發現支持H5。

表2 自變量對溫暖化歸因影響力的回歸檢驗
(六)發現六
回歸檢驗還顯示,外部信息類型對于前景判斷無顯著預測力(p=0.269),控制感則預測力顯著(p=0.000),且系數高達1.010(表3)。發現支持H6,說明控制感對溫暖化前景判斷有更大影響。

表3 自變量對溫暖化解決前景預測影響的回歸檢驗
(七)發現七
為進一步確定外部信息類型與控制感的影響力量,我們還測量了被試對溫暖化問題的事前認知和人際傳播的影響,計有對溫暖化問題的了解程度(1=“完全不了解”~5=“非常了解”),對溫暖化的感受(1=“感受不到”~3=“感受得到”),溫暖化對生活的實際影響(1=“無影響”~3=“有影響”),以及周圍朋友對溫暖化形成的歸因(1=“人為因素”~2=“自然因素”)等四個問題。回歸檢驗顯示,在考慮事前認知和人際傳播影響的條件下,外部信息類型、控制感對溫暖化歸因預測力顯著,對溫暖化的感受預測力邊緣顯著(p<0.10),其他變量無顯著預測力(表4)。檢驗還顯示,僅控制感對前景判斷有顯著預測力,其他變量均不顯著(表5)。發現表明,雖然感受對歸因或有作用,整體上,事前認知與人際傳播對歸因和前景判斷并無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選擇信息類型和控制感作為自變量是合理的。

表4 自變量、事前認知和人際傳播因素對溫暖化歸因影響的回歸檢驗

表5 自變量、事前認知和人際傳播因素對溫暖化前景判斷影響的回歸檢驗
四、討論
我們的發現支持H1、H3、H4、H5和H6,拒絕H2,說明信息類型,特別是個體控制感強度,對全球溫暖化歸因和解決前景判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量。本研究支持過往研究者的觀察,再次說明主觀控制感在復雜問題判斷中的顯著作用。
對本研究思路的進一步發掘還可以為傳播策略提供有益啟示。例如,設想某政黨以批評企業破壞環境的發展方式為政治訴求,其競選宣傳強調人類行為是溫暖化的主要成因。我們的研究顯示,這類宣傳會對溫暖化歸因產生影響(發現一、發現五)。研究還顯示,強控制感選民更可能是該黨的“鐵桿票倉”,弱控制感選民支持對立看法的概率更高(發現三)。進一步分析還透露,雖然外部信息類型對強或弱控制感被試都有影響,但對后者影響更為顯著。如圖2所示,以3為界區分不同控制感被試,雖然強控制感組在閱讀人為成因信息時,無人做出自然歸因,弱控制感組在閱讀自然成因信息時,無人做出人為歸因,但強控制感組在閱讀自然成因信息時,僅有20%的人會做出自然歸因,而弱控制感組在閱讀人為成因信息時,高達42%的被試做出了人為歸因。若為歸因賦值(參見發現五),在人為成因信息條件下,強控制感組歸因均值為1.00,在自然成因信息條件下,該組歸因均值為1.20,兩者差別顯著程度p=0.0105。在同等條件下,弱控制感組歸因均值分別為1.58和2.00,差別顯著程度為p=p=0.00011。換言之,信息類型對弱控制感組和強控制組影響力差別顯著程度超過100倍。這不啻說明,比之強控制組對自然成因信息的接受程度,弱控制感組更容易接受人為成因信息。對于政黨競選而言,彼此競爭的雙方或多方均會擁有“鐵桿票倉”,“鐵桿”們的投票意向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爭奪選票或影響輿論,政治傳播的目標是那些“搖擺選民”。我們的分析顯示,宣傳對于弱控制感選民或有更強烈影響,強調人為成因的信息傳播更可能改變這群人的歸因,從而改變他們的選舉意向。

圖2 信息類型和控制感對溫暖化歸因的影響
五、結語
傳播效果研究經歷了從強調外部信息影響到重視受眾內在特征作用的轉向。我們的研究提供為支持這類轉向的新例證,并為人們理解對全球溫暖化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的判斷機制,提供了經驗化的分析和解釋。
需要說明的是,使用大學生被試和較小規模樣本,本研究發現的外部效度尚需通過背景多樣的大規模樣本來驗證。此外,本研究在上海實施,比較我國許多城市和地區,例如常被霧霾籠罩的北京或河北,環境污染對上海居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或相對較輕。若實驗在污染問題更為嚴峻的地區實施,事前認知因素或會對溫暖化歸因和前景判斷有顯著影響。進一步研究需對這些問題有更充分的考慮。
(本研究獲得上海交通大學文理交叉研究重點項目資金支持,項目編號:10JCZ01。)
① [美]約翰·安德森:《認知心理學及其啟示》,秦裕林、程瑤、周海燕、徐玥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年版。
② 王才康、胡中鋒、劉勇:《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應用心理學》,2001年第1期。
③ A.Bandura(2001).Social cognitive theory:An agentic perspectiv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52:pp.1-26.
④ A.Bandura(1989).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44(9):pp.1175-1184.
⑤ A.Bandura(1986).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New York:Pretince Hall,Englewood Cliffs.
⑥ G.Downey,P Moen(1987).Personal efficacy,income,and family transition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women heading households,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Vol.28:pp.320-330.
⑦ R.White(1959).Motivation reconsidered: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Psychological Review,Vol.66(5):pp.297-333.
(作者葛巖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社會認知與決策實驗室教授,媒體與設計學院雙聘教授;陸捷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社會認知與決策實驗室研究生;秦裕林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訪問特聘教授,社會認知與行為研究院(籌)實驗室研究員;何俊濤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張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