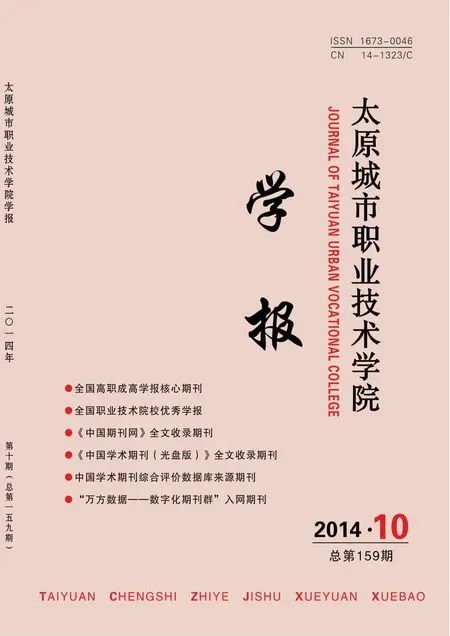論白居易新樂府詩之創作動機
李 冰
(河南工業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52)
詩歌一直以來都是古代文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媒介,總在扮演著傳達詩人內在思想、聯系個人與社會的重要角色。時至中唐,新樂府詩歌創作忽然呈現出燎原之勢。這種大肆興發的文體并不是中唐文人的首創,但它的蓬勃發展卻是在“元白”等人手中。在白居易久負盛名的新樂府詩中,以《買花》《輕肥》《縛戎人》等為代表的詩歌尤其彰顯出了白居易作為新一代現實主義詩人的寫作準則及技巧。而白居易積極創作新樂府的原因,或應有三。
一、時代所驅
大唐王朝在經歷了“安史之亂”之后,逐漸淪入動蕩。從天寶之年到元和之末,正是整個唐朝由盛轉衰的特殊時期,諸多社會矛盾漸次浮現: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外族入侵、民生凋敝……昔日熱烈飽滿的盛唐氣象已然褪去,代之而起的是一幅日益腐朽的衰亡之相。然與此同時,面對盛世不再的殘酷現實,眾多文人依然在竭盡全力地呼喊,希望警醒君主、感化黎民。
但是,如果想要達到改良社會、拯救國運的目的,就必須實施一場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的全民改革。而元和之時的白居易在官職上也僅僅居于諫官之職,以其個人之政治權力,絕無“改革”之可能。故而,白居易等人曲線救國,將這場事關中唐之勢的革新寄希望于文學作品之中,試圖以一種特殊的聲音完成從改良文字到改良社會的最終理想。正如白居易所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下以將喪之弊。……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紉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他認為,國家應以文化天下,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引導國家走向清明,與此相反,不良的文學之作及其氛圍則會將國運墜向沒落。鑒于文學這樣的大“用”功能,再加上白居易一貫的文名,“……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所以,時值國家多事之秋,白居易在朝堂之外選擇用詩文來傳達自己的忠君愛國之志實為常態。正是因為有著這樣廣大的文學受眾基礎以及積極的為政之情、遠大的人生理想,所以在中唐,以白居易為代表的詩人不得不利用他們所擅長的詩文寫作來達到其心中的政治愿望,即救濟人病、裨補時闕。
但是,這種詩文書寫在被賦予了特殊的書寫前提之后,白居易在選擇寫作內容時就必須緊扣現實,因為惟有如此才能將中唐的真實之態予以濃縮、展現,才能在一片昏黃、靡靡之中,產生一種振聾發聵的聲效,從而警醒昏聵的君主、教化躁動的民眾。
欲揭示最真實的中唐之景象,就離不開對現實生活的記敘,而生活則是由一樁樁一件件的“事”以及由這些“事”而勾連出的種種“情”連綴而成。于是,“事”與詩文寫作就構成了一種特殊關系。正因為如此,白居易才會在《與元九書》中言道:“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史書,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這種對于“事”的思考還被白居易多次闡發:“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在上述自敘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在“詩”與“事”之間的思考,其創作中的敘事意識逐漸成為自覺。由此,如何將所處時代的多“事”之態書寫出來,便成為白居易功利性詩歌寫作的重要表現因素。
二、身份所使
白居易選擇用歌詩的形式來書寫現實、呼吁革新,不僅僅緣于其文人的身份,更多的因素還是來自于其作為政治官員的社會身份,正如陳飛先生所論:“中國古代的文人文學,說到底是政治的文人文學”。
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依前充翰林學士同時授左拾遺。同年五月八日,白居易在被授予左拾遺之職一個多月后,特作《初授拾遺獻書》。文中詳敘了“拾遺”之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同時,在文末白居易也表達出了自己居于拾遺之職必要恪盡職守的政治決心:“然今后萬一事有不便于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此番自陳并非白居易的官場委蛇之語,在其后的諫官生涯中,白居易確實踐行著自己的政治責任,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不遺余力地上奏。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曾這樣描述白居易:“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而在白居易現存的文集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在諫官之任上的一些奏疏:《論于由頁裴均狀》《論魏征舊宅狀》《論太原事狀三件》《論姚文秀打殺妻狀》等。在《論制科人狀》一文中,白居易更是為因直言時事而獲罪的牛僧孺等三人以及一眾因賞識牛僧孺而被貶謫的官員鳴不平:“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不僅如此,在稍后的文辭間白居易更是情緒激昂,一展諫官本分:“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言辭激烈,錚錚之情力透紙背。
正因身懷諫官之使命,所以白居易才會在政壇之上如此奮不顧身。但同時白居易也深知,面對如今滿目瘡痍的中唐之世,他需要做的不僅在朝堂上指陳時弊,把那些“側聽”而來的“時議”奏聞于上,他還需要用更多更靈活的方式來完成他諫官的職責,及其作為儒家用世文人的責任。于是,在廟堂之上,白居易選擇用政治性的文書來表達意見、警示君主;而在廟堂之下,白居易轉而用樂府詩來潤化圣心及民心。對此良苦用心,白居易也多次在與朋友的書信往來中道明。《與楊虞卿書》中,白居易回顧自己身居諫官之時的行徑:“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于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而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將自己的行為、心態解釋得更為詳細:“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在白居易看來,欲挽國家之頹勢,必先以君主為重點警醒對象,因此,在白居易元和年間所作的《新樂府》五十首中,近四十首都是從“戒”“刺”“惡”“愍”“傷”“憂”“疾”“誚”“哀”等角度,力圖展現中唐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弊端及丑陋之態,以期下情上達、警示君王,試圖敦促李氏王族采取積極有為的政治措施。而余下的數首《新樂府》則轉換心理角度,采用“美”王業的敘述方式,或以初、盛唐之氣象激勵君王振奮向上,或以作者內心期望之藍圖引導君主體恤民情、重整河山。總而言之,出于自我政治角色的需要,白居易需要借助一種特殊而有效的方式來輔助自己完成諫官之任及“兼濟天下”的人生志向。
三、文體所擅
而對于白居易為何會選擇樂府歌詩來實現自己的教化目的,吳相州先生在他的文章《論元白新樂府創作與歌詩傳唱的關系》中已然指明:“元白的新樂府創作是對盛唐以來朝廷音樂反思的結果,這一創作固然是要實現其‘補察時政’的參政目的,但他們所采取的形式也有很強的針對性,即意在以這種新的歌詩取代朝廷的大雅頌聲和樂府艷歌。”在吳先生的這番論述中,點出了一個重要的線索,那就是樂府詩作為一種詩歌體裁,它具備了音樂性、傳唱性。這一特性,有助于樂府詩在朝廷以及民間的傳頌,從而裨益于白居易創作目的的實現。
除了攜帶有音樂性、傳唱性之外,樂府詩歌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性、政治性。從樂府的起源可知,樂府詩的出現是和朝廷中央所實施的“采風”制度緊密相關的。而所謂“采風”則具有不容忽視的政治色彩,即補察時政。在《策林》中,白居易就將采詩之舉描繪得極為清晰:“臣聞圣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日采于下,歲獻于上者也。……然后君臣觀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故政有毫發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辟以來,未之聞也。”在這段論述中,白居易明確指出,國家欲永享太平,首先必須確保上、下溝通之暢,而承擔起這種溝通重任的載體則是詩歌。詩歌進入朝廷,經樂師加工之后,便成為樂府歌詩流入廟堂之上、君王之畔。由此,樂府詩就使得下情上達成為一種可能。而縱觀唐之時,采詩之制久已不存,彌漫于詩壇之上的樂府多為媚俗娛樂之辭。由此白居易在《采詩官》一詩中憤憤不滿:“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而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白居易認為,責在朝廷。白居易甚至在《采詩官》的自序中將“采詩”的重要性直接上升到了決定國家存亡的高度:“鑒前王亂亡之由也”。他認為采詩的設置與執行,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開明之態,借助下情上達的民情互通,可以及時、有效地完成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與踐行,從而達到長治久安的政治目的。有鑒于此,作為一國之君,中唐君王必須改變以往端居朝堂的閉塞之態,要自上而下地去采集盛行于民間的“歌詩”,“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再加上此前“詩圣”杜甫與時俱進,已開創了“因事立題”的新樂府,為古老的樂府詩歌注入了屬于李唐王朝的獨特氣息。樂府文體的諸多積淀都為白居易等詩人走向新樂府的創作陣營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所以,白居易選擇以民生、民情撼動君王之時,充滿現實主義色彩的樂府歌詩就成了他的首選。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朝廷選中,以實現其詩作的諷諭、警誡之用,最終借采詩之形式使一己之作及理想流播宇內。
由此,新樂府詩便成了白居易于廟堂之外而著力創作的一類詩體,最終成為他表達政治理想、人生責任的重要工具。
[1][唐]白居易.策林·六十八議文章[A].[清]董誥等.全唐文(卷 671)[C].北京:中華書局,1983.
[2][唐]元稹.白氏長慶集序[A].[清]董誥等.全唐文(卷 653)[C].北京:中華書局,1983.
[3][唐]白居易.與元九書[A].[清]董誥等.全唐文(卷 675)[C].北京:中華書局,1983.
[4]陳飛師.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精神品質[A].陳飛,俞紹初.中州學術論文集第一輯[C].北京:中華書局,2000,181.
[5][唐]白居易.初授拾遺獻書[A].[清]董誥等.全唐文(卷667)[C].北京:中華書局,1983.
[6][唐]白居易.論制科人狀[A].[清]董誥等.全唐文(卷 667)[C].北京:中華書局,1983.
[7][唐]白居易.與楊虞卿書[A].[清]董誥等.全唐文(卷 674)[C].北京:中華書局,1983.
[8]吳相州.論元白新樂府創作與歌詩傳唱的關系[J].中國詩歌研究,2002(3).
[9][唐]白居易.采詩官[A].[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 427)[C].北京:中華書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