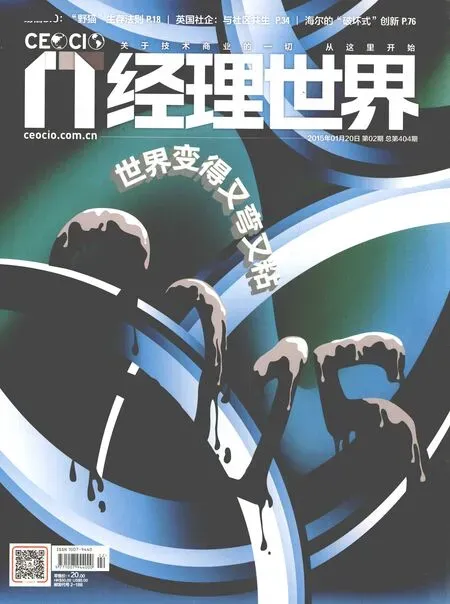1024
胡泳 郝亞洲

未來很可能存在于機器交互的界面中,但是大量的技術、倫理問題都要在人機交互的階段解決。
希望讀者看到這個標題后,可以會心地一笑。就像寧財神在《龍門客棧》的一版預告片中打出“1024”的時候,草榴一族好像接收到了族人發出的暗號,激動萬分——1024等于草榴,草榴等于“無尺度”、“無節制”、“無下限”的分享。
所以,當東西文庫的主編李婷把一本叫做《1024》的Mook給到手里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你們是在向草榴致敬嗎?”。李婷的解釋是:“1024在這里象征了字節。”
好吧,對于這個機智的解釋,不妨表示接受。這個名字取得很巧。脫胎于草榴的“1024”有著“重口味”,“精致”,“技術流”,“分享”,“極客”等意思,不管它被用在什么地方,這些都是不會變的。
如果你還是不明白,抑或非草榴中人,不如翻翻這本Mook:極其精致的版式設計,絕不小清新的內容,奇妙的插畫,相信“技術可以作為一種文化”的KK式信仰,加之東西文庫的母體譯言網本身就有的追求高度分享的組織文化,“1024”這個名字的確是再合適不過了。
比爾·喬伊的憂傷
《1024》的創刊號主題是“人機交互”,這也是人類社會在不遠的未來要面對的最現實的問題,任何領域都無法逃脫。甚至說,更遠一步的未來很可能存在于機器交互的界面中,但是大量的技術、倫理問題都要在人機交互的階段解決掉。我們看到了幾乎這個領域內所有大腕的觀點和文章,甚至尼爾·弗格森這樣的歷史學家也加入了討論陣營。
最有意思的是比爾·喬伊、邁克爾·德圖佐斯和庫茲維爾三位大佬爭鳴的一組文章。比爾·喬伊,技術狂人,太陽微系統的創始人。他更加為人所知的是“聰明人總在組織之外”的喬伊法則。德圖佐斯,已故大師,曾經是美國計算機科學的領軍人物。庫茲維爾,年少成名,因為“奇點說”名聲大震,是奇點大學的創始人。
喬伊曾寫過一篇《未來為什么不需要我們》的2萬字長文。在文中,喬伊盡情揭示了人類面對機器進化時的無力與無奈。“在發現和創新之間狂飆突進時,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無法察覺自己發明之物帶來的后果,這是一種通病。科學探索的本質——求知,一直壓倒性地驅使著我們,讓我們無法停下來看一看,技術進步的進程也會完全失控。”
在庫茲維爾的眼中,喬伊的憂傷基本算是無病呻吟,因為喬伊一直遵循著直觀線性觀的邏輯,也就是按照穩定節奏看待技術進步,而忽略了在真正的歷史中每次技術變革帶來的指數級發展。這正是庫茲維爾奇點理論的基礎。當所謂的技術爆炸式增長來臨的時候,被它顛覆的將會是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實,庫茲維爾的這些判斷和喬伊無甚區別,區別在于態度。庫茲維爾是典型的行動派,他覺得與其在那自怨自艾,不如直面顛覆,敬畏技術。
雖然德圖佐斯也極力反感喬伊的憂傷,但是他依然不忘譏諷庫茲維爾這種僅僅關注技術狂野不羈一面的思路是“嘩眾取寵”。德圖佐斯還是彰顯了一位MIT學者的嚴謹和人文風范,他在目睹了MIT計算機科學實驗室的幾十項試驗后總結說:“每一項成功技術的革新,都是兩種力量同時發揮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是理智控制下的強烈欲望,急于突破當前教條和觀念的束縛;一方面是對人類潛在需求的嚴格評估,據此淘汰那些極端荒謬的研究方向。”德圖佐斯認為,僅僅有理性是不夠的。感性的作用有兩個,一個是和理性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一個是糾正理性的過度發展。
喬伊的憂傷在于他放大了理性的作用,認為機器進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反制人類。只要機器不具備人類的感性,它就無法到達人類的高度,它就永遠不是人。
不知道德圖佐斯如果活到現在的話,他會不會對自己的理論進行糾正。如果人類情感或者人性可以被量化,并成為大數據被挖掘和分析的話,也許喬伊的憂傷會成為現實。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喬伊的理論和上世紀70年代哲學鬼才京特·安德森在《過時的人》中所闡述的想法極為相似:技術進步把我們帶入了死亡的深淵,尤其原子彈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全面掌握了消滅自己的技術。在他的眼里,庫茲維爾的奇點來臨之時,就是人類社會失控之日。
三位大師的這場爭論已經成為現代科技發展過程中的經典場景,也感謝東西文庫的編輯耗費心血,全景呈現于《1024》之中。
當然,如果你是技術史迷的話,創刊號中關于《全球概覽》的內容不容錯過。看看這本影響了KK,喬布斯,馬爾科夫等大佬們的嬉皮士范兒讀物,是如何闡釋工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