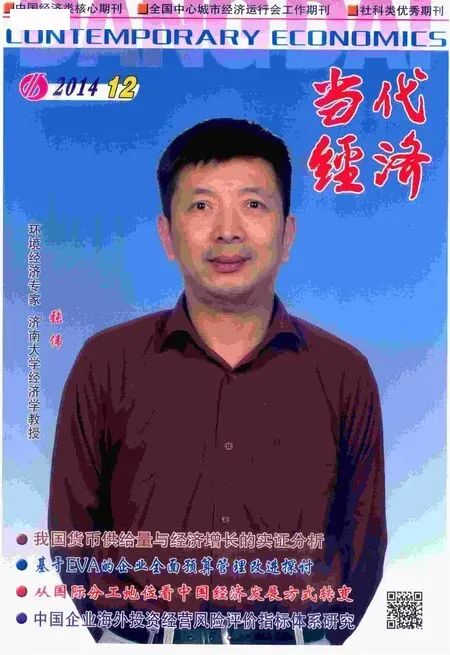天津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關(guān)系的實(shí)證研究
○劉 帥 劉 洋 孫 莉
(河北工業(yè)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 天津 300130)
一、引言
隨著片面追求高GDP的經(jīng)濟(jì)增長方式所導(dǎo)致的環(huán)境、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問題的不斷凸顯,在保持經(jīng)濟(jì)高速平穩(wěn)增長的同時(shí),如何提高經(jīng)濟(jì)增長的質(zhì)量,已被政府和相關(guān)學(xué)者放在了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首位。合理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可以提高經(jīng)濟(jì)增長的速度和質(zhì)量,同時(shí)經(jīng)濟(jì)增長又會(huì)反過來促進(jìn)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化。兩者是互促互進(jìn),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
英國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威廉·配第(1672)指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不同是引起世界各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最主要原因,這是對(du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關(guān)系研究的起點(diǎn)。隨著工業(yè)革命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國家步入工業(yè)化國家的行列,從而為研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間相互關(guān)系的理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克拉克(1940)通過分析三次產(chǎn)業(yè)中勞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的變動(dòng)情況,得出在不同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下,勞動(dòng)者收入水平的差異影響著勞動(dòng)力在三次產(chǎn)業(yè)間順序流動(dòng)。西蒙·庫茲涅茨(1957)在對(duì)50多個(gè)國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歷史數(shù)據(jù)分析后發(fā)現(xiàn),隨著社會(huì)化分工的發(fā)展,各產(chǎn)業(yè)部門的數(shù)量得以增加,分工愈發(fā)細(xì)化,隨之引起社會(huì)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經(jīng)濟(jì)所處的發(fā)展階段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相互影響。當(dāng)前,天津市正在積極推進(jìn)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shè),而新型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蘊(yùn)含著工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及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因此,從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角度探究天津市的經(jīng)濟(jì)增長顯得很有必要。
二、模型設(shè)定及數(shù)據(jù)說明
1、變量間因果檢驗(yàn)?zāi)P?/h3>
研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之間的關(guān)系,首先應(yīng)該對(duì)二者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關(guān)系檢驗(yàn)法來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
目前,對(duì)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衡量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克拉克所定義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系數(shù),用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數(shù)占社會(huì)勞動(dòng)力總數(shù)的比例來表示;另一個(gè)是國內(nèi)研究中較常用的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系數(shù),用第一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與GDP之比表示。基于數(shù)據(jù)的可得性和完整性原則,本文采用第一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S)作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指標(biāo)。衡量經(jīng)濟(jì)增長的主要指標(biāo)為GDP,剔除物價(jià)變動(dòng)造成的影響,可采取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指數(shù)(GDP I)進(jìn)行分析。采用1978—2011年天津市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為樣本數(shù)據(jù),其中GDP I以1978年為計(jì)算的基期。
2、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模型
考慮不同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 GDP影響的函數(shù) Y=(X1,X2,X3,A),其中,Y表示天津市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X1,X2,X3分別表示第一產(chǎn)業(yè)、第二產(chǎn)業(yè)與第三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值;A表示技術(shù)水平及制度變遷。對(duì)函數(shù) Y=(X1,X2,X3,A)求全微分得到:

兩邊同時(shí)除以Y,(1)式變?yōu)椋?/p>



三、對(duì)天津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的實(shí)證研究
1、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的格蘭杰因果關(guān)系分析
在對(duì)變量的格蘭杰因果檢驗(yàn)之前,先對(duì)數(shù)據(jù)的平穩(wěn)性進(jìn)行檢驗(yàn)。對(duì)S和GDP I取對(duì)數(shù),記為L S和L GDP I,而后進(jìn)行ADF單位根檢驗(yàn)(見表1)。

表1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濟(jì)增長序列的ADF單位根檢驗(yàn)結(jié)果
檢驗(yàn)發(fā)現(xiàn),指標(biāo)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wěn)序列。但進(jìn)行一階差分后變?yōu)槠椒€(wěn)序列,故兩個(gè)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進(jìn)而采用E G兩步檢驗(yàn)法對(duì)變量L S與L GDP I進(jìn)行協(xié)整檢驗(yàn),得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0%的情況下,殘差序列是平穩(wěn)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所以,L S與L GDP I是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的非平穩(wěn)變量,從而對(duì)變量進(jìn)行格蘭杰檢驗(yàn)(見表2)。

表2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濟(jì)增長的格蘭杰檢驗(yàn)結(jié)果
根據(jù)表2的結(jié)果可以看出,L GDP I的變化可以引起L S的變化,與滯后期無關(guān);L S對(duì)L GDP的影響與滯后期有關(guān):滯后期為1時(shí)L S的變化不會(huì)引起L GDP I的變化,為4時(shí)L S的變化會(huì)導(dǎo)致L GDP I的變化。所以可以看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guān)系,但是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時(shí)滯性。
經(jīng)濟(jì)增長對(du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首先經(jīng)濟(jì)增長張會(huì)導(dǎo)致需求結(jié)構(gòu)的變動(dòng),催生新的產(chǎn)業(yè);其次國民收入的提高會(huì)促進(jìn)社會(huì)投資的增長,推動(dòng)技術(shù)進(jìn)步,加速新產(chǎn)業(yè)的成長。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優(yōu)化資源配置、促進(jìn)社會(huì)分工,提高生產(chǎn)效率以及技術(shù)創(chuàng)新擴(kuò)散等方面。
從長遠(yuǎn)來看,天津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化與調(diào)整對(duì)經(jīng)濟(jì)的快速增長有顯著的推動(dòng)作用。因此,以加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調(diào)整來推動(dòng)天津經(jīng)濟(jì)發(fā)展在理論與實(shí)踐上是可行的。
2、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的回歸分析
通過查閱《天津統(tǒng)計(jì)年鑒2012》和《2012年天津市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中,1978年至2012年天津市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與三次產(chǎn)業(yè)增加值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利用(4)式的模型進(jìn)行回歸分析,回歸結(jié)果為式(5)。

回歸結(jié)果顯示,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很高,但D.W值不高,誤差項(xiàng)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關(guān)。對(duì)殘差序列ut建立A R MA模型,并用A R MA模型替換(4)式中的殘差項(xiàng),以消除回歸中的自相關(guān)問題。對(duì)(5)式中的殘差項(xiàng)進(jìn)行平穩(wěn)性檢驗(yàn)的結(jié)果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t的值為-4.989745,小于臨界值-3.670170,概率值為0.0003,所以殘差序列是平穩(wěn)序列。進(jìn)一步分析殘差序列的相關(guān)圖和偏自相關(guān)圖后,可以認(rèn)為自相關(guān)具有拖尾性質(zhì),而偏自相關(guān)在k=1與k=4處出現(xiàn)兩個(gè)峰值,然后呈截尾特征。進(jìn)而把誤差項(xiàng)表示為一個(gè)A R(4)形式。進(jìn)一步對(duì)(5)式加入ut的一至四階回歸項(xiàng),變?yōu)闉椋?)式。
lnY=α+α1lnX1+α2lnX2+α3lnX3+ut

對(duì)(6)式回歸結(jié)果顯示,和 沒有通過t檢驗(yàn),因而將這兩項(xiàng)剔除,最終的回歸結(jié)果如(7)式所示。

其中,模型殘差vt通過Q檢驗(yàn),是白噪聲過程。模型的D.W值達(dá)到2.2,有效地消除了自相關(guān)現(xiàn)象。R2項(xiàng)和三次產(chǎn)業(yè)的彈性系數(shù)表明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有很強(qiáng)的促進(jìn)作用。第一產(chǎn)業(yè)增長1%會(huì)引起GDP 0.029%的增長,顯著低于第二產(chǎn)業(yè)的0.636%和第三產(chǎn)業(yè)的0.335%。這說明,總體看來第一產(chǎn)業(yè)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帶動(dòng)作用不強(qiáng),第二產(chǎn)業(yè)仍是天津市經(jīng)濟(jì)增長的主要支柱。
由計(jì)量結(jié)果我們得出,天津市三次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促進(jìn)作用仍有很大的潛力,應(yīng)積極推進(jìn)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向現(xiàn)代化農(nóng)業(yè)、傳統(tǒng)工業(yè)向現(xiàn)代化工業(yè)的轉(zhuǎn)變,推動(dòng)三次產(chǎn)業(yè)向技術(shù)密集型和集約型轉(zhuǎn)變。此外,從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來看,在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初級(jí)階段和中級(jí)階段前期,工業(yè)發(fā)展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顯著高于第一產(chǎn)業(yè)和第三產(chǎn)業(yè)。到中級(jí)階段后期,第二產(chǎn)業(yè)的貢獻(xiàn)率開始下降,而第三產(chǎn)業(yè)的貢獻(xiàn)率開始迅速上升。天津市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工業(yè)化中級(jí)階段特征大體上吻合。所以,要大力推進(jìn)天津市工業(yè)化發(fā)展,推動(dòng)工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升級(jí),促使工業(yè)由傳統(tǒng)的低效粗放型向現(xiàn)代高效集約型的轉(zhuǎn)化,使經(jīng)濟(jì)獲得更高的增長速度。
四、結(jié)論
本文運(yùn)用格蘭杰因果關(guān)系檢驗(yàn)法和回歸—A R MA模型深入分析了天津市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之間的因果及數(shù)量關(guān)系。研究證明天津市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濟(jì)增長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guān)系,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從三次產(chǎn)業(yè)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來看,天津市正處于工業(yè)化發(fā)展的中期階段,第二產(chǎn)業(yè)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作用最大,同時(shí)第三產(chǎn)業(yè)也表現(xiàn)出了巨大潛力。因此,政府應(yīng)該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重點(diǎn)放在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化升級(jí)上,推動(dòng)工業(yè)由粗放向集約型轉(zhuǎn)變。同時(shí),應(yīng)合理引導(dǎo)發(fā)展第三產(chǎn)業(yè),深入挖掘第三產(chǎn)業(yè)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的帶動(dòng)能力。
[1]張曉峒:應(yīng)用數(shù)量經(jīng)濟(jì)學(xué)[M].北京:機(jī)械工業(yè)出版社,2009.
[2]楊公仆、干春暉: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5.
[3]劉偉、李紹榮: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增長[J].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2002(5).
[4]查奇芬、焦小偉:指數(shù)回歸—ARMA模型在我國人均生活電力消費(fèi)量預(yù)測中的應(yīng)用[J].數(shù)理統(tǒng)計(jì)與管理,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