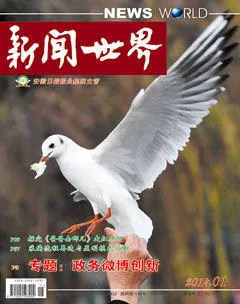新聞紙上的社會印記
王琍琍 徐霞
【摘 要】新聞史作為一門研究新聞事業(yè)發(fā)生、發(fā)展及其演變規(guī)律的科學(xué),是新聞學(xué)研究的基本組成部分。從本源上看,新聞史兼具史學(xué)基本特征,適用于史學(xué)研究方法。本文以對兩份重要報刊的研究為例,結(jié)合史學(xué)研究視角來分析新聞史研究的發(fā)展變化。
【關(guān)鍵詞】新聞史 《大公報》 范式 《申報》 跨學(xué)科
一、新聞史研究歷程
作為信息與輿論的傳播媒介,新聞事業(yè)都從屬于一定的社會階級,受制于當時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因此,對于中國歷史的各項研究,最終都繞不開對于新聞史的研究。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新聞史也隸屬于中國文化史的范疇,是社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聞史的研究,正式開始于1927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xué)史》。其中共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①,1949年前屬于新聞史研究的奠基階段,主要集中在通史、報刊史以及新聞人物傳記上;建國以后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新聞史研究全面展開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顯示出海峽兩岸共同進步的特點;1978年以來則是新聞史研究的繁盛階段,特別是重要刊物的個案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縱觀八十多年的研究歷程,新聞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歷史的報刊與報刊的歷史等同起來,新聞史變成了報刊史。就像學(xué)者李彬在談到中華民族新聞史的研究現(xiàn)狀時所說的:新聞史研究缺乏敘事,少情寡趣。一部新聞史差不多等于一份報刊出版流水帳,里面難以見到鮮活的人物、鮮活的故事、鮮活的作品,滿目多是枯澀的、干巴巴的、死氣沉沉的“貨物清單”。②在其后的研究中,雖然有廣播、電視、網(wǎng)絡(luò)等新內(nèi)容加入,但新聞史研究的范式依舊如故,顯現(xiàn)出嚴重的陳舊保守氣息。除去新聞史本身編寫的缺陷,在研究過程中,重視史料本身的研究,而輕視思想發(fā)展探析的傾向頗為嚴重。
新聞史作為一個基礎(chǔ)學(xué)科,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與此同時,“古為今用”的思想?yún)s極難踐行。對待新聞史研究,不是陷在史料的泥沼里,灰頭土臉;就是束之高閣,敬而遠之。就像新聞史學(xué)家方漢奇所指出的那樣,新聞史的研究因為總是在固有的條條框框中打轉(zhuǎn)而缺少了作為史的特點以及新聞這個學(xué)科的特點。
二、《大公報》與史學(xué)研究范式
在新聞史的漫長過程中,總有一些報紙和一些名記者繞不開跳不過。被密蘇里新聞學(xué)院評為“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的《大公報》就是其中之一。在關(guān)于《大公報》的研究中,“范式”兩個字似乎是其撇不開的核心。
如庫恩所言,每一個學(xué)科的發(fā)展階段都有其特殊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而體現(xiàn)這一結(jié)構(gòu)的模式就成為“范式”(Paradigm)③。他在《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系統(tǒng)闡述道,范式指的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shù)等等的集合。指常規(guī)科學(xué)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chǔ)和實踐規(guī)范,是從事某一科學(xué)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簡單來講,就是立足研究所采用的理論前提。
80年代之前,《新華日報》將《大公報》定性為“小罵大幫忙”,之后在改版為《進步日報》時,發(fā)表宣言坦言前身“是一張反動的報紙”,是一張為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集團服務(wù)的報紙,導(dǎo)致否定《大公報》成為輿論的主旋律。這種以是否具有先進的斗爭性的評價基點,被稱為革命化范式的邏輯。就是將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歸結(jié)為兩大基本矛盾的演化,即封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帝國主義列強和中華民族的矛盾,由此構(gòu)成革命化范式“不言自明的信念”或“共同前提和出發(fā)點”。這是新聞史研究長期以來的固有思想,以政治的眼光和史學(xué)的方式研究新聞史的發(fā)展路程。造成的局限在于,僅以黨報和革命報刊為主,忽視了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全貌,對新聞事件和任務(wù)的評價以階級分析、革命判斷為標準。可以說,在這種范式之下,我們確實走出了史學(xué)本身,卻又陷在了政治的漩渦里。
直到80年代之后,方漢奇“用‘亦捧亦罵來描述《大公報》與行政當局的關(guān)系”④,才開始扭轉(zhuǎn)革命范式下的一邊倒評價。這時候,現(xiàn)代化范式開始出現(xiàn),史學(xué)開始以世界為主題構(gòu)建中國近代史,將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稱為一個從封閉、傳統(tǒng)和落后的社會,一步步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在新聞史的研究中,加入了生產(chǎn)力發(fā)展和科學(xué)技術(shù)的觀念,將新聞史的發(fā)展放到了整個社會當中,開始關(guān)注民營報刊和報人以及當時的社會。
21世紀初,“歷史證明《大公報》是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它“堅持中國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方向,與時代共進”⑤。民族國家范式出現(xiàn)并開始在研究中滲透,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文化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zhuǎn)型歷史。新聞史研究在這一范式的主導(dǎo)下,其核心思路變?yōu)樽穼駥φ喂餐w的認同過程,突出的是認同感,強調(diào)的是經(jīng)由媒介而建構(gòu)的心理意象和感情認同。
在這些范式的演變中,出現(xiàn)變化的是研究視角,就像史學(xué)研究開始關(guān)注文化史、社會史一樣,新聞史也開始走出作為政黨喉舌的政治視域,融入了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文化的視角,這是一種視域融合的過程,同時也是多學(xué)科方式滲入的過程。
就像波蘭著名歷史學(xué)家波托爾斯基所說的:“社會學(xué)側(cè)重于現(xiàn)實世界,而史學(xué)則側(cè)重于以往的歷史過程在現(xiàn)代史學(xué)中,企圖在理論結(jié)構(gòu)和解釋上把史學(xué)與社會學(xué)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⑥
新聞史也不例外。在新聞史的研究中,要將新聞傳播視為社會運動的一個有機環(huán)節(jié),既關(guān)注新聞本體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更探究新聞與社會的外在關(guān)聯(lián),如政治經(jīng)濟、文化思想、社會生活、風俗習(xí)慣、時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聞?wù)勑侣劊兔襟w談媒體,就人物談人物。體現(xiàn)為三個融合,一是新聞與社會的融合,二是理論與歷史的融合,三是新聞學(xué)與傳播學(xué)的融合。將新聞傳播與社會生活打通,從新聞解讀社會,從社會透視新聞;將新聞理論與新聞歷史打通,歷史滲透理論,理論立足歷史;將新聞學(xué)與傳播學(xué)打通,以兼容新聞與傳播的視角,透視新聞傳播的紛繁圖景,追索其脈絡(luò),描繪其狀貌,解析其意義,探究其規(guī)律。
三、《申報》研究及史學(xué)跨學(xué)科視角
以上提到研究范式變遷,表現(xiàn)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跨學(xué)科對話,也就是“跨學(xué)科的史學(xué)研究”。“跨學(xué)科”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紐約,其最初含義大致相當于“合作研究”,而在我國最早采用的是“交叉學(xué)科”的概念。伴隨著技術(shù)的融合以及科學(xué)、技術(shù)與社會的相互滲透,科學(xué)成為一項綜合性事業(yè),方法、路徑多元化的需求,迅速推進了跨學(xué)科研究的發(fā)展。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跨學(xué)科研究隨著史學(xué)危機論的提出而興起并漸成思潮,到20世紀末達到了一個頂峰。這種在研究具體的歷史對象時吸收、借鑒相關(guān)的其他學(xué)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獲取新的視角,拓展新的思路,以開闊視野,深化理解的方法在新聞史的研究中,也已經(jīng)廣泛使用。
在中國近代報業(yè)發(fā)展中,存在最久、影響范圍最廣的當屬《申報》,她經(jīng)歷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豐富的一個時期,在78年中,《申報》歷經(jīng)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tǒng)三個朝代,又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等各個歷史階段,記錄了晚清以來中國曲折復(fù)雜的發(fā)展歷程,被人稱為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百科全書”。
對于《申報》的研究,既可以歸為個案研究,也可以看作區(qū)域研究的一部分。總的來說,《申報》研究主要包括報紙自身的發(fā)展研究、報紙與社會的研究以及報紙上社會呈現(xiàn)的研究。其已經(jīng)突破了載體層面的研究,擴散到了其承載的內(nèi)容、文化層面問題的研究,開始透析這些層面受到媒介形態(tài)的制約和推動所產(chǎn)生的變化。
從建國以來所有研究《申報》的論文來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重點已經(jīng)集中在《申報》這個媒介與近代社會演變之關(guān)系以及對于社會的展示上,比如政治輿論建設(shè)、重要時期的思想傾向和文化引導(dǎo)等。不管是愛國主義思想的傳遞,女性形象構(gòu)建和女性地位的提升,還是消費社會的形成與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分析,都加入了不同學(xué)科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定量與定性分析,文本透視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新聞史本身,而是用經(jīng)濟學(xué)、社會學(xué)、心理學(xué)等研究路徑來觀察新聞史的一個演變過程,展現(xiàn)社會全貌。
《申報》本身包含了新聞史研究的諸多要素,比如名記者,比如副刊定位、經(jīng)營理念、不同階段的發(fā)展變化,同時又包含其他學(xué)科研究的素材,比如廣告、裝幀編排藝術(shù)、歷史事件,這些都說明了新聞史研究可以尋求的視角和采用的方法,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社會學(xué)理論和人文思想的滲透。
不管歷史的發(fā)展進程是線性的還是循環(huán)往復(fù)的,重要的一點是通過歷史來關(guān)照社會,研究社會歷程以及對當今的意義。在對《申報》的不同視角的研究當中,媒介的社會屬性被不斷深入展示。但也出現(xiàn)了一點偏向,我們開始過分關(guān)注學(xué)科之外的方式而忽略了自身理論的視角。在十年的《申報》研究中,關(guān)于新聞理論視角的論文少之又少,這同時在提醒我們,采用不同研究視角本身是為學(xué)科發(fā)展服務(wù)的,如果將學(xué)科的顯著性抹殺,那么所有史學(xué)的研究就成為一種形式,一種啟示。
結(jié)語
正如當代英國知名史學(xué)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說,歷史學(xué)家向社會科學(xué)去尋找新見解和新觀點的根本原因是對歷史主義及其立場和觀點的強烈反動,那么,歷史學(xué)家首先應(yīng)當面向人類學(xué)和社會學(xué)去尋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會科學(xué)中,社會學(xué)和人類學(xué)在觀點上與歷史學(xué)最為接近。”新聞媒介作為承載社會歷史的一個重要載體,自身所富含的史學(xué)意義、社會人文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對于新聞史的研究突破已有范式,采用不同的研究視域是獲得新進展的必要路徑。
新聞史作為史學(xué)的一個分支,其研究路徑受其影響和制約,其中跨學(xué)科的視角的提出,已經(jīng)成為新聞史關(guān)照社會提供新的研究利器,學(xué)科觀念與學(xué)科研究方法上的跨越重點還是落腳于采用怎樣的視角來擴大新聞史的意義,這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采用不同領(lǐng)域的方法對其進行更深層次的剖析。□
參考文獻
①方漢奇,《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首屆中國新聞史學(xué)研討會專題發(fā)言,1992-6
②李海若,《從敘事學(xué)視角看中華民族新聞史研究范式》[D].中央民族大學(xué),2009:5
③庫恩:《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M].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9
④方漢奇,《為〈大公報〉辯誣—應(yīng)該摘掉〈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帽子》[J].《新聞大學(xué)》,2002(3)
⑤周少四,《論〈大公報〉的歷史貢獻和局限》[J].《現(xiàn)代商貿(mào)工業(yè)》,2009(16)
⑥喬志強、行龍,《從社會史到區(qū)域社會史》[J].《山西大學(xué)學(xué)報(哲社版)》,1998(3)
(作者單位:王琽琽,安徽廣播影視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徐霞,安徽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