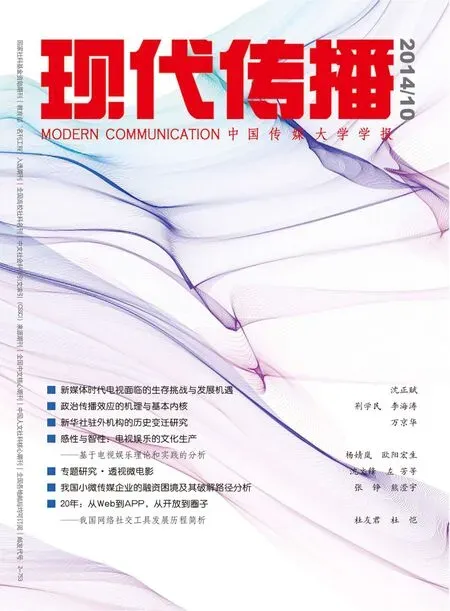跨文化視閾下《西游記》審美媒介的演進*
■ 李萍
跨文化視閾下《西游記》審美媒介的演進*
■ 李萍
數百年來,《西游記》被翻譯成多國文字,譯本總體上忠實于原著。影像時代開啟后,影視大眾傳媒發揮了雙面作用,綜合的感官享受吸引了大量受眾,同時激起了對繼承還是變革原著精神的審美討論。電子技術時代,創作者往往借用《西游記》題材講述新故事,網游則使觀眾與讀者親臨故事之中。審美媒介在對大眾欲望的迎合中不斷演進,但形式的變幻亦促使我們思考“精神”的回歸。
跨文化;《西游記》;審美媒介
《西游記》的跨文化傳播,展現出清晰的媒介演進脈絡。伴隨媒介演進,受眾的審美感受也出現了復雜的變化,從紙質的小說文本到影像再到動漫、網絡話語體系轉換,跨越的不只是媒介,還有歷史背景、文化風尚和審美風格的轉換。
一、墨香紙白間的原著意味
紙質媒介在全球范圍內持久、廣泛的使用既固化了文字的形式,又固化了經典作品的原意。雖然不可避免地烙上譯者的文化印記,但再大膽的譯者也無法拋開原著重啟新的篇章,因此,在跨文化傳播中譯作總體上保持著對原著的忠誠。
《西游記》故事因其特有的英雄神魔色彩和歷險傳奇結構在海外譯介頗豐,至今出現了二十多種語言的譯本,但大部分是節譯本,全譯本較少。對于《西游記》在域外的傳播,總體來說,東方的譯本出現時間早,一般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西方的譯本出現時間晚,早期譯本有一定基督教傾向,同時更加凸顯悟空的英雄形象。
原著《西游記》以小說示人,主要依靠文字語言敘述事件、展開情節、描繪人物、表達情感和反映現實,需要受眾具備相當程度的閱讀、理解、想象和思考能力,以此再現作者的一切意旨。由于地域及文化背景的原因,在東方文化圈內,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多國,《西游記》的愛好者多,文化認同高,理解和共鳴深。因此,《西游記》在東方世界出現的譯本,比西方早了100多年。早在公元7世紀,即唐貞觀年間,日本高僧道昭聽說玄奘取經歸國,即赴東土求學,在抄寫經文的同時,也抄錄了一些取經故事,傳入日本,在密教的佛畫中就有關于西天取經故事的描述。在日本,最早關于玄奘取經的故事幾乎都是僧侶翻譯的;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對《西游記》的早期翻譯也帶有很濃的佛教意味。①
最早的《西游記》英語片斷譯文出現在1895年,是塞繆爾·I·伍德布里奇(Samuel I.Woodbridge)翻譯的《金角龍王,皇帝游地府》,這里的地府意向基本等同于基督教里出現的地獄。1913年,由晚清傳教士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翻譯的《西游記》(譯名:《圣僧天國之行》)由上海基督教文學會出版,該版本對《西游記》的前七回和后三回進行了全譯,其余部分基本都是選譯。蒂莫西·理查德第一次讓《西游記》在英語世界有了較完整的故事框架,同時也對《西游記》的宗教意義進行了個性化的基督教式的理解。《西游記》在西方世界甚至是國外最有影響力的節譯本,應該是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A.Waley)翻譯的《猴》。一部一百回的《西游記》,在韋利筆下只剩下三十回。但譯本的上下文銜接仍然比較緊湊,文筆連貫流暢。該譯本顯然彰顯了原著追求獨立與叛逆的精神,也突出了孫悟空的人物形象和勇于拼搏、追求自由獨立的性格。因此在西方影響大、聲譽高,自發行以來,共再版五次。
綜上所述,在《西游記》的跨文化翻譯過程中,雖然由于譯者個人文化背景和觀點的不同、文學作品語言的藝術性和翻譯過程的特殊性,《西游記》在海外的譯本出現了一些宗教傾向性的變化和中心人物的轉換現象。但總體來看,《西游記》的譯本基本保持了原著的情節和特色,尤其在東方文化圈,《西游記》的翻譯更是遵循于原著。
二、綜合感官下的心靈碰撞
小說改編成影視的過程,也就是文字語言走向影像語言的過程。最初,影像語言比較拘謹地表現著文字語言,或者是對文字語言的一種直譯,即將小說書面語言所述內容用對應的影像語言呈現出來,在思維方式上也是沿用文學作品的主要模式。正如最初傳播到東亞、東南亞等國家的86年版國產《西游記》電視劇,就基本遵循了原著的模式和情節。86版《西游記》正是借助對原著的努力再現,成為迄今仍頗受歡迎的精典作品。然而,影像語言與文字語言有著不同的特性,不同特性的語言之間的轉換往往意味著變化。這種戴著鐐銬的舞蹈終究不是影像語言的特長所在,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時間的推移,對原著的過于拘泥限制了影像想象力和表現力的發揮。正如喬治·布魯斯東所說:“當人們從一套多變的、然而在一定條件下是性質相同的形式過渡到另一套形式的那一分鐘起,變動就開始了;從人們拋棄了語言手段而采用視覺手段的那一分鐘起,變化就是不可避免的”。②
逐漸地,影像語言開始對文字語言實行變異,追求用更適合鏡頭語言的方式,獨立地表達思想。例如,日本制作的不同版本《西游記》電視劇,都與原著有著不小的差異。從2006版來看,唐僧師徒四人不僅在造型上更具時尚感和視覺吸引力,性格上更接近平常人的悲喜哀愁;在中心母題上,也突破原著的限制,結合本國的文化傳統進行自由地創造。原著中從沒涉及的母愛主題,在日劇中得到濃墨重彩地展現;原著中較少提到的婚戀主題,成為日劇的主要線索之一,除了三藏法師一貫少有“緋聞”,悟空、八戒、沙僧個個在取經的同時,體驗了蕩氣回腸的愛情奇遇。原著中曾經出現的團隊意識、自我超越、勇氣與叛逆等精神也在日劇中被一再強化。
進而,影像語言開始脫離對原著的依賴,謀求自己的獨立身份,更全面地展示自己的優勢。在2001年美版《西游記》中,一方面大量運用電腦特技,原著中的蟲怪牛妖、花精狐魅等人物造型,大多進行了高科技特技處理,更具視覺沖擊力和現代性;另一方面,劇組在取景上又充分考慮了中國背景和中國元素。在內容上,美版《西游記》的故事情節還兼備了好萊塢模式的諸多要素:光明與黑暗的殊死搏斗、英雄拯救世界,以及感天泣地的經典戀情。只是這段故事完全沒有按照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來進行解讀、建構。唐僧是故事中拯救世界的英雄,觀音則與唐僧展開了一段跨越神界與凡塵的生死之戀……在美國電影《功夫之王》和《龍珠》中,雖然都出現了孫悟空的形象,但影像語言只是從小說中獲取了某種靈感,從而更好地彰顯自身的獨特魅力。正如米克·巴爾所認為的,電影并非是對小說一一對應的重現,而是對小說意義的一種視覺再現:“一部小說轉換為電影不是故事要素向形象的一對一的轉換,而是小說最為重要的方面及其意義的視覺操作。”③
影視語言的魅力是難以抵擋的。可是,在我們漸漸被影視包圍并且贊美影視語言進步之時,也有人對此提出警醒。法國作家兼批評家喬治·杜亞美這樣評價電影及各種電子媒介:“被奴役者的消遣,是給那些愚昧無知、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終日的可憐蟲們散心用的娛樂……一種既不需要觀眾全神貫注也不需要觀眾有多少智商的熱鬧場面……除了能給人帶來有朝一日會成為好萊塢明星這一荒謬可笑的幻想外,它既不能撥弄出心中的火花也不能喚醒任何希望”的。④現在看來,杜亞美的評價是有些苛刻了,大眾傳播媒介與大眾審美已經緊密聯系起來,浸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已經習慣接受它,并且,它不是不能“撥弄出心中的火花”“喚醒任何希望”。除86版《西游記》電視劇近三十年經久不衰以外,港片《大話西游》早已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日版、美版《西游記》相繼傳播到其他國家,不能不說是影視藝術在《西游記》傳播中的勝利。有人認為:“語言并不天生就比別的媒介更具有豐富的審美精神……與此相反,影像則一開始就可以進入心靈,一開始就可以產生美的感動”。⑤但或許,語言藝術或者影像藝術,本身并無高下,都是心靈碰撞的一種方式。
三、電子語境中的虛實交幻
與《西游記》的譯本和影視傳播比較而言,《西游記》的動漫、網絡傳播是與原著距離更大的傳播方式。這些動漫或網絡作品雖然仍然保留了原著的書名或者原著中人物的姓名,但事實上內容已與原著文本關系不大。電子世界的虛擬能力給了作品無限的創造空間。在動漫、網絡的傳播過程中,經過再生產的作品影像意義與原著的小說敘事意義之間幾乎找不到對應關系,完全以動漫、網絡本身的開發和推廣為本位,最多從變形化的人物和已然破碎的情節上分辨出原著的影子。如此決絕的做法使動漫或網絡版的《西游記》從根基上脫離了原著作為特定時代小說文本的意義。對于《西游記》在域外的影視改編,批評家大多以不忠實原著、惡意篡改原著的罪名大加評論,而面對動漫或網絡版的《西游記》,批評家感到語言的無力,對這些作品已經無法再以損害原著的名義進行討伐了。因為在這些作品中,原著的意義被漠視、擱置,或者被完全消解。
動漫與網絡作品在表現形式上充分發揮了電子化語言的獨特優勢,追求敘事效果的最大化。另外,動漫與網絡作品人物形象的夸張化、服飾道具的現代化、時間空間的流動化、視覺效果的唯美化等表現方式,相對小說而言,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比如唐僧師徒四人既可以在摩天大樓林立的現代城市開著汽車冒險,也可以在充滿鳥語花香的人間仙境自由活動,這樣或驚險或唯美的鏡頭運用在動漫及網絡作品中無處不在。甚至小說敘事中表現的情緒、話語都可以用動畫的方式形象地表現,比如“憤怒”一詞,動漫可以將它處理成眼睛里噴出的燃燒火焰,“害羞”一詞,可以表現成砰砰跳動的心臟。這時,抽象的形容詞就有了形象的體現。用動畫的方式將抽象名詞視覺化,進一步拉進了與觀眾的距離,顯示出電子文化產品獨特的親和力和娛樂效果。
特技或動畫效果給電子化改編帶來了巨大的娛樂享受,聲音效果則帶來了聽覺上的盛宴。動漫版的《西游記》有時會以時尚化的音樂推進情節、抒發感情和展示環境。例如,在日本動漫《西游記》中,以激烈的搖滾樂作為背景音樂,來襯托三藏法師與悟空初次相遇時兩位主人公的對立情緒。在三藏、悟空、八戒、悟凈四人第一次相遇的那個雨夜,以快節奏的打擊樂為襯托,預示了事態的緊急和人物各自的急切心情。可以說,現代音樂元素很好地襯托出動漫版《西游記》的現代情節,與變異后的人物形象相契合,給人以聽覺上的極大享受。
《西游記》的動漫、網絡作品以其符合時代特點的形式,引發受眾感官的直接反應,促進了《西游記》在全球更大范圍內的傳播,進而吸引更多大眾知道、了解、接受《西游記》及其所附帶的文化要素。網絡、動漫作品強烈的虛擬色彩,使其制作不受演員、場景、設備等傳統因素的限制,傳播亦不受傳統的時間、地點、設施等因素的影響,這增大了其傳播的可能,提升了傳播速度與效果。“網絡傳播更具有跨文化的意義,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淡化差異,強調多元文化的共享性和一致性。盡管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色彩的網絡媒體依然‘各自為政’,擺脫不了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的束縛,但網絡傳播不以滿足某類或某種文化觀念為主導,它能夠明晰而多樣化地或者說比較均衡地呈現差異,而這恰恰是為了達到人們共同使用的目的,是一個注重‘個性’共享的媒介。”⑥可見,動漫、網絡的媒介形式雖然可能在某些程度上脫離了原著,但同時也賦予了中華傳統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尤其在中華傳統文化跨文化交流方面引發新的、深入的思考。
與《西游記》十分不同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和《紅樓夢》在跨文化影像改編的情況差異明顯,這種差異本身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三國》在日本有動漫版的改編,《水滸》與《紅樓》僅有中國版的海外發行,卻極少有國外的改編翻拍。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日本動漫版《三國志》。這部動漫片共三部:分別為《英雄的黎明》《長江的燃燒》《遼闊的大地》,是日本東映動畫制作史上的最大制作,耗資14億日元,歷時四年完成。動漫經過在中國大陸實地考察,后期精心制作,其播放后被譽為最忠實原著的三國卡通,最終榮獲日本動畫最高榮譽——動畫金座獎。但是這樣“忠實”原著的改編,卻出現了其他爭議。由于它很多畫面風格與20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上海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連環畫《三國演義》很相似,有些觀眾評價說它有“抄襲”的嫌疑。抄襲也罷未抄襲也罷,忠實于原著的改編在日本和中國同時得到了認同,這中間有令人深思的審美傾向問題。
如果說影視版或動漫版的改編我們尚能糾結作品與原著的聯系,那么有一種變化發生時,我們忽然忘記了對原著的執著。這種變化就是網游的盛行。大型場景網絡游戲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充斥了網絡。網絡游戲對中國古典名著的改編即便在國內,也是個較新的研究課題。網游幾乎具備影視動漫作品的一切要素,但它又在很多方面完成了對傳統影視動漫作品的超越。由于最先進的技術的加入,網絡游戲一開始就比動漫做得更“搶眼球”。從完全虛擬的角色設計,到邀請著名演員充當形象代言,或者干脆就是從某部影視作品中衍生出來。然而,網絡游戲與傳統影視作品最大的區別還不在于此,而在于——觀眾是可以直接“走進”影像并改變其情節進程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種互動的影視作品。
對網游審美態度的思考,對于研究跨文化語境下的中國古典名著影像改編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我們除了可以在社會學意義上反思網游使參與者的身份發生錯位——以至可能走向“反現實社會”以外,還應該思考在影像技巧上越走越遠的改編與跨文化改編是否讓我們缺少了一些東西。“互動式多媒體留下的想象空間極為有限。像一部好萊塢電影一樣,多媒體的表現方式太過具體,因此越來越難找到想象力揮灑的空間。相反地,文字能夠激發意象和隱喻,使讀者能夠從想象和經驗中衍生出豐富的意義。”⑦甚至,在網絡游戲這種互動性極強的多媒體產物讓受眾投入其中的時候,根本就忘記了視覺與聽覺上的享受,而是沉浸在虛幻的個人成就之中。現實社會的浮躁伴隨著影視、網游的虛擬性使我們越來越遠離內心的寧靜,在現實社會之外,在視覺、聽覺極度刺激與虛擬的英雄氣概之后,是不是出現了更深的內心空虛?在這個時候,靜靜地閱讀一本無論什么內容的書,再步入樹林草地,看一看嬉戲的孩童,是不是恰好能彌補這種空虛,得到現實意義的審美愉悅?
回歸語言與文字,是我們在討論審美媒介之初未曾考慮到的問題,在絢爛奪目的聲光電轉換與令人震顫的鏡頭跳躍之下,當我們沉靜下來,再次回顧這一發展歷程時,我們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地發現,原來文字并未離我們遠去。《西游記》在日本、美國、韓國的跨文化改編從未脫離原著的影響,原著的精神象靈異事件一樣揮之不去,而這個靈異,正是影像前世的情人。
注釋:
① 李舜華:《東方與西方:異域視野中的〈西游記〉》,《學術交流》,2001年第1期。
② [美]喬治·布魯斯東:《從小說到電影》,高駿千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③ [荷]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頁。
④ [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范靜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頁。
⑤ 藍愛國:《影像民間及其工業化:好萊塢主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頁。
⑥ 孟威:《網絡傳播的文化功能及其運作》,《新聞與傳播評論》,2002年卷。
⑦ [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張國濤】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新形勢下中國影視文化發展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1BC02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跨文化影像改編研究”(項目編號:13YJA7510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