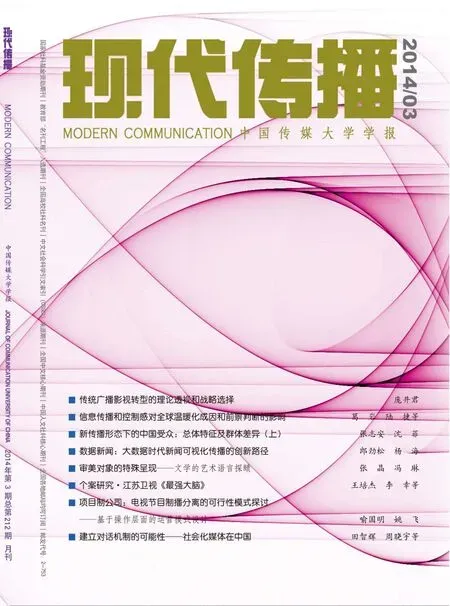外交構想力與中國在非洲國際話語權的提升*
■龍小農
外交構想力與中國在非洲國際話語權的提升*
■龍小農
中國“走進非洲”遭遇西方輿論建構的“威脅論”“新殖民論”困境,亟需提升有關非洲事務的國際話語權。外交構想力作為一種塑造國際規則和設置國際議題的能力,是軟實力的構成要素之一。提升外交構想力、積極就非洲事務貢獻外交構想并依托綜合國力將之轉化為國際機制、國際公共產品,是提升中國在非洲國際話語權的重要策略。為此,中國學者應用全球視角、中國立場加強對非洲難點和熱點問題的研究,就解決問題貢獻有創見性的外交構想;中國政府應轉變外交觀念、積極參與非洲事務,就解決非洲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創制基于中國世界秩序觀和文化價值觀之上的外交構想并付諸實施,為非洲提供國際公共產品。
中國;非洲;外交構想;國際話語權
隨著經濟實力的日漸提升,中國已步入國際政治舞臺中心;隨著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的建構,中國利益、中國存在遍及非洲,世界對中國的期待與恐懼同時增加。如何向世界展現中國,如何化解西方輿論建構的“中國威脅論”“新殖民論”,如何讓世界客觀理性、與時俱進地認識中非關系,成為當下中國國際輿論引導亟需破解的難題。破解這個難題的鑰匙,從政界到學界幾乎達成一致共識,即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或實施中國國際話語權戰略。然而,如何旋動這把“鑰匙”以盡快取得效果,各家仁智互現,各有創見。本文擬從外交構想力這一微觀角度出發,闡述對中國對非洲國際話語權提升戰略實施的看法。
一、外交構想力與國際話語權
當今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轉向,即是從以傳統的實力競爭為主轉變為以推進利益合作基礎上的話語權競爭為主,國際話語權的爭奪成為當下國際關系的新特征。國際話語權主要表現為影響如何定義、如何評價、如何處理國際事務和國際問題(如中國崛起、中國走進非洲)的能力。就中國來講,國際話語權即中國借助各種話語權建構主體,通過各種渠道與平臺,就國際事務、國際問題的處理,提出蘊含自身文化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等要素的話語,使其他國家自愿接受并認同的能力,屬于軟實力范疇。中國國際話語權建構的主體最起碼包括:政府層面、媒體層面、學界層面和社會層面四個層面。根據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的話語權理論,話語是一種具有權力建構功能的社會實踐。因此,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的落腳點是將國際事務、國際問題的處理與國際話語體系的建構在實踐中結合起來,強化中國塑造并鞏固國際機制的外交構想力。
國際話語權在國際交往實踐中通常表現為國家借助各種傳播渠道展現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貢獻能力,可概括為“議程設置”能力。要提升中國在非洲的國際話語權,就必須大力提高中國有關非洲事務與問題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貢獻能力。政治操作能力主要體現為議題設定和規則制定能力,理念貢獻能力主要體現為提出并推廣新思想和新觀念的能力。要使中國提出的話語具有國際影響力,這種話語應是中國性和普世性的結合,即基于中國經驗而具備世界價值。那么,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貢獻能力來自哪里?一個國家要為國際社會設定議題、制定規則、推廣新思想和新觀念,就需要不斷給國際社會提供可接受的外交構想,需要有用之不竭、源源不斷的外交構想力。
所謂外交構想力,即是一種立足本國利益、放眼世界格局,根據本國地位、地區和國際發展趨勢,就國際事務處理等提出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方案、建議和構想,并付諸實施的能力。外交構想力首先是一種制度創新力,提出的構想必須具有獨創性,是一種可制度化的前所未有的方案或建議。其次,外交構想力是將自己的外交構想貢獻于國際社會,并積極實踐之的能力。再次,外交構想力既是一種能力,也是潛在的權力。①外交構想力本質上表現為一個國家塑造國際規則和設置國際議題的能力。影響一國外交構想力的形成和發揮的因素主要有:參與國際事務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國家領導人和外交人員的觀念創新力;國家的綜合實力;國家所處地緣位置與國際地位;立足本國利益,從世界全局著手維護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洞察力、國際責任感與使命感等。
外交構想力首先是一種制度創新力,在于國際制度作為外交構想被國際社會采納后的機制化產物,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表征之一。這主要體現在:構想提出國的政治理念與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貫徹到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去,并能確保國際制度的規范不與本國國內基本規范相沖突;構想提出國能在國際制度框架下的議程設置上擁有相應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構想提出國在國際制度框架下擁有一定的政治動員與結盟能力;構想提出國對國際制度良好的遵守與承諾將有利于塑造負責任、重承諾的國際形象;由外交構想轉化而來的國際制度可以作為國家的戰略性資產。②因此,國際制度的提供者,通常就是國際話語權的掌控者,并經常用這種國際化的話語要求其他國家遵守這一制度,乃至批評其他國家不遵守這一制度。
環視世界各國,美國無疑是國際話語權的主宰者。美國贏得國際話語主導權除了依靠獨一無二的媒體傳播力外,貢獻外交構想并將之轉化為國際機制和國際公共產品也是其重要策略。從1917年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點計劃”規劃一戰后世界藍圖、主導國際聯盟開始,到二戰后美國主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和“馬歇爾計劃”實施,再到近年倡導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構想,美國一直積極貢獻外交構想并將之付諸實施,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成為當今國際機制的主要制定者和主導者。可以說,自從美國置身世界權力中心后,它就注重制定有形和無形的國際法規、規則和制度,力圖掌控現存的國際組織,按照其價值觀念和全球秩序觀建立或擱置相關的國際機制,來維持其國際話語權。
美國主導或組織建立,并努力予以維護的國際機制包括核不擴散機制、導彈技術控制機制、知識產權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它以經濟或軍事制裁來懲罰違反這些國際機制的國家,以維護相關國際機制的權威與效能。這些蘊含美國價值觀念和國際治理理念的國際公共產品,構成美國國際話語霸權的戰略性支撐資產,是當今美國國際話語權及影響力強大的重要基礎和表征。具體到非洲事務來說,2013年6月,在南非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新的援助非洲的構想——“電力非洲計劃”,目的在使非洲目前還黑暗的地方被電燈照亮。③這一對非援助構想與美國前總統布什提出的“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援助計劃”(PEPFAR)一脈相承、彼此呼應,將助推美國提升在非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在如何利用外交構想力提升自身對非國際話語權方面,英國也是能手。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為英國在非洲國際話語權及影響力的提升做出過重要貢獻。2002年9月,布萊爾提出西方現在經常用來批評中國在非洲“掠奪資源”的采掘業透明度倡議(EITI)。④該倡議推出后,國際社會反響積極,八國集團峰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后出臺《反腐敗和提高透明度宣言》和《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守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均通過政策建議、政策性貸款項目和技術援助等方式促進合作對象國更有效的資源收入管理。作為對非洲發展與援助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相關方,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相關政策也直接影響到非洲。根據報告,截至2013年,全球加入EITI的37個國家中,非洲國家就占到21個。莫桑比克、坦桑尼亞、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加納和加蓬等國在防止沖突、改善治理透明度和增加收入等方面都取得積極進展。⑤
2005年3月,布萊爾借英國擔任八國集團輪值主席國之機,牽頭建立“非洲委員會”。該委員會吸收了部分非洲國家前政要以及在非洲有影響力的智庫人士和聯合國副秘書長等著名人士,使其在非洲議題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當年,非洲委員會即提出報告,建議援助國每年給非洲國家增加250億美元援助直到2010年,建議全部免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債務、建立更加公平的國際貿易體系等。⑥同年召開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非洲議題正式吸收和采納了非洲委員會報告的有關建議。2010年非洲委員會報告盤點和檢討了2005年報告以來非洲的進步,包括政府治理與能力建設、和平與安全、投資于人民、增長與公平貿易等多項領域,又提出改進和推動非洲發展的多項建議。⑦
實踐表明,國際規制的制定者、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往往就是規制話語權、產品話語權的操控者。借助國際規制和國際公共產品,美英等西方國家不僅得以維持和強化自己在非洲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也得以拒斥和抵消其他新興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現今西方國家及其媒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責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漠視人權、良治”“掠奪資源、破壞環境”,其依據即是西方外交構想轉化而來的國際規制和公共產品,如“巴黎俱樂部”“采掘業透明原則”“赤道原則”等。西方國家企圖借助它們創制的國際規制和依此而生發的輿論壓力,迫使中國進入既定國際體系,接受由西方國家制定的有關非洲的國際游戲規則。顯然,由外交構想轉化而來的國際規制、國際公共產品,是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源泉。
二、外交構想力提升中國在非國際話語權
回顧中非關系發展史,也可看出將自己的外交構想轉化為提供給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是國際話語權提升的重要策略。在中非關系史上,中國并非一個外交構想力貧乏的國度。中國提出的諸多外交構想曾轉化為國際準則和國際關系理論話語,有效提升了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這正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經濟盡管貧弱但在國際上較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原因。當下中國要繼承這一傳統,充分發揮外交構想力,掌握創制外交構想、利用國際規制和公共產品建構國際話語權的能力。
1955年4月亞非萬隆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提出的界定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獲得廣大亞非國家認同,被會議通過的宣言采納,并在以后被其他國際文件采納,成為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時提出的以平等互利、不附帶條件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獲得非洲國家好評并被其他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采納。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肯尼斯·卡翁達時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同年4月,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在聯大大會上發言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闡述我國對外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國廣泛的關注。1982年12月-1983年1月,趙紫陽訪問非洲時又提出中非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同樣獲得廣大非洲國家認同。中國提出的系列外交構想,有效展現了中國當時在有關非洲問題上塑造國際規則和設置議題的能力,彰顯了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
中國在非洲國際話語權的取得,一定意義上取決于中國能夠為非洲的和平與發展提供哪些公共產品。這就要求當下中國利用外交構想力,依托日漸雄厚的經濟實力,積極為非洲貢獻國際公共產品;在相互尊重主權的前提下,積極參與非洲事務處理,為非洲事務的解決和安全機制建設,貢獻中國的外交構想并付諸實踐。作為軟實力的重要源泉,發揮外交構想力,依托經濟實力,積極為非洲貢獻國際公共產品,不僅有助于中國提升對非國際話語權,還可借助國際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減少與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對抗,讓西方接納認同中國的價值觀念,除非它不愿意搭便車享受這種國際公共產品;利用自身不斷提升的經濟實力,中國可積極聯合非洲國家、其他國家集團為非洲提供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樹立負責大國形象,提升對非國際話語權。在國際體系正在轉變之時,中國還可積極貢獻外交構想,為非洲從國際體系邊緣地帶走向國際體系中心制定路線圖,從而在國際范圍內破解西方輿論建構的中國在非“威脅論”“新殖民論”,提升有關非洲事務的國際話語權。
在認識到國際機制、國際公共產品對國家利益和國際話語權的促進作用后,中國開始逐漸從國際機制反對者轉變為融入者和利用者,并致力于國際機制體系的改革和新機制創設。隨著中國與區域和世界融合的加深、利益的不斷擴大,中國在地區和國際機制建設上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議程設定者和倡議發起者,積極貢獻外交構想,探索自主機制建設。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以及最新興起的“金磚國家”等就是例證。由中國外交構想創設的國際機制體現出平等、協商、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精神,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對國際機制的影響力和改造力,也在實踐中不斷注入獨具中國特色的國際機制建構理念和國際合作理念。這是中國對國際機制體系穩定和轉型所做出的重要貢獻,為中國在國際社會贏得了相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2010年12月23日,中國倡議并主導將南非吸收進“金磚國家”;2013年3月,南非承辦第五屆“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再次彰顯了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對中國在非國際話語權提升的顯著作用。
無論是美英還是中國自身的實踐均證明,外交構想力作為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源泉,是相對經濟和軍事等硬資源而言的軟資源和軟實力。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等國際機制與秩序的創制權是國家國際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等國際機制與秩序的創制,往往首先源于某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外交構想。某個國家或幾個國家構想的國際組織、制度或秩序若被眾多國家接受,其宗旨、原則、規則、決策程序必然體現該國的文化價值和利益取向,也就必然成為該國國際話語權的延伸和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近些年在有關非洲事務或問題處理上話語權不彰,甚至有關中非關系正常發展都無法用話語來捍衛,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對非外交構想力不足,就非洲事務或問題貢獻外交構想偏少。
因此,中國可通過提升對非外交構想力,研發有關非洲區域性的國際公共產品或者參加非洲區域性的國際公共產品提供兩種途徑,獲取國際公共產品具有的軟實力。首先,國際公共產品是國際層面的具有軟實力價值的重要國際性權力資源;其次,國家可以通過研發和參加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在國際層面獲取軟實力。⑧中國如果能夠發起并促成更多符合自己價值觀念,當然也有著與非洲或者全球共容利益相配合的國際規制,無疑將為自身贏得更多的話語權。現今,中國可在文化傳播、國際發展與發展模式創新、以及貢獻于國際新秩序構建與外交新理念、新范式的成長等領域,承擔與自身實力相適應的責任,通過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有效提升軟實力。⑨當然,制度的發起者以及制度的維護者,在享有制度給自己帶來話語權的同時,有義務及責任承擔制度運行的成本,并成為國際公共產品供應的重要一方。
三、如何提升中國對非外交構想力
外交構想力是國家軟實力的組成部分,靈活充分運用外交構想力、積極為國際社會貢獻外交構想,是提升國家國際話語權的重要策略。那么,中國怎樣才能借助外交構想力提升在非洲的國際話語權?中國應適度調整中庸之道、主動出擊提出有關非洲事務的外交構想,將之轉化為國際規制和國際公共產品。如中國發起的“中非合作論壇”倡導建構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就是提升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的成功范例,中國現有對非國際話語權,相當程度上歸功于2000年創始并持續至今的“中非合作論壇”。
正如前面所述,外交構想力是一種立足本國利益、放眼世界格局,根據本國地位、地區和國際發展趨勢,就國際事務處理等提出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構想并付諸實施的能力。考察國際關系史可以發現,影響一國外交構想力的形成和發揮的主要因素有:參與國際事務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立足本國利益和世界利益,從世界全局著手維護本國利益和世界利益的洞察力及責任感;國家領導人和人文社科研究人員的觀念創新力;國家的綜合實力及國際地位;國家所處地理位置等。根據這些限制性因素,中國可從三方面入手提高對非外交構想力,提升對非國際話語權。
首先,改變“善于守拙、絕不當頭”“辦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世界最大貢獻”的外交觀念,積極承擔國際責任。
有這么一種觀念,一直左右著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影響著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即“中國只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能夠解決13億多人口大國的富足,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極大貢獻。”一定意義上,這是中國版的“孤立主義”。誠然,中國應首先解決好自己的事情,實現國富民強、人民幸福,但隨著中國走向世界、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中國應走出“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的舊思維,提出“既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又要告之世界自己是怎樣把事情辦好,還要帶動其他國家辦好自己的事情”的新思維。
換言之,中國應把自身發展創建和積累的具有借鑒性的發展模式、價值觀念,傳播給世界供世界共享,帶動其他國家尤其是廣大非洲國家發展。這應是中國對非傳播的主要內容、提升對非國際話語權及影響力的重要支撐。除非中國不想做一個響當當的大國,否則中國就應當積極貢獻自己的外交構想,并將之轉化為國際規制和公共產品。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精辟地分析過大國與小國的不同。他極具洞見地指出,“小國的目標是國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國則命定要創造偉大和永恒,同時承擔責任與痛苦。”⑩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去承擔責任與痛苦,創造偉大和永恒。這就要求中國在相互尊重主權的前提下,積極參與非洲事務處理,為非洲事務解決和安全機制建設,貢獻外交構想并付諸實現。
其次,中國學界和外交機構應加強非洲難點和熱點問題研究,就問題解決貢獻有創見性的外交構想;就解決非洲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提出基于中國世界秩序觀和文化價值觀之上的外交構想并付諸實施,為非洲提供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
有學者指出:“在當今重大國際會議中,尤其是對重大國際或地區熱點問題討論時,以美國為主導的、以西方價值觀為核心的理論和學術話語體系,往往成為大多數當事國判斷是非的理論依據。”(11)因此,中國對非外交構想力的提升必須以中非問題、非洲問題為導向,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以及微觀、中觀和宏觀的角度,就中非關系發展、非洲問題解決進行深入研究,創新理論創新話語,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依托中國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的優勢,將之機制化、制度化、區域公共產品化。如此,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才有堅實的基礎。
研究非洲難點和熱點問題,旨在了解非洲對哪些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有需求。非洲有哪些難點和熱點問題?貧窮問題、災荒問題、債務問題、腐敗問題、安全問題、環境問題、能源問題、基礎設施問題、教育與公共衛生問題等發展問題一直困擾著非洲復興,都需要世界各國貢獻外交構想去解決。中國學界和外交部門可根據非洲發展需要、自身能力范圍,分清輕重緩急先后順序,逐一研究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構想。加強對非洲發展問題的對策研究,就如何解決問題提出系統可行的方案與建議,還可以主導有關非洲問題的學術話語權,提高中國有關非洲問題的話語質量,充實話語內容。
第三,洞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遷的趨勢,協調好中國走進非洲后與非洲主要經濟體、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其他新興國家在非洲的利益關系。
隨著非洲變成“希望的大陸”和“新的經濟增長極”,傳統大國和新興國家紛紛重視與非洲發展戰略伙伴關系,非洲大陸成為國際話語權競爭的主戰場。中國應洞悉非洲本身的政治經濟格局,更應熟知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在非洲的政治經濟格局,在這基礎上提出與非洲國家、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互利合作的外交構想,掌握話語主導權。如與歐盟、非盟建立三邊合作機制,與美國、非盟建立三邊合作機制等。甚至可以提出更宏大的外交構想,倡導建立中國、歐盟、美國和非盟的四邊合作機制。事實上,美國、歐盟的對外政策制訂者們已在提出類似的外交構想。如2008年10月17日,歐盟委員會正式推出“歐盟、非洲與中國:走向三邊對話與合作”的政策文件,提出了開展中、歐、非三邊合作的機制構想和政策建議。中國應掌握主動權,而不是被動接受他國提出的外交構想,被動地澄清西方輿論對中國在非活動的誣蔑;中國也應跳出中非關系、站在國際格局變化的高度創制外交構想,協調好與利益攸關的關系。
四、結語
提升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是保障中非關系健康發展的需要,是捍衛中非發展成果的需要,而強化中國對非外交構想力則是提升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的重要途徑。中國創制的有關非洲事務的外交構想付諸實施并轉化為國際機制、國際公共產品,將為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及影響力的掌控與提升,提供堅實的文化價值理念和國際制度基礎。
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的嬗變,以國際機制為主的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正處在新一輪調整與變遷的張力中。中國應積極利用自身不斷增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創制外交構想、參與或主導新的國際公共產品的設計與提供,從而為中國置身國際舞臺中央、構建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提升國際話語權。這就需要中國外交從被動應對型轉變為主動出擊、求變求進的積極型外交,提出基于中國世界秩序觀和文化價值觀之上的外交構想并付諸實施。
與此同時,非洲本身的政治經濟權力格局、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在非洲的政治經濟權力格局也正在發生結構性轉移。這兩個轉移使非洲需要外來力量提供并維持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借助這一千載難逢的契機,中國應強化對非外交構想力,積極倡導針對非洲的國際雙邊、多邊合作機制,為非洲問題解決創制構想,提供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中國如能抓住這兩個轉移,就雙邊合作、多邊合作、非洲問題解決機制提升對非外交構想力,必將提升中國對非國際話語權。
注釋:
① 龍小農:《外交構想力與軟權力的形成》,《國際觀察》,2005年第5期。
② 蘇長和:《中國的軟權力——以國際制度與中國的關系為例》,《國際觀察》,2007年第4期。
③ 高原:《奧巴馬宣布新的援助非洲計劃》,2013年7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7/01/c_124933436.htm。
④ 該倡議通過鼓勵以石油、天然氣和采礦業為收入的國家更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和加強責任追究制,以減輕因理財不善而引起的潛在負面影響,從而使這些收入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⑤ Progress Report 2013 Beyond Transparency:http://eiti.org/files/EITI-progress-report-2013.pdf.2013-07-08.
⑥ Our Common Interest,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frica:http://news.bbc.co.uk/2/shared/bsp/hi/pdfs/11_03_05africa.pdf,2013 -07-6.
⑦ Still Our Common Interest,Commission for Africa Report 2010,http://www.commissionforafrica.info/wp-content/uploads/2010/09/cfareport-2010-full-version.pdf,2013-07-10.
⑧ 吳曉萍:《從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看大國軟權力的獲得》,外交學院博士論文,2011年6月,第128頁。
⑨ 王雙:《國際公共產品與中國軟實力》,《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4期。
⑩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81頁。
(11) 周凱敏:《加強國際關系領域中國話語體系建設提升中國話語權的理論思考》,《國際觀察》,2012年第6期。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傳播研究院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國濤】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在非洲的國際影響力與國際話語權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2CXW021)、中國傳播能力建設協同創新中心國家傳播體系研究平臺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