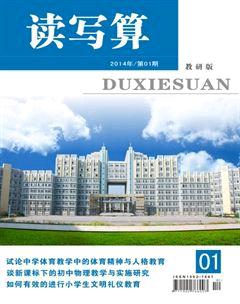翻譯的歷史功績和再創(chuàng)造(改版)
郭永瑛
摘 要:語言研究是二十世紀以來哲學(xué)、文化研究的核心,而翻譯研究又是語言研究的重中之重。語言是有生命的,有些語言之所以依然生機勃勃,是因為有很多因素存在。首先涉及到此種語言的使用人口和這種語言的傳播范圍,涉及到這種語言自身是否能有利地保持其自身的活力,是否能保持其自身的開放性等。
關(guān)鍵詞:語言;翻譯賦予語言活力;歷史功績;再創(chuàng)造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biāo)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01-006-01
一、翻譯賦予語言新的活力
談到翻譯,首先要談到語言,那么,什么是語言?這是一個較復(fù)雜的概念。哲學(xué)家們說語言差不多就是人本身,就是能夠證明人活著、存在著。?那么,什么是人的存在?存在就是指可說的那部分,把想說的事情用語言說出來,它能讓人知道世界是什么,世界將會怎樣等等問題。20世紀后期,德國語言學(xué)家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中,對現(xiàn)代語言學(xué)做了系統(tǒng)的描述。他說語言是一個用于命名和表意的符號系統(tǒng)(包括文字),他把語言分成了兩個層面。當(dāng)我們說話的時候,一個是概念,為所指,如:手表擺放在那里,那個是手表,手表就是語言符號本身叫所指;我們把所說的事或命名的對象叫能指;?如:人是所指的話,具體是指誰?如郭達就是能指。還有血壓升高,就是所指,?憤怒后血壓就會升地更高,這樣的一個狀態(tài),就是能指。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從根本的意義上說,沒有太大的區(qū)別,關(guān)系是任意性的。人類語言是很復(fù)雜的,為什么有那么多語言?有人類文明以來,人類文明的標(biāo)志就是有了語言,有幾千種語言,很多語言都消亡了。到目前為止,在世界上還有幾十種語言在消亡。有些語言是口頭上的,沒有語言文字,若沒有文字,將消亡得更快,尤其是小語種。要保存這種消亡的語言,是語言學(xué)家的使命。任何語言在千百年中都包含著一種豐富的、獨特的東西,它具有獨特的看法、獨特的命名和獨特的表達方式,這些都是人類的成就。語言消亡是人類的一大損失,假如一萬年或十萬年以后,漢語消失了,意味著李白不再有人知道,紅樓夢等沒有人能看得懂了,那么多智慧都消失,意味著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化都消亡了。
語言是有生命的,有些語言之所以依然生機勃勃,是因為有很多因素存在。首先涉及到此種語言的使用人口和這種語言的傳播范圍,涉及到這種語言自身是否能有利地保持其自身的活力,是否能保持其自身的開放性等。因此,一種語言它自身能否隨時接納新的經(jīng)驗,能否和其他的語言開放地交流,即與時俱進,隨著時間的進步而進步,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是考驗?zāi)撤N語言是否生機勃勃的關(guān)鍵。語言研究是二十世紀以來哲學(xué)、文化研究的核心,而翻譯研究又是語言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語言翻譯推動了文化和時代的發(fā)展
翻譯涉及兩種:一種是時間意義上的翻譯,如古人類如何說話,古語言需要翻譯去破解。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種圖畫符號),在1822年——1824年間被法國學(xué)者商博良在研究羅塞塔石碑時破譯了。我國的西夏文字到目前為止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沒有被破譯。但有相當(dāng)多的古文被翻譯出來。如古代突厥語族語言的文明史,特別是鄂爾渾河流域的古代突厥碑銘文獻,還有用回鶻文寫成的《玄奘傳》、《金光明經(jīng)》、《彌勒會見記》以及喀喇汗王朝時期的《突厥語大詞典》和《福樂智慧》,都是古今翻譯家們的杰作。大約九、十世紀是回鶻文翻譯經(jīng)文的鼎盛時代,回鶻文其佛經(jīng)主要源于三種語言:(P07)其一,《彌勒會見記》譯自古代庫車語和焉耆語;其二,《玄奘傳》、《金光明經(jīng)》譯自漢文和藏文。因此,可以推斷,突厥人、回鶻人從公元前十世紀就跟漢民族接觸,通過翻譯交流,互相學(xué)習(xí)、互相溝通,以達到人類社會生存、發(fā)展之需求。第二種是空間意義上的翻譯。這個翻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作用。漢語翻譯經(jīng)過兩次大的浪潮,一次,歷史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僧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帶來了大量的佛經(jīng),進行翻譯,一直持續(xù)到唐朝,如此持續(xù)了幾百年。西游記實際上就是翻譯家的故事,唐僧就是一個翻譯家,他將大量的佛經(jīng)進行翻譯,不僅僅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書,而是給我們帶來了大量的新的思維。包括思維這個詞都是從梵文中翻譯過來的。新的思維,新的精神不是原來漢語中就有的,它是從印度佛經(jīng)上的梵文中翻譯過來的。給漢語增加了許多新的色彩,新的內(nèi)容,也增加了新的日常用語,由此使?jié)h語變得更加豐富。唐僧佛經(jīng)的翻譯為推動文化時代的發(fā)展,也起到巨大的作用。
三、翻譯具有再創(chuàng)造性
人類的分析、判斷都是運用語言來進行創(chuàng)造,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人類還有內(nèi)心語言,也是一種創(chuàng)造。一種命名接納其它語言的時候,就有了主動權(quán),因此,也可以說是語言創(chuàng)造了世界。當(dāng)然翻譯就是語言的再創(chuàng)造者。當(dāng)在一種語言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文學(xué)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種語言中去時,為了使接受者能產(chǎn)生與原作同樣的藝術(shù)效果,譯者就必須在譯語環(huán)境里找到能調(diào)動和激發(fā)接受者產(chǎn)生相同或相似聯(lián)想的語言手段。這實際上也就是要求譯作成為與原作同樣的藝術(shù)品。在這種情況下,文學(xué)翻譯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取得了相同的意義,文學(xué)翻譯也已顯而易見不再是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zhuǎn)換,而是一種創(chuàng)造型的工作。
當(dāng)代翻譯研究也已經(jīng)證明,翻譯不僅是一個很崇高的職業(yè),而且還是一個充滿巨大創(chuàng)造性的職業(yè)。翻譯者的創(chuàng)意是難以否定的,翻譯的過程就是創(chuàng)造的過程。當(dāng)然沒必要一定要去強調(diào)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要超過原創(chuàng)者,但是至少可以說,譯者與原創(chuàng)者一起會成為一種新的文字和新的文化中的新作品的共同擁有著,具有同籌的創(chuàng)意,而且客觀事實也是如此。翻譯工作的創(chuàng)造性應(yīng)當(dāng)?shù)玫匠姓J,同時翻譯工作創(chuàng)造性的特殊性也應(yīng)得到理解。美國學(xué)者對翻譯者的特殊創(chuàng)造性作了這么一種概括性描述: "翻譯者的技巧是一個深刻的矛盾體,這種技巧是在兩種沖動形成的極度張力之間得以發(fā)揮的:一方面有"依樣畫葫蘆"的沖動,另一方面又有適當(dāng)再創(chuàng)作的沖動。"這部分學(xué)者都以為這是翻譯研究的一大進步,因為單從語言學(xué)角度研究翻譯,其實就是研究翻譯的原語和目的語的轉(zhuǎn)換,這就對翻譯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強調(diào)譯者的譯品,譯者不再是從原語到目的語的簡單的轉(zhuǎn)化者,他有再創(chuàng)造的權(quán)利,可創(chuàng)造出原文沒有的東西。
參考文獻:
[1] 詹姆斯·C·斯托克 王桂英.社會的標(biāo)志—在語言消亡論者筆下的英國語言.網(wǎng)絡(luò)文.
[2] 買提熱依木.沙依提,僧古.薩里.金光明.經(jīng)翻譯方法談,民族翻譯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