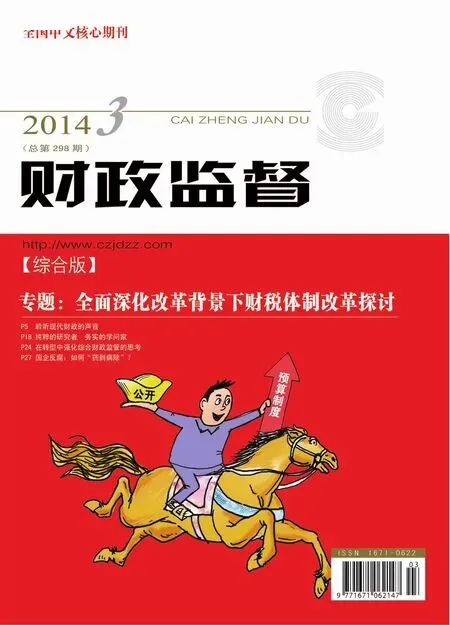新形勢下我國地方稅系構建的現實選擇
●李建軍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是當前經濟社會改革的最強音。重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建立完善的地方稅體系是規范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支撐和保障。“營改增”的加速推進倒逼分稅制和地方稅改革,當前我們已進入分稅制和地方稅系重構的歷史關口,直面地方稅系重構的重大問題,科學選擇地方主體稅種,建立合理、穩定的地方稅體系迫在眉睫。
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政府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其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有效履行需要相應的財力保障。縱觀世界各國,地方政府的財力保障都是通過地方稅、共享稅(共享稅基、稅收分成等)、轉移支付三大途徑實現的。以稅種和稅收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劃分和分享為特征的分稅制,是中央與地方財力分配的主要內容和機制,但應該看到,在一個以經濟社會政治的統一、社會公平穩定為價值追求,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分稅制是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規范、地方政府財力保障的基本框架,但不是全部,轉移支付制度同樣是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規范的重要支柱。由于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結構極為不均衡,在全國統一分稅制下,地方主體稅種和地方稅系不可能完全支撐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需要。因此,在地方稅系構建和地方主體稅種選擇中也不能要求所構建的新分稅制下,地方主體稅種和地方稅系的稅收收入能夠支撐地方法定支出責任,應保障在中央與地方分稅制的初次財力分配占比中中央的優勢,以發揮中央宏觀調控、均衡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表1 中央與地方劃分稅收的參照辦法
地方稅和共享稅的地方部分是地方稅系的兩大組成部分。2012年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三大共享稅約占地方稅收收入的35%,營業稅占約地方稅收收入的33%,除營業稅之外的契稅、土地增值稅、城建稅、房產稅、耕地占用稅等地方稅約占地方稅收收入的32%。隨著“營改增”的深化,地方失去了作為最主要主體稅種的營業稅后,選擇地方主體稅種、構建地方稅系,應結合稅制改革,根據稅種屬性來選擇地方主體稅種、構建地方稅系。根據馬斯格雷夫的政府間稅收劃分原則:以收入再分配為目標的累進稅、穩定經濟手段的稅收、地區間分布不均的稅源、課征于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稅收等應歸中央;具有周期穩定性的稅種,依附于居住地的稅收,課征于非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稅收應劃給地方。基于稅種屬性和特點,世界銀行(1997)給出了政府間稅收劃分的參照性建議(如表1)。
目前,我國增值稅為最主要的共享稅,但增值稅一方面具有順經濟周期性、地區間分布差異較大,另一方面,增值稅為地方主要收入來源可能加劇地方政府注重投資、重產出輕效益的粗放型增長,因此包括原征收營業稅改征為增值稅的部分,所有增值稅應全部劃為中央稅。企業所得稅雖然理論上具有順經濟周期性和流動性應劃為中央稅,但將企業所得稅作為地方重要的共享稅收入,一方面相比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對地方政府行為的負向激勵小,有助于促使地方注重經濟績效、改善社會經商環境,另一方面,將企業所得稅作為地方共享稅符合國內現實,也是國外常見做法。一般來講,個人所得稅具有收入再分配效應和流動性,理論上應歸屬于中央稅更好,但是在個人所得稅稅制統一情況下,將個人所得稅作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種并不會妨害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及其功能的實現,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個人所得稅制的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規模將越來越大,在稅種有限、地方稅主體稅種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將個人所得稅作為地方的共享稅是現實的有效選擇,從國外的實踐來看,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家地方稅收入中都包括個人所得稅(其中,日本地方為個人居民稅)。
除了共享稅收入外,地方稅體系中還需要獨立的地方稅種以支撐地方財力,促進公共品受益和負擔的公平、地方自主和主動性的發揮。理論上地方稅的征收對象應是非再分配的、非流動性的、不可轉嫁的和非周期性的稅種。反觀我國稅收體系現狀和發展,真正具有成長為地方稅主體稅種的只有財產稅(主要為房產稅)和消費稅。以房產稅為代表的財產稅由于其稅基的非流動性、符合公共服務受益和負稅的匹配性,且以居住地為基礎,是公認的具有成為地方主體稅種潛力的稅種。雖然目前房產稅占地方稅收收入比重仍很低,2012年僅為2.9%,但我國房地產業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商業和居民自用房產規模龐大,并依然增長迅速。據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2年底城鎮人均住房面積32.9平方米,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3》顯示,全國家庭平均住房面積為100平米,人均30平米,超過10%的家庭有兩套及以上的住房,住房存量巨大、配置不均衡,若改革房產稅、將居民自用住房納入征稅范圍,房產稅有成為地方主體稅種的現實可能性和可行性。
零售環節繳納,消費者為納稅人的消費稅是以居住地為基礎的稅種,稅基來源于當地居民消費,居民消費又和居民所在地地方政府提供的消費設施、公共服務聯系密切,同時消費所產生的外部成本主要是由消費地承擔,因此消費稅還體現受益稅的特性,理論上比較適合作為地方稅。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不少國家都將零售環節征收的消費稅或銷售稅作為地方稅,如美國、德國、日本和加拿大。目前,我國消費稅主要在生產環節征收,征收范圍非常窄。一方面,應實現消費稅消費環節征收,使消費地成為消費稅收入的法定獲得者,平衡地區間消費稅的分配,體現消費稅由消費者繳納和負擔的特征,更好地發揮消費稅的消費引導調節功能,并使稅收和地方政府行為激勵相容,促使地方消費驅動型增長方式的實現。另一方面,應擴大消費征收范圍,使消費稅逐步成為征收對象豐富的 “大眾稅”。首先,對高檔奢侈品,污染環境強、資源消耗多,負外部性強的商品和服務納入征稅范圍,并適用高稅率;同時改革汽油、啤酒等消費稅的計稅方式,實現從量計征到從價比例計征的轉變,增強稅收彈性;并逐步將部分非生活必需品、非鼓勵性商品服務納入課稅范圍,使消費稅成為地方稅系的主體稅種之一,成為地方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應在穩定我國宏觀稅負的基礎上,推進“消費稅擴圍”改革,在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提高零售環節消費稅比重的同時,要真正降低增值稅的平均稅率和稅負,實現宏觀稅負穩定,貨勞稅中增值稅和消費稅比重的一降一升。
承上所述,可初步勾勒出我國地方稅系構建的一個可選擇方案:“消費稅+房產稅”兩大地方主體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兩大共享稅收入,以及其他多個零星小稅種。與此相對應,我國主要稅種在中央和地方間未來選擇的分配結構可簡要概括如表2。

表2 主要稅種在中央與地方間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