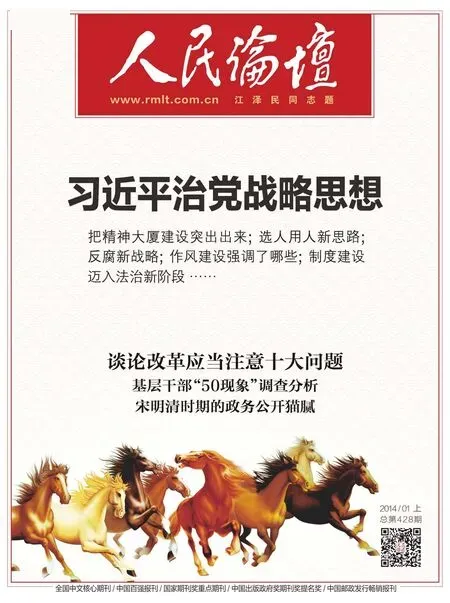透析基層干部“50現象”
——“50干部”是寶貴的社會財富
王明杰 潘 磊
透析基層干部“50現象”
——“50干部”是寶貴的社會財富
王明杰 潘 磊
“50”對基層干部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既意味著其步入閱歷豐富、處事成熟的階段,又無奈地遭遇了晉升的“天花板”困境
五十歲正是“知天命”時,然而,目前我國基層干部隊伍中卻存在著一種所謂的“50現象”。“50”對基層干部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既意味著其步入閱歷豐富、處事成熟的階段,又無奈地遭遇了晉升的“天花板”困境。
“50現象”緣何產生
價值觀偏差。從歷史原因來看,基層干部“50現象”無疑是“官本位”思想作祟的結果。在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的“官本位”思想潛移默化地給基層干部進行了“洗腦”,引導其把當官看作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并以官職大小、官階高低作為衡量其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的標準。而且一些干部認為當官、尤其是當高官可以“封妻蔭子”,可謂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因此,追求晉升幾乎成為每一個干部的最大追求,而原地不動是所有干部的最大忌諱 。然而,當基層干部處于“50”這一階段時,由于基層干部基數大,職數少,很難再有發展空間。現實和意識形態的強烈反差使得“50干部”產生落寞和失望,工作的熱情逐漸減退,產生工作倦怠。一些“50老干部”看到年輕干部得到“火箭式”提拔,心里就覺得不服;想到自己即將退休,曾經的名與利將逝去,心里就覺得不值;看到一些干部貪污腐敗卻沒有落馬,心里就“蠢蠢欲動”。于是產生一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趁在位時能撈一把是一把”的失衡心理。一些信念不堅、意志薄弱的“50干部”開始了小貪小腐,“不給好處不辦事”,最后晚節不保。
激勵機制不到位。一是晉升機制不完善。片面理解干部年輕化,晉升年齡上“一刀切”。近年來,一些地方、部門片面理解干部年輕化,晉升年齡上采取“一刀切”,“唯年齡是舉”,例如35歲以上的就不再提拔進鄉科級班子;40歲以上的不再提拔進縣處級班子;縣以下的正職局長、鄉鎮長52歲、副職50歲退居二線,目的就是為后面的年輕人“讓路”。這種干部任用年齡上的“一刀切”,導致“三十當官,四十靠邊,五十賦閑”現象發生,大批工作經驗豐富、年富力強的“超齡干部”無情地被剝奪了晉升的機會,被迫閑置起來,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面對“超齡”,一些優秀的中年干部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劉俊生教授就曾說過“在選拔干部時,要防止在干部選拔上簡單地以年齡劃線,注重使用各個年齡段的干部,特別是多用一些熟悉情況、經驗豐富、口碑好、善于做群眾工作的干部,調動整個干部隊伍的積極性。”
二是薪酬激勵效果不足。我國基層公務員是公務員中工作最繁忙、工作量最大、最累的一個群體,但是大多數基層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整體偏低,有些地方遠遠低于當地的平均工資。很多基層干部發現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大半輩子,到頭來僅僅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開支,獲得的回報遠遠彌補不了付出。這必然會帶來“50干部”心理落差和消極情緒,影響工作積極性。
三是績效考核難以發揮激勵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對公務員的考核主要包括德、能、勤、績、廉五方面,重點考核工作實績。但我國公務員實行固定薪級,工資與績效掛鉤不充分。他們包括工資在內的經濟收入和其他福利待遇幾乎都與行政級別相對應,這就導致績效考核流于形式,平均主義盛行,難以真正發揮其激勵作用。
人文關懷偏少。眾所周知,人的需要引發動機,動機引起行為,需要則是人們各種行為的出發點和基礎。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交往需要、尊重的需要與自我實現的需要。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看,我國基層干部雖然年屆五十,退居二線,但還是有著較強的社會需要和尊重需要,希望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和支持。隨著經濟的發展,當官不為民做主、貪污腐敗、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的不斷涌現,使得公眾越來越不相信政府,政府公信力下降。公眾很可能會無限放大與人民群眾面對面的基層干部在日常工作事務中的瑕疵,不支持也不配合基層干部的工作。基層干部渴望社會大眾關心和支持與基層干部“污名化”之間的矛盾無疑加劇了“50現象”的產生。
引導“50干部”走出困境
第一,關鍵是完善公務員晉升機制和激勵制度。繼續完善從基層選拔干部的機制,讓更多信念堅定、勤政務實、清正廉潔的基層干部走上領導崗位,這樣不僅能提高行政隊伍的整體執政水平,還能夠提高干部的社會存在感。要廣泛推行公推公選競爭上崗機制和差額推薦、差額考察、差額醞釀、差額票決的基層干部選拔機制。一些省份先后提拔縣(市)委書記、鄉鎮黨委書記到省直廳局任職,一些地方從村官中選拔鄉鎮干部,就是干部人事制度的完善;正確理解并執行干部年輕化方針,打破晉升年齡上的“一刀切”。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是當前干部隊伍的整體傾向,但年輕化的本質是隊伍的精神狀態和能力的與時俱進。如果在年輕化問題上搞“一刀切”,可能導致干部隊伍年齡結構的不合理,影響年輕干部的成長和中老年干部的工作積極性,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影響干部隊伍的穩定;采取靈活的晉升和激勵制度,對于在某地或某一崗位連續工作很長時間的優秀基層干部可以通過“低職高配”制度來延長他們的“政治生命”;改革待遇與職務層層掛鉤的模式,強化績效考核機制,重視個人基層工作經歷。如果能完善目標責任考核機制,注重考核工作結果,將考核項目進行科學的細化和量化以便提高可操作性,更加重視個人基層工作的經歷,在績效考核和個人工作資歷的基礎上考慮基層干部職務晉升和福利待遇問題,基層干部工作積極性將大大提高。
第二,強化行政問責制度,以黨紀和法律鞭策基層干部,用剛性的規范引導基層干部的行為導向,加強行政效能監察,完善對干部的紀檢監察機制。一旦基層干部觸犯黨紀國法,要嚴懲不貸。
第三,“50干部”自身要不斷加強對理論的學習,創新思維方式,提高個人能力水平。“50干部”要摒棄“官本位”以及不健康的競爭思想,同時也得加強自身的理論學習。
第四,建立健全干部交流輪崗機制。針對不同類型的基層干部要實行不同層次的輪崗交流,以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交流原則,做好黨政干部、國企事業單位人員、高校科研人員三支隊伍之間的交流。本著干部交流同領導班子調整、干部培養結合起來的理念,既要有機關和基層的縱向交流,也要有職能部門之間的橫向交流。如工作能力突出的基層干部可以去機關單位拓展視野;而工作懈怠、作風懶散的干部要從重要崗位交流到一般崗位;工作出現嚴重問題的干部要進行降職降級交流。
第五,許多基層干部一直堅守在黨執政前沿,他們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同時清正廉潔。對于表現優秀的基層干部,社會要給予充分肯定。這樣不僅能夠淡化“污名化”對基層干部的消極影響,也能引導部分“50干部”重新定位,在崗位上繼續發光發熱。
當前中國正處于政府向市場、社會、地方放權的關鍵時期,同時也處在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治理模式的多元化給基層干部提出了更多的挑戰。基層干部處在黨執政的最前沿,大部分擁有豐富的經驗、勤政務實的作風和理性的思維信念,少部分在50歲上下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消極情緒,但是通過正確的價值引導、制度規范和公眾關注,“50現象”干部群體必然能走出困境,繼續在崗位上發光發熱。
(作者分別為中國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講師)
責編/徐艷紅 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