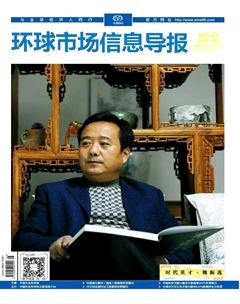刑事立法的正當性依據探析
俞彬彬
作為國家創制罪刑規范、規定犯罪與刑罰的一項重要活動,刑事立法的正當性問題由于其對象的特殊性而備受關注。該文即試圖從形式與實質兩個層面出發,以程序與實體為角度,圍繞刑事立法權來源、刑事立法主體、罪刑規范內容等三個方面的問題,對我國刑事立法的正當性依據進行探析。并從我國刑事立法實踐著手,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有機結合起來,為法定刑的合理制配提供有力的依據,實現罪刑均衡。
馬克思曾指出:“如果認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況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實際的幻想。法官只能夠絲毫不茍地表達法律的自私自利,司法只能夠無條件地執行它。” 刑法執定罪量刑之柄、操生殺予奪之權,在一國法律體系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其正當與否關乎每一國民的切身利益,須慎而重之。正當性是指某種事物存在的合理根據。刑事立法的正當性,是指立法者對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作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設定時,應當符合正義觀念、具有內在合理性的根據。
一、國家刑事立法權來源之正當性
根據洛克的自然法理論:在法律產生之前,人們處在一種自然狀態中,這種自然狀態并不是放任和無所顧忌的,而是存在一種人人遵守的“自然法”即人類的理性。為了約束所有的人不侵害他人的權益,人人都可以執行這種自然法。 然而,人性并不是自覺的,起初為了人類共同的發展,人們可能會自覺遵守“自然法”。但是,自然法內容模糊不清,私人之間的處罰難免濫用。因此,人們用法律來指導如何行為,同時尋求一個絕對權威且公正的機構來進行裁判與刑罰。
經過霍布斯、洛克的發展,盧梭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社會契約論。根據社會契約論,在國家和法律出現之前,人類處在自然狀態之中,基于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與本能,人類處于爭斗沖突之中。為了實現社會群體內部的有效秩序與最大共同利益,人們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達成契約,組建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或者政府,并將自己的一部分權利——如立法權、管理權、刑罰權等讓渡于這個政治共同體。因此,國家刑事立法權的取得是基于一國內全體公民的自覺意志,國家從公民的同意、承諾中獲得其權力來源的正當性以及要求公民信守契約、服從其權力行使的正當性。
當然,自然法理論與社會契約論雖然為國家獨享刑事立法權提供了正當性依據,卻也對國家刑事立法權的行使提出了有限性的要求,即國家刑事立法權來源于公民契約的當然結果是受節制的。本文在此不予贅述。
二、刑事立法主體之正當性
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國家權力必須依賴于具體機構來行使。在現代民主政治國家中,具體行使刑事立法權的主體往往是議會或權力機關 ,那么這些機構行使刑事立法權的主體資格來自于哪里?其正當性依據又在哪里?我們認為,人民主權原則與代議民主制度為其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作為現代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人民主權原則承認并強調國家權力屬于人民,而其具體的實現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民主,二是間接民主。雖然直接民主更符合人民主權原則的基本要求,但是考慮到立法成本與效益,現實可行性等因素,大多數國家都選擇采用選舉制、代議制的間接民主途徑。具體而言,西方國家往往采用議會制,議會的組成人員一般由該區域或國家的公民直接選舉產生,代表民眾制定法律、討論并決定國家方針政策的制定與施行。而在我國,根據《憲法》第2、3條的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權力機關,代表廣大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并有權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
不過,關于我國的刑事立法主體問題,有一點要引起我們的重視。由我國《立法法》第7條規定可知,刑事法律的制定、修改權歸屬全國人民大表大會,全國人大常委會為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為彌補全國人大會期短、召集難等缺點,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發揮補充、修改刑事法律的輔助功能,但不得與原有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這一規定賦予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靈活性與自主性,同時也為它的權力越位埋下伏筆。以《刑法修正案(八)》為例,其調整了刑罰結構、新增了若干罪名,也修改了刑法總則中的刑法基本制度,這引起我們對合理正當地行使刑事立法權的更深思考。
當然,在具體進行刑事立法實踐的過程中,還應當遵循一定的方法或程序,以保證立法結果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增強國民認同感,以使得立法能得到民眾自覺的遵守和施行。這些措施主要包括立法前的公眾參與機制、立法聽證機制,立法中的嚴格程序規則以及立法后的評估機制等等。
三、罪刑規范內容之正當性
刑事立法權來源、刑事立法主體的正當性是否就必然能保證刑法內容的正當性?法律實證主義對此持肯定觀點。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辦的《環球市場信息導報》雜志http://www.ems86.com總第577期2014年第45期-----轉載須注名來源其強調法律正當性來源的自洽性和絕對性,認為形式意義上的正當性就是法律正當性問題的全部內容。 然而,歷史告誡我們,法律的正當性若僅求證于自身,往往會成為暴政的堂皇借口。我們認為,法律的正當性是無法自洽的,法律僅具備形式正當性不夠,更應在內容上具有實質正當性。尤其對于刑法而言,罪刑規范關乎個人的財產、自由甚至生命,更應當確保其內容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犯罪圈”劃定之正當性。在良好處理自由與秩序的矛盾、合理劃定“犯罪圈”的大小的過程中,即在認定某一行為是否應當被認定為犯罪納入刑事制裁的范疇時,有以下幾個原則可供我們遵循以實現正當性:
社會危害性原則。社會危害性原則來源于英國學者約翰·密爾提出的危害性原則。其認為自由的核心有兩個基本原則:(1)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個人就有完全行動的自由,其他人不得對這個人的行為進行干涉;(2)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接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 社會危害性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國內社會主文化群體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利益追求,形成一套共同的善惡判斷標準,并以此標準對某一行為在刑法上作出的價值判斷。
隨著民主法治發展,“法益”概念被刑法學者引進并大加推崇,法益侵害性逐漸取代社會危害性成為我們判斷某一行為成立犯罪、是否應當納入刑事制裁的首要標準。不過,法益侵害性與社會危害性的區分只是所指對象的傾向不同,其內容與標準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將法益侵害性作為論證刑事立法正當性的依據時,同樣適用前文對于社會危害性的界定。
謙抑性原則。謙抑性原則又稱為“最后手段原則”。所謂謙抑,即是指“只有行為的違法性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其他部門法已不足以制裁、遏制該行為時,才能認為該行為具有刑法上的違法性,才能動用刑法這一 ‘最后手段,否則,行為只具有一般的‘違法性而不具有‘刑事違法性‘。” 質言之,在某一行為領域,只有當民事、經濟、行政等刑法前置性手段均不足以制裁不法行為、保護相對人的合法利益時,作為補充手段的刑法才能得以有限介入。
刑罰配置之正當性。實現刑罰配置的正當性即要求刑事立法遵循、體現罪刑均衡原則,實現“罰當其罪”,以得到民眾的廣泛認同。那么這里的“罪”指的是什么?我們認為,正當的刑罰配置應當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為基礎,同時考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以確定相應的刑罰。
因此,我們在踐行罪刑均衡原則,考察罪刑相當性的時候,應當善于從相統一的原理出發確立罪刑關系。在規定相應犯罪與刑罰時,以報應為基礎,同時考慮一般預防的需要,并在有關的量刑制度中規定體現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從輕或者從重的情節, 以實現刑罰的正義,使之得到民眾認同,以更好地發揮其教育、矯正功能。因為只有刑罰得到規制對象、即犯罪人的認同,才能使犯罪人受到教育,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性,重新回歸社會。使得刑法立法一方面堅持傳統刑法的基本品質,另一方面又眷顧社會發展,在體現刑法懲罰害惡、恢復公平正義的同時,發揮現代刑法維護社會安全秩序的控制目的。
(作者單位:嵊州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