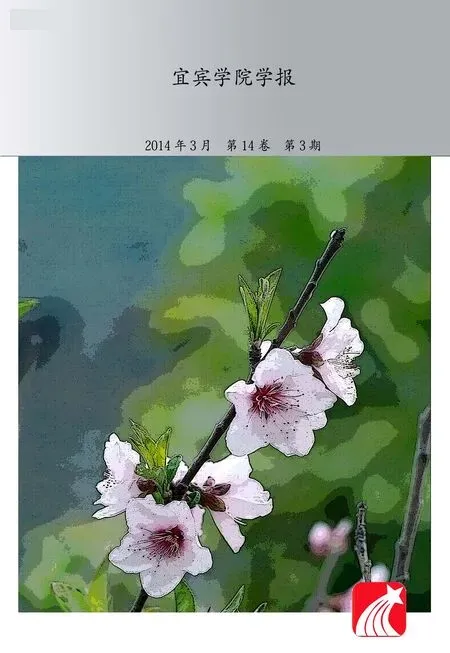早期關于人的本質論斷嬗變的深層邏輯
——基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文本之思
郭鎧毓,王玲杰
(廣西大學 政治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
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馬克思在思想上已經擺脫了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束縛,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他得以轉變的基礎是對德國現狀的批判。文章一直緊密聯系德國現狀,客觀的具體的歷史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和社會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唯物史觀的出發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同樣是基于對宗教、舊哲學和舊制度的批判而來的。所以,把握《導言》的思想,就要把握馬克思對于當時德國狀況的科學分析和辯證批判。
一 《導言》對宗教的批判
《導言》前七個自然段是對宗教的批判,立足于德國宗教現狀。德國1843年的宗教(反宗教)狀況就世界而言較先進,德國在反宗教方面領先于歐洲,并出現了很多反宗教的思想家。馬丁·路德是16世紀的宗教改革家,費爾巴哈在德國關于無神論的主張進一步指出,所謂的宗教不過是人們對塵世的恐懼的擬人化表達。“人對上帝的意識就是人對自己的意識,人對上帝的認識就是人對自己的認識;上帝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神學就是人本學。”[1]11神性就是人性,進一步揭示出了宗教的虛幻性。馬克思之所以要對先進的德國宗教理論進行批判,原因如下:第一,“對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1]13。馬克思批判的中心是“黑格爾法哲學體系”及其影響下的德國現狀,要首先澄清現實和宗教的區別,要正確指出宗教與現實的聯系,“謬誤在天國的申辯一經駁倒,它在人間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1],進而分析宗教帶給人民的災難,把斗爭的矛頭直指現實社會,“因此,反宗教的斗爭間接地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慰藉的那個世界的斗爭。”[2]1第二,把人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構建歷史唯物主義的主體。“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2]1是《導言》的邏輯起點:宗教和社會制度都應該從人的角度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人不依賴任何主觀的東西,只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產物。第三,從對宗教的批判中找出宗教、人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系,提醒人們脫離宗教的桎梏,回到現實的世界中來。“宗教批判使人擺脫了幻想,使人能夠作為擺脫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來思想,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性。”“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馬克思肯定了截止到“今天”哲學家(反宗教思想家)所作的貢獻,指出了以往宗教的虛偽性。但是又對他們的批判表示不滿,為批判宗教而批判宗教,走得不遠,也不可能走遠。真正應該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創立新的宗教,是徹底消滅宗教存在的根源——塵世的根源:法律、政治,也就是對政權的批判,馬克思指出了宗教與德國(塵世)現狀的直接關聯。在對宗教的批判中,提到了人的異化現象,這里的異化不是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而是對宗教的批判,宗教把屬于人的東西變成神的,從而壓迫現實的人,使人非人化,這也是宗教最為劣根的地方。
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還要引出人的本質問題,“人是人的本質”,即人的本質是現實的、具體的;是由社會關系決定的;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諸多社會關系的統一,以此摧毀宗教的謊言,擺脫了宗教對人的異化,是論證人是人本身的第一步。人的概念的澄清是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
二 《導言》對當時德國社會的批判
就歐洲范圍而言,德國是落后的。19世紀初,英、法已經相繼確立資本主義制度,完成了產業革命,社會迅猛發展,而德國的封建勢力仍然很強大。在馬克思撰寫《導言》之前的1843年1月31日,德國政府發出了“書報檢查令”,表現了大量逆歷史潮流的專制行為。“也就是說,當英法的無產階級在為自身解放而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時候,德國的問題還停留在上一個時代”。青年馬克思對德國的這種處境十分痛恨。馬克思已經明確意識到,解決德國的問題需要從德國現實的國情出發,相對于對宗教的批判,德國社會的批判更具有現實性。德國為什么會落后?這是馬克思在批判德國社會時的邏輯起點。從歷史角度看,“德國歷史上有過一個引以為豪的運動”[2]3,這一運動是指路德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德國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路德用理性來證明教義的合理性,理性成了最高的裁判者,這就為德國哲學的理性權威和思想自由提供了基礎,思想成了一種權利,而理性的權能變得合法化了。從這一點來講,德國應該是歐洲各國的楷模,應該是不批判的地方,但是“我們和現代各國一起經歷了復辟,而沒有和它們一起經歷革命。我們經歷了復辟,首先是因為其它國家勇敢地進行了革命,其次是因為其它國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種情形下,我們的統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種情形下,我們的統治者沒有感到害怕。我們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們牧師的領導下,處于自由社會。”[2]3一方面,宗教改革為除德國外的各國理性開辟了大門,但是德國仍然徘徊在黑暗的統治下;另一方面,德國只有復辟,沒有革命。看上去是因為德國統治者的強權專制,但是說明先進的德國思想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變成現實的革命實踐活動。對于德國社會客觀狀況,馬克思在《導言》的第14、15段又繼續闡述了卑鄙的德國政府和奴性的德國各階級,深刻地揭露了德國的丑陋。馬克思對德國狀況的描述是具體而客觀的,馬克思從德國落后的現狀出發,提出自己對德國的態度,同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觀對舊制度、不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制度應有的態度,“應該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馬克思已經把斗爭的對象從宗教加深為德國現實的制度,并對制度批判的原則方法進行了比喻和闡述,“在同這種制度進行斗爭當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對象就是它的敵人,它不是要駁倒這個敵人,而是要消滅這個敵人,因為這種制度的精神已經被駁倒。”[2]3-4馬克思在《導言》的第17段,闡述了德國革命對于世界的意義,“因為德國現狀是舊制度的公開的完成,而舊制度是現代國家的隱蔽的缺陷。”馬克思在分析德國現狀及德國應產生的革命時是具體、全面而客觀的:縱向上,批判從本國制度、思想、統治者和其他受壓迫階級出發;橫向上,批判又從各國和德國的比較及德國革命與各國之間的關系出發,是歷史唯物主義觀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具體體現,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社會現象從來都不以形而上學的觀點為基礎,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歷史發展和歷史事件都是以客觀、具體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由社會經濟基礎下的具體的人的活動出發的。
三 《導言》對黑格爾哲學及德國舊哲學的批判
對德國社會現狀的批判是對黑格爾舊哲學批判的基礎,哲學必然生存在現實的土壤中,這個土壤就是德國的現狀。馬克思提出,德國的現狀落后于歐洲同時代水平,所以已經沒有批判的必要,要做的是消滅。這種消滅就是要把德國來一個顛覆。顛覆的對象首當其沖便是德國的法律和政治,而法律與政治存在的“理性根據”就是德國的國家哲學——黑格爾哲學。這是馬克思的智慧之處,也是其對唯物史觀的運用之處,因為以往的革命都是“革”統治者的命,馬克思在文中沒有明確提出對某個統治者的反對,而是針對整個德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
從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到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可以看出,舊哲學對人的束縛同宗教對人的后果是一樣的,所以把人從舊哲學中解放出來也是《導言》的一個重要任務。但是按照唯物史觀,社會意識由社會存在決定,那么對哲學這種意識形態的批判還是不徹底的,徹底的是摧毀社會意識存在的物質基礎,馬克思不談改變經濟舉措而以哲學和法律為目標,在文中馬克思給出了答案。馬克思把德國舊哲學比作“本世紀所謂的問題所在的那些問題的中心。”[2]7因為“在先進國家是同現代國家制度的實際脫離,在甚至還沒有這種制度的德國,首先卻是同這種制度的哲學反映的批判脫離。”也就是說,對哲學的批判應該首當其沖,現實國家制度需要批判,人們觀念中的國家制度更需要批判。這是馬克思對歷史,尤其是對德國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科學分析。對哲學的批判是德國具體、迫切的需要,是德國的“特殊國情”,因為德國的特點是哲學先于生活,哲學指導生活。馬克思具體地批判了德國現存的“理論派”和“實踐派”,這二者包括了當時德國哲學的大部分,他們的根本錯誤在于割裂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當時對德國社會制度的批判存在兩種傾向,一種是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組成的實踐派,企圖直接行動來改造社會,忽視哲學批判的作用;另一種是由鮑威爾為代表的柏林自由人組成的理論派,輕視實踐,輕視現實的政治斗爭,把一切斗爭歸結為理論斗爭、思想革命。”[3]45馬克思在《導言》第23段批判了“實踐派”的觀點,“不在現實中實現哲學,就不能消滅哲學。”[2]7在《導言》第25段對“理論派”進行批判,“不消滅哲學本身,就可以使哲學變成現實”。“實踐派”和“理論派”的錯誤就在于一個試圖在實踐中直接解決哲學問題,一個試圖在哲學中解決哲學問題,二者都割裂了現實和哲學的關系(即實踐和理論的關系)。經驗論和唯理論是古典哲學爭論不休的話題,哲學界有人認為康德的批判終結了爭論幾個世紀的話題,但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恰是馬克思在《導言》中的論述,馬克思對這兩者的批判不僅停留在批判本身,而且為科學的哲學找到了符合歷史規律的出路。馬克思又從德國和西歐各國的現狀和國家意識的比較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德國人在政治上考慮過的正是其它國家做過的事情……那末德國的國家學說的現狀就表現了現代國家的未完成,表現的現代國家的機體本身的缺陷。”[2]9馬克思看似沒有批判黑格爾哲學,似乎承認黑格爾哲學現階段代表了“現代國家的未完成”,就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未完成,對于黑格爾那個時代來講,這種意識是超前的,馬克思也對這種意識超越物質的現象加以解釋,“脫離生活的思維只在德國才有可能產生,那末反過來說德國人之所以有可能從現實人抽象出現代國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為現代國家本身是從現實人抽象出來的”[2]9,這種理論并不違背社會歷史規律,恰好是符合的,是“人”產生的。馬克思針對黑格爾的法哲學中關于國家、市民關系作一小結,說明國家無論在制度還是現實中,都是現實中的人實現的。馬克思明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路徑是“會集中于只用一個辦法即通過實踐才能解決的那些課題上去。”[2]9-10這是馬克思在文中第一次單獨、正式地提出實踐這一問題,這個“實踐”概念與“實踐派”的概念截然不同。馬克思在《導言》第27段又提到了“實現一個原則高度的實踐”,這是與舊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同的實踐,甚至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想法。馬克思在《導言》第28段提出了唯物史觀最具分量的觀點“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10《導言》的全文也不過是為了得出“人是人”的概念,“批判的武器”是指理論,“武器的批判”是指“物質力量”,他指出了理論轉變物質力量的方法,就是讓人民群眾掌握理論,這里已經凸顯了“群眾”這一概念在《導言》中乃至唯物史觀中的分量,馬克思整篇文章對宗教和德國現狀的批判無非是要得出舊“物質力量”需要同為“物質力量”的“掌握理論的群眾”來摧毀。在這一段話的論證中,馬克思已經把理論的合法性加以具體的規范:“掌握群眾”、“徹底”和“抓住事物的根本”,即符合“客觀實際”與“客觀規律”。《導言》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實踐的標準,但是已經指出了“群眾”是整個歷史的關鍵。既然“群眾”是歷史的主宰,那么“群眾”就不能依賴任何物質以外的東西。“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這個論斷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本體論’的根本——把對人的追問徹底地訴諸人本身。”“把人從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來’,這就是馬克思為新哲學提出的使命。”[4]101至此,馬克思完成了對黑格爾及德國舊哲學的批判,把哲學的視野從宗教、制度和國家中移回人本身,把人本身作為哲學的起點,同時也為歷史唯物主義找到了科學的本體——人本身。
四 唯物史觀的理論意義
馬克思把具體的歷史的人看作整個國家乃至歷史發展的根本,已經完成了唯物史觀理論層面的闡述,但是這些批判還僅停留在“意識的層面”,“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19馬克思同舊哲學家的區別就在于他不僅“解釋了世界”,而且對新世界有具體的構想。
馬克思首先證明他對德國的期望是符合實際的。“那么,德國解放的實際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2]14馬克思所說的這種革命一定不是資本主義革命,雖然他沒有明確社會主義革命的概念,但是這是一個關乎人類解放的革命,是把人從一切束縛人發展的東西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是根本解決人的異化的革命。這種革命首先的疑問就是人的“解放何以可能?”馬克思在《導言》中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從德國的歷史和現狀闡述了這種革命的“可能性”。德國歷史上的宗教改革是理論的解放。所以,對于德國而言,這種解放也應該從思想中開始,即從“哲學家的頭腦開始”,因為德國官方的哲學(黑格爾哲學)是個絆腳石,《導言》已經毀滅了這塊絆腳石。這是德國歷史上的優秀傳統和革命的應然起點,同時,德國革命又面臨著重大的困難——“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2]10這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具體呈現,是社會生產力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上層建筑就沒有條件改變的另一種論證。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德國是落后于英、法的,按照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德國的經濟基礎是不能引出這個革命的需要,但是德國的矛盾在于人民迫切需要這種革命,而且德國在理論上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革命的階梯。這些結論盡管依舊沒有在德國實現,但是就德國先進的“舊哲學”而言,已經超越了歐洲的現實,這一結論同樣是從馬克思具體的調查和實踐中得出的。1843年10月,馬克思與在巴黎和法國的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德國的正義者同盟盟員建立了聯系,觀察了那里的工人運動,同時也是建立在馬克思對德國社會的現狀理解上的。在《導言》的37和38段中,馬克思有著對德國制度和市民社會具體的考察,他描述了黑暗的德國統治,概括了以往革命的本質,“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解放自己”,而德國需要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是“解放整個社會”。這種“所有人的解放”或者“整個社會的解放”需要這樣一個階級來扮演:第一,它是社會的普遍代表;第二,該階級的要求和權力是社會本身的要求和權力;第三,這個階級是“一個被徹底的鎖鏈束縛著的階級”。馬克思明確指出了這一階級就是無產階級,而且這個階級正在不斷壯大。馬克思通過一步步的論證,終于得出了無產階級解放社會這一結論。這一理論與唯物史觀的聯系在于:第一,馬克思分析了德國的具體狀況,從當時具體的歷史出發;第二,馬克思對社會各階級有著具體的分析,尤其是對無產階級進行了分析,
“德國革命的可能性在于形成了工業無產階級,闡述了無產階級由于其歷史地位而具有的世界歷史使命”[3]45-46;第三,德國革命的落腳點在人身上,“德國人就會解放為人”“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2]15,正是由于這一結論的得出,才使得整個唯物史觀完整。馬克思用這種方式得出了唯物史觀的方法論,也是第一次用這種方法從理論上解決德國革命的問題,從整體而言,唯物史觀就是要得出人是社會歷史的中心,人的解放必然是歷史發展的方向,沒有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科學預測,就不能構成完整的唯物史觀。
結語
馬克思從宗教的批判、德國社會的批判、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到革命的批判,從德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基本脈絡進行,從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物質條件出發,對國家、社會和意識領域進行綜合分析和批判,并把整個歷史的根本歸結到人本身,科學地把無產階級推上了歷史的高度,讓人重新成為歷史的主宰者。當時的馬克思還沒有給《導論》的體系命名為唯物史觀,但是從《導論》中不難發現,馬克思已經擺脫了舊哲學的束縛,重新樹立了人的形象,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社會歷史領域上從唯心到唯物的轉變。《導言》不僅是對于唯物史觀的具體闡述,還為后人提供了一種尊重歷史和現實的態度,一種永恒的批判精神。
參考文獻:
[1] [德]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M].榮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顧海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4] 孫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馬克思的本體論革命[J].學術月刊,2002(9):9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