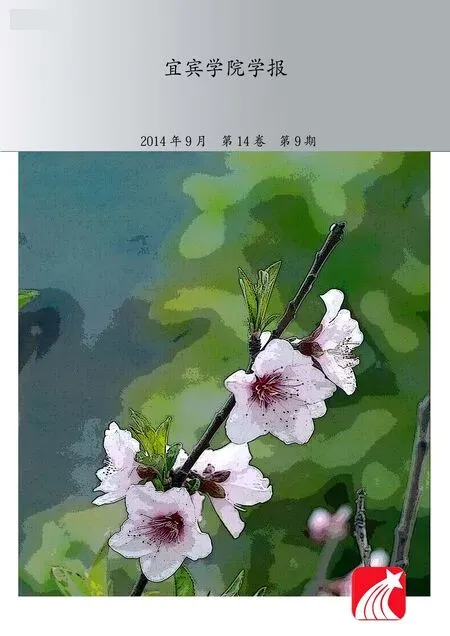圖式理論觀照下的異化翻譯傾向
——以《紅樓夢》“警幻仙姑賦”中涉及的文化現象翻譯為例
田筱倩
(山東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1813年,德國古典語言學家、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在OntheDifferentMethodsofTranslating中就不同的翻譯方法提出:“只有兩種翻譯方法:要么譯者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讓讀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譯者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讓作者去接近讀者。”[1]191995年,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其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書中,將第一種方法稱作“異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即偏離民族中心主義,壓制目的語文化價值觀,標示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讓讀者走出國門”;將第二種方法稱作“歸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 ,“即從民族中心主義出發,使原文屈從于目的語文化價值觀,將作者帶回本國”[1]20。自此,歸化與異化作為直譯與意譯的延伸,成為翻譯策略二元對立的爭鋒熱點。
在此,謹從皮亞杰圖式理論出發,對《紅樓夢》“警幻仙姑賦”中有關文化現象的兩種譯本——楊憲益、戴乃迭譯本與大衛·霍克斯譯本的翻譯策略進行剖析,以期對文學翻譯中的歸化與異化傾向作進一步闡釋。
一 研究歷史回顧
歸化與異化之爭,在翻譯各個時期雖稱謂不同,但實質可謂源遠流長,不論東方還是西方,翻譯二元對立爭鋒從未真正平息過。
在中國古代譯學史上,佛經翻譯中的“文質之爭”是歸化與異化的開端。梁啟超曾指出“好文好質,隱表南北氣分之殊。雖謂直譯意譯兩派,自漢代已對峙焉可耳。”[2]6-298支謙的《法句經序》記載了其與維祗難對佛經翻譯策略的不同看法,開啟了文質之爭的先河。在該序中,支謙強調“名物不同,傳實不易”[2]6-298,闡釋了其尚文的立場;而維祗難則主張“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2]6-298,其尚質思想流露其中。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主張質譯,鳩摩羅什則傾向于文譯,而慧遠則認為“文過其義,理盛其辭”,主張文質結合。[2]6-298該階段不論是文譯還是質譯,目的都是以期實現原文內容的忠實再現。
近代譯學史上,直譯與意譯作為“文質之爭”的延伸嶄露頭角。以魯迅為首的直譯派堅持譯文必須有異國情調譯,主張直譯,而以梁實秋為首的意譯派則強調譯文不應以辭害意、佶屈聱牙。魯迅指出,“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2]6-298,此處的“洋氣”指的正是異化。因近代譯學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歸化與異化更強調譯本的啟蒙作用,強調原文中的文化因素。
在當代翻譯研究中,歸化與異化之爭不再單純局限于直譯與意譯兩種翻譯策略之爭,跨學科、跨領域、多視角的研究取得進展。郭建中認為考慮到不同的翻譯目的、文本類型、作者意圖和讀者對象,文化因素翻譯中歸化與異化各有所需[3];韓子滿結合《苔絲》的譯本翻譯強調譯文翻譯中歸化與異化要掌握一個度,要恰到好處[4]。葛校琴區分了歸化與異化在后殖民視角下內涵、論域中的不同,強調社會情境的重要性。[5]蔡平指出歸化與異化是語言層面和文化因素的結合,從翻譯目的看,歸化占主導地位。[6]朱建平從歷時角度出發,強調語言尚未成熟時重視形式異化,語言走向成熟之時便會轉向文化因素,此時歸化為主。[7]劉艷麗、楊自儉從譯入語文化需求和國內懂外語讀者群擴大亟需了解異域風情兩個方面闡釋異化成為21世紀翻譯主流的原因。[8]孫會軍強調歸化與異化的動態性以及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9]劉芳從民族文化身份角度強調異化策略的重要性。[10]羅選民采用對比方法,從語言和文化角度探討文學翻譯中的異化。[11]孫藝鳳提出“文化流散”概念,試圖在歸化與異化的二元對立中另辟蹊徑。[12]余國良、文炳從語言哲學出發,意欲消除翻譯中的二元對立,提出翻譯“工具說”,主張適合特定語境,使用得當的翻譯方法就是好“工具”。[13]黃艷春強調需理清歸化異化與直譯意譯的關系以及英漢文化特色語句的差異空缺,提出歸化異化是原則性和譯者靈活性的辯證統一。[14]朱安博從哲學角度出發,試圖突破翻譯中的二元對立,使翻譯研究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發展和動態方向發展。[15]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當代關于歸化與異化的研究之爭主要集中在文學翻譯中文化因素的對待上。
在中國知網輸入“圖式 翻譯”關鍵字,在核心期刊發表的相關論文中,大多數是圍繞“意象圖式”“圖式與口譯研究”“圖式與轉喻”“圖式與翻譯認知過程”“圖式與聽力教學”“圖翻譯解析”和“文化圖式”展開研究的,而真正將圖式與文學翻譯中的文化現象所應采取的歸化與異化策略研究結合在一起的相對較少。
二 圖式理論
皮亞杰圖式理論由康德的認識論發展而來。皮亞杰認為:“圖式是指動作的結構或組織,這些動作在同樣或類似的環境中由于重復而引起遷移或概括。”[16]5-7圖式相當于我們所說的經驗知識或背景知識,但并非具體的知識,而是在具體知識或經驗中抽象概括出的借以容納新知識的動作結構,它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基礎。皮亞杰認為,刺激與反應并非某種單向S→R關系,而是S﹤=﹥R的雙向關系,“說的更確切一些,應寫作S(A)R,其中A是刺激向某個反應格局的同化,而同化才是引起反應的根源。”[17]61“刺激輸入的過濾或改變叫做同化;內部圖式的改變,以適應現實,叫做順應。”[16]5-7同化與順應相輔相成,同化是引發刺激輸入的前提,在同化過程中,因客體對主體而言并非新事物而被主體毫不費力地納入其中;順應是引起客體質變的前提,在順應過程中,因客體對主體而言是新事物,主體不得不主動改變以適應新客體形成新圖式。順應發生的前提是主體對某一新客體感興趣,而原圖式又沒有相關的經驗知識將其同化,否則主體圖式將認為是與己無關的事物而排斥在認識之外。新圖式是對舊圖式的繼承與發展。新圖式取代舊圖式,是“以新的、更穩定的平衡取代舊的、不穩定的平衡,既表現了認識發展的連續性,又表現了認識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的階段性。”[18]38-43皮亞杰圖式理論對翻譯中的歸化與異化傾向有明顯的指導作用。“對譯者而言,對原文進行同化的翻譯方式表現為歸化翻譯策略,對原文進行順應則表現為異化翻譯策略。”[18]38-43Cook認為,從讀者認知圖式的角度考察, 文學文本的主要功能是通過打破、更新、重組讀者原有認知圖式來建立新的認知圖式。[19]192譯者通過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借以實現譯入語讀者的原圖式在順應下得以打破、更新、重組,使譯入語讀者建立起新的更高層次的圖式,從而實現認識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但是前文已提到過順應產生的前提條件,如果譯者采取過度異化的翻譯策略,譯文與譯入語讀者的原圖式不存在聯系,原圖式只會將其排斥在認識之外。所以,異化翻譯策略不可能一蹴而就,異化的最終實現還需在歸化的基礎上慢慢過渡,隨著譯入語讀者認知圖式的不斷發展,異化翻譯策略將逐步加深。
三 《紅樓夢》“警幻仙姑賦”中的幾處文化現象
《紅樓夢》作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國古典小說中最具現實意義的一部巨著,無論是在思想內容、寫作風格,還是藝術形式上,都堪稱一部不朽的杰作。“警幻仙姑賦”出自《紅樓夢》第五回,描寫的是賈寶玉眼中警幻仙姑的萬千姿態。按中國古典小說的寫作手法,在一個重要人物出場時,作者總喜歡采用一段辭藻極其華麗的贊美之詞,通常是賦的形式,借以顯示該人物的重要性和作者多方面的才華。該賦不僅辭藻華麗,其中涉及到的文化現象更是值得作為個案來分析研究。下面謹以該賦中出現的幾處文化現象為例,以楊憲益和戴乃迭以及大衛·霍克斯的譯文為藍本[20]149-156①,分析皮亞杰圖式理論對文學翻譯的指導作用和其中涉及文化現象的翻譯策略。
(1)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
霍譯:A half-incipient look of pique
Says she would speak, yet would not speak;
While her feet, with the same irresolution,
Would halt, yet would not interrupt their motion.
楊譯:Her mothlike eyebrows are knit yet there lurks a smile, and no sound issues from her lips as if to speak as she glides swiftly on lotus feet and, pausing, seems poised for flight.
“蓮步”語出《南史·齊廢帝東昏侯記》“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21]40后人借此比喻美女的腳步。霍克斯將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蓮步”直接歸化成“feet”,這與譯文讀者的原有圖式完全一致,譯文完全被主體圖式所同化,譯文沒有陌生感和理解的難度,讀者圖式沒有產生順應,這很難對譯文讀者原圖式的重組與更新起到推動作用;相反,楊譯為傳遞原語文化,采用異化策略,直接譯為“lotus feet”,中國讀者圖式中有這樣的認識:中國古代的審美習俗是女子以小腳為美,纏過的小腳被譽為“三寸金蓮”,“步步生蓮華”正是對這種小腳的贊美。但相對于中國讀者的認知圖式,譯文讀者(西方讀者)的圖式中并沒有這樣的認識,所以很容易導致譯文讀者感到不解:蓮花做的腳?由于譯文讀者的圖式與原文差距太大,這很容易導致認識的排斥甚至是歪曲。
(2)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
霍譯:I wonder at her fine-cut features——
Marble, which fragrance marks as one with living creatures;
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
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楊譯:Sweet her face, compact of fragrance, carved in jade; 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龍鳳作為中華民族古老的圖騰,在歷史的發展長河中形成源遠流長、輝煌燦爛的龍鳳文化。龍鳳在中國文化中象征著吉祥如意。“龍”是神圣與權威的代表,“鳳”是高貴與美麗的化身。中國人的認識圖式中到處滲透著深厚的龍鳳文化意蘊,如“生龍生鳳”“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等。而在西方國家,phoenix是傳說中生活在阿拉伯半島的一口井邊,或五、六百年后點火自焚,在熊熊火焰中復生為幼的phoenix,因此,在西方國家,phoenix有“復活”和“再生”之意。Dragon 在西方神話中指口中吐火的巨大蜥蜴,在圣經故事里,它是邪惡的象征,與東方的神獸完全相反。[20]149-156楊譯尊重原文的語義結構以及文化意象,把“龍”“鳳”直譯為phoenix和dragon,這是嚴格的異化翻譯策略。由于中西方文化中對于“龍鳳”的圖式認識存在巨大差異,讀者原圖式中沒有相關的信息來同化譯文中的信息,楊譯很難將原文中的文化意象與深層內涵有效地傳達給西方讀者,借以更新西方讀者的認識圖式。霍譯尊重讀者的認識圖式,把“龍鳳”的文化意象轉成了西方所熟悉的雌雄巨鳥(simurgh 波斯神話中的一種能說會思的巨鳥),這雖然有助于幫助譯文讀者克服文化障礙,但譯文不具備一定的陌生感和理解的難度,讀者圖式無法產生順應,繼而無法得以更新。即便是看過《紅樓夢》的西方讀者,在過度歸化的譯文中也很難產生新的圖式,很難對中國的“龍鳳”文化意象產生深刻的認識。
(3)應慚西子,實愧王嬙。
霍譯:The beauties of days gone by by her beauty are all abashed.
楊譯:She would put Xi Shi to shame and make Wang Qiang blush.
西子、王嬙,指的是西施和王昭君,她們與貂蟬、楊玉環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美女,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詞。霍譯回避了“西子”“王嬙”這兩個特有的中國文化意象,只抽取二者的共同本質,譯為英文讀者能接受的“beauties”。此種翻譯雖克服了文化障礙,但是由于該歸化譯法提供的信息與譯文讀者的原圖式重疊,原圖式完全將其同化,譯文讀者失去了原圖式借以更新的機會,失去了一次了解中國文化的機會,即便看過《紅樓夢》,殊不知西子和王嬙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美女中的兩位。楊譯與霍譯采取了正好相反的翻譯策略,將“西子”“王嬙”直譯為“Xi Shi” 和“Wang Qiang”,其初衷是為了保留中國特有的文化意象,但是由于讀者的認識圖式中并沒有這方面的“背景知識”和“新信息”,譯文信息與讀者圖式缺少必要的聯系,主體無法將譯文信息同化整合到原圖式中加以重組、更新。譯文讀者若對“Xi Shi”和“Wang Qiang”這對新客體不感興趣,順應也就無從談起,讀者的原圖式也就無法實現打破、更新與重組。
對以上三處文化現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楊憲益和霍克斯在《紅樓夢》翻譯中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截然不同的。楊憲益采取嚴格的異化譯法,忠實于原文作者,是一種忠實地傳達中國文化的文化翻譯觀,藝術性強。霍克斯采取嚴格的歸化譯法,忠實于譯文讀者,可讀性強。但是,從圖式理論來看,過分的歸化譯法與過分的異化譯法在翻譯初期都很難實現譯文讀者原圖式的打破、更新與重組。基于Cook所提出的文學文本的功能,文學翻譯特別是在其中文化現象的翻譯中,異化翻譯策略應占主導地位,至于異化實現的程度,要取決于譯文讀者的原圖式,它決定了譯文讀者的認識水平和對異化信息的接受程度。如果異化程度過高,超越了譯文讀者的原圖式認識,譯文會因為過于晦澀而遭到不解甚至是排斥。
孫致禮早在2002年就撰文通過回顧中國一個世紀以來文學翻譯策略的發展歷程對21世紀文學翻譯策略的發展趨勢給予了展望:“我們有理由相信:21世紀的中國文學翻譯,將進一步趨向異化譯法,而這異化譯法的核心,就是盡量傳譯原文的‘異質因素’,具體說來,就是要盡量傳達原作的異域文化特色,異語語言形式,以及作者的異常寫作手法。但同時又指出,異化譯法還要注意限度,講究分寸,行不通的時候,還要借助歸化法。”[22]此處,圖式理論為其推斷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
以皮亞杰圖式理論為基礎,通過分析文學翻譯中歸化與異化的策略對讀者圖式所產生的不同影響可知,對于文學文本中的文化現象翻譯,半異化的翻譯策略在初期是必要的,即譯者可以采取加注(邊注、尾注或腳注法)的方法,對其中的典故或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予以解釋說明。這樣,具備一定“背景知識”或“已知信息”的譯文讀者,在同化譯文的基礎上,逐步順應其異化部分,從而為新的同化創造條件。這種半異化的翻譯策略在翻譯初期既照顧到譯文讀者的原圖式,又忠實地傳達了原文中的文化意象,不僅為譯文讀者提供了更新原圖式的機會,還為譯文讀者提供了感興趣的新鮮文化信息,進而實現文化的傳播與交流。隨著譯語讀者對原語特有文化現象的原圖式不斷實現打破、更新與重組,新的認識圖式會不斷建立,后來的譯者在遇到同樣的文化現象時就可以逐步省略注釋,采取完全異化的翻譯策略。
結語
皮亞杰圖式理論及其涉及的同化與順應為翻譯,至少是文學翻譯中文化現象所采取的歸化與異化策略的選擇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文學文本的功能是對讀者原圖式進行更新、重組與新建,這也就意味著文學翻譯應該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而順應正是實現這一功能的必經之路。但是,認識與理解是原圖式(已知信息)與新信息相互作用的結果,順應實現的前提是原圖式讀者有一定的“背景知識”或具備的一定的“已知信息”,這也就意味著在翻譯初期不可能采取完全異化的翻譯策略,翻譯只能是逐步趨向異化的過程。在翻譯初期,半異化的翻譯策略在翻譯特別是文化現象翻譯初期是必要的,隨著譯文讀者認識圖式的不斷更新,與譯語文化不同的信息會逐漸得到讀者的感知與認可,文學翻譯也會由歸化策略向半異化策略進而向異化策略過度。同化與順應是認識的兩個過程,由于認識的局限性和無窮盡性,異化只能是一個逐步加深、逐步深入的過程。
注釋:
①例文中,大衛·霍克斯的翻譯簡稱霍譯,楊憲益和戴乃迭的翻譯簡稱楊譯。
參考文獻:
[1] Lawrence V.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 陳福康. 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修訂本.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0:6-298.
[3] 郭建中. 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外國語, 1998 (2): 12-18.
[4] 韓子滿. 過猶不及:淺論譯文的歸化問題[J]. 外語教學, 2000, 21(2): 73-77.
[5] 葛校琴. 當前歸化/異化策略討論的后殖民視閉:對國內歸化/異化論者的一個提醒[J].中國翻譯, 2002, 23(5): 32-35.
[6] 蔡平. 翻譯方法應以歸化為主[J]. 中國翻譯, 2002,23 (5): 39-41.
[7] 朱建平. 歸化與異化:研究視點的轉移[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2, 25(2): 78-82.
[8] 劉艷麗,楊子儉. 也談“歸化”與“異化”[J]. 中國翻譯, 2003,23 (6): 20-24.
[9] 孫會軍. 歸化與異化:兩個動態的概念[J]. 外語研究, 2003(4): 60-64.
[10]劉芳語.文學作品英譯中的異化與歸化問題:兼評林語堂在《浮生六記》中的文化翻譯[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3, 26(4) : 71-74.
[11]羅選民. 論文化/語言層面的異化/歸化翻譯[J]. 外語學刊, 2004(1): 102-106.
[12]孫藝鳳. 離散譯者的文化使命[J]. 中國翻譯,2006, 27 (1): 8-10.
[13]余國良,文炳. 關于異化翻譯的再思考[J].外語學刊, 2009(3): 97-100.
[14]黃艷春. 異化歸化要義[J]. 外語學刊, 2010(4): 116-120.
[15]朱安博. 翻譯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的反思[J]. 外語教學, 2010, 31(2): 105-108.
[16]皮亞杰, 英海爾德.兒童心理學[M].吳福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
[17]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M].王憲細,等譯. 胡世襄,等校.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5.
[18]王克友.翻譯過程與譯文的演生:翻譯的認識、語言、交際與意義觀[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
[19]Cook G.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20]馮慶華. 文體翻譯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2.
[21]蔡義江. 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1.
[22]孫致禮. 中國的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J]. 中國翻譯, 2002(1): 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