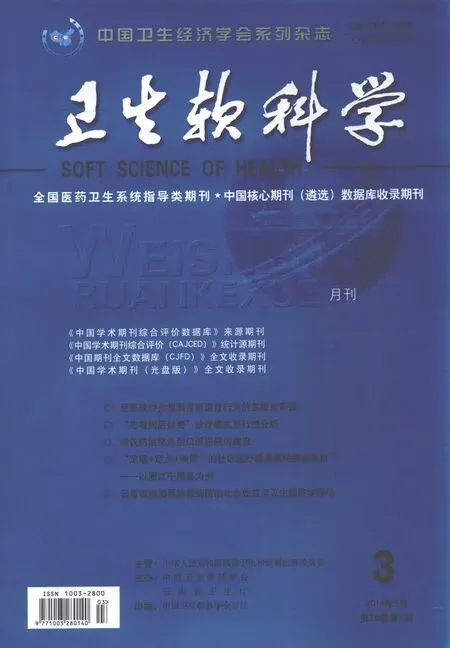后醫(yī)改時代我國過度醫(yī)療行為的多維度審視
馬 妍,樊 宏,吉華萍,陸 慧,尤 華
(南京醫(yī)科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江蘇 南京 211166)
我國目前的醫(yī)療體制環(huán)境下,不合理的醫(yī)療服務仍較為普遍,主要表現(xiàn)在不合理診斷、不合理治療、不合理用藥。據(jù)統(tǒng)計,大約1/3的醫(yī)療資源均耗費在了無實際意義的醫(yī)療服務上,過度醫(yī)療是其主要內(nèi)容。這種現(xiàn)象的長期存在勢必導致醫(yī)療費用的不合理上漲、醫(y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進一步突出,同時也成為當前衛(wèi)生服務諸多矛盾聚焦的集中點[1~2]。如今,新醫(yī)改的“重點期”已過,醫(yī)療衛(wèi)生行業(yè)正式進入“后醫(yī)改時代”。在后醫(yī)改時代,公立醫(yī)院改革是其重點所在,而如何治理過度醫(yī)療行為可作為其重要突破口,但目前對于過度醫(yī)療行為的理論研究基礎(chǔ)尚處于非常模糊甚至混亂的狀態(tài)[3]。因此,本研究將分別從倫理學、經(jīng)濟學以及法學的視角對過度醫(yī)療行為進行審視,以便為其治理對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jù)。
1 倫理學視角下的過度醫(yī)療行為
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過度醫(yī)療指醫(yī)務人員在非醫(yī)學目的的驅(qū)使下,出于各種不良動機,在醫(yī)療過程中不遵循臨床醫(yī)學規(guī)范,違背倫理學準則,從而提供給患方的不能真正為患者提高診療價值,只是徒增患者經(jīng)濟負擔,浪費社會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的不良診治行為[4]。
從上述表述可知,過度醫(yī)療行為從倫理學的視角來審視,主要違背了下列的原則和要求:
1.1 違背了醫(yī)學倫理學的最優(yōu)化原則
最優(yōu)化原則作為臨床診療護理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倫理原則,是指在選擇和實施診療護理方案時,盡可能用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效果,使診療護理達到最佳程度。而過度醫(yī)療行為的實施,體現(xiàn)了醫(yī)務人員的動機與效果不統(tǒng)一、目的與手段不一致、科學理性與人文理性不協(xié)調(diào),這完全違背了醫(yī)學倫理學所要求的最優(yōu)化原則,不利于我國衛(wèi)生服務事業(yè)的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我們應盡最大努力在確保診療護理需要和效果的前提下,降低診療費用,選擇資源消耗少、病人經(jīng)濟負擔輕的診療護理手段,做到“少花錢、看好病”。
1.2 違背了醫(yī)學倫理學的節(jié)約醫(yī)療資源的原則
目前,我國醫(yī)療資源還十分有限,如果醫(yī)務人員對某些病人實施過度醫(yī)療行為,勢必導致另外一部分病人無法完全得到公平優(yōu)質(zhì)的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衛(wèi)生服務公平性的降低,對于維持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wěn)定都是極為不利的。因此,杜絕過度醫(yī)療行為的發(fā)生,可以最大限度地節(jié)約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以有限的衛(wèi)生資源滿足更多人的衛(wèi)生服務需求對于我國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進一步改革與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5]。
1.3 違背了醫(yī)學倫理學的生命價值原則
生命價值原則要求尊重人的生命及其價值,對人的需要的滿足,是醫(yī)學行為選擇的主要倫理依據(jù)。現(xiàn)代醫(yī)學模式的貫徹,也要求醫(y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以病人為中心,全面考慮其生理、心理和社會的健康狀況,把病人置于首要位置,做到“一切為病人著想”,對其進行合理診療。而過度醫(yī)療行為的發(fā)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醫(yī)務人員單純把病人作為某種疾病的載體,通過其技術(shù)操作機會,追求超出合理范圍的經(jīng)濟收入,其代價是損害了病人的經(jīng)濟利益,甚至會危及病人的健康利益,這是對生命價值的嚴重踐踏。
1.4 違背了醫(yī)學倫理學的知情同意原則
知情同意原則,要求醫(yī)務人員必須向病人提供包括診斷結(jié)論、治療方案、病情預后以及治療費用等方面的真實、充分的信息,使病人或其家屬經(jīng)過深思熟慮自主作出選擇,并以相應的方式表達其接受或拒絕此種治療方案的意愿和承諾,在患方明確承諾后才可最終確定和實施擬定治療方案。而過度醫(yī)療行為往往無視患者的知情同意權(quán),某些醫(yī)務人員利用病人對醫(yī)學專業(yè)知識的無知,對病人自主權(quán)進行干預和限制,由醫(yī)生作出決定。這種行為并不是為病人利益或他人和社會利益考慮,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醫(yī)療權(quán)力使病人就范于過度醫(yī)療行為。這種行為具有一定的欺詐性,違背了醫(yī)學倫理學的知情同意原則,不僅不利于醫(yī)院與醫(yī)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fā)展,同時也必然進一步加劇醫(yī)患雙方的矛盾。
因此,從倫理學的視角審視,盡管過度醫(yī)療的產(chǎn)生有其各種客觀原因,但它確實也違背了醫(yī)學倫理學原則,其結(jié)果不僅嚴重損害了病人的身心健康,更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在患者權(quán)利意識日益增強的當代醫(yī)療體制環(huán)境下,很容易造成患者對醫(yī)務人員信任度的下降,從而惡化醫(yī)患關(guān)系,激化醫(yī)患矛盾,引發(fā)醫(yī)患之間的劇烈沖突[6]。
2 經(jīng)濟學視角下的過度醫(yī)療行為
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看,所謂過度醫(yī)療是指由于醫(yī)生給予患者的醫(yī)療手段超過患者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需要而給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與經(jīng)濟上浪費的醫(yī)療行為[7]。近年來,衛(wèi)生事業(yè)發(fā)展嚴重滯后于經(jīng)濟和其他社會事業(yè)發(fā)展,制約衛(wèi)生事業(yè)發(fā)展的體制性、機制性、結(jié)構(gòu)性的矛盾還沒有解決。很多醫(yī)療機構(gòu),尤其是公立醫(yī)院基本上靠醫(yī)療服務收費來維持運行和發(fā)展,導致醫(yī)療機構(gòu)片面追求經(jīng)濟利益,一些醫(yī)療機構(gòu)甚至采取了經(jīng)濟效益和醫(yī)務人員收入掛鉤的政策[8~9],這必然會引起過度醫(yī)療現(xiàn)象。
首先,就我國的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而言,由于對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投入長期不足,加之缺乏有效順暢的補償機制,對醫(yī)院和藥品生產(chǎn)的有效監(jiān)管缺位,醫(yī)院亦缺乏合理臨床流程和診療常規(guī),過度醫(yī)療也就在所難免了。其中,過度用藥尤為典型。據(jù)調(diào)查,在我國每年醫(yī)療費用上漲14%的幅度中,藥品費用支出占了60%以上,而藥品支出中抗生素的費用就占40%~50%。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濫用抗生素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每年約有8萬多人因濫用抗生素而死亡[7]。由于目前我國醫(yī)療機構(gòu)的補償機制改革進展緩慢,“以藥養(yǎng)醫(yī)”的局面在短時間內(nèi)難以改變,出于生存考慮,醫(yī)院的處方在短期內(nèi)還無法在社會自由流動,這使得群眾到藥品零售商店購藥受到處方的限制。同時,由于目前我國的執(zhí)業(yè)醫(yī)師及其處方權(quán)限的信息無法為社會共享,藥店很難確認處方者的身份,藥師也無法確認處方的合理性。任何人只要拿一張醫(yī)療機構(gòu)的處方箋,都能在零售藥店買到抗生素。藥品零售商此舉的目的主要還是利益驅(qū)動,為的是保住抗生素經(jīng)營的“大蛋糕”。但是,這種狀況的長期存在,勢必會出現(xiàn)抗生素濫用,威脅群眾用藥安全,也使過度用藥這樣的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監(jiān)管,必將對過度醫(yī)療行為的長期存在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次,從醫(yī)生與患者的立場來看。如今,醫(yī)患關(guān)系日益緊張,為防止因工作出現(xiàn)過失而引起醫(yī)患糾紛,醫(yī)務人員在醫(yī)療過程中通常會采取各種方式保護自己,因此,各種防御性醫(yī)療行為層出不窮,其中很多均屬于過度醫(yī)療行為。此外,有些醫(yī)院醫(yī)生待遇較低,付出和回報嚴重失調(diào),部分醫(yī)生常常通過多做檢查多開藥提高自身的經(jīng)濟收入,這也導致了過度醫(yī)療行為的產(chǎn)生。而從患者的角度來看,有些人為了尋求根治或早日治好疾病,對于別人指責的“過度醫(yī)療”行為他們并不認為應界定為過度醫(yī)療,他們有能力并情愿選擇這種診療行為。例如,因膽石癥或膽囊炎而行膽囊切除術(shù),可以采取傳統(tǒng)的腹部切口的方法,也可采用腹腔鏡小切口的方法切除。在特定的情況下,這兩種方法都可以認為是適度醫(yī)療,但對于經(jīng)濟收入較低的病人來說,腹腔鏡小切口的方法可能就會被認為是過度醫(yī)療行為,而對經(jīng)濟狀況較好的病人來說,卻多會選擇腹腔鏡小切口手術(shù),這對他們來說,并不會被認為是過度醫(yī)療[10]。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助長了過度醫(yī)療行為的發(fā)生。
3 法學視角下的過度醫(yī)療行為
從法學的視角來審視,過度醫(yī)療行為是指醫(yī)療機構(gòu)及其醫(y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違反醫(yī)療衛(wèi)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和診療護理規(guī)范、常規(guī),以獲取非法經(jīng)濟利益為目的,故意采用超越個體疾病診療需要的手段,給就醫(yī)人員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chǎn)損失的行為[3]。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權(quán)責任法》中第一次將“過度醫(yī)療”加入醫(yī)療損害責任款。《侵權(quán)責任法》第63條規(guī)定:醫(yī)療機構(gòu)及其醫(yī)務人員不得違反診療規(guī)范實施不必要的檢查。從而從法律層面上對過度醫(yī)療行為加以了限制,進而促使醫(yī)院和醫(yī)生應提供規(guī)范性的合理醫(yī)療,維護患者合法權(quán)益[11]。
《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四條第八款明確規(guī)定:“因醫(y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quán)訴訟,由醫(yī)療機構(gòu)就醫(yī)療行為與損害結(jié)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guān)系及不存在醫(y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為患者維權(quán)提供相應的法律依據(jù),同時也保護了醫(yī)方的合法權(quán)益,因為只要醫(yī)方具有足夠的證據(jù)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便不需承擔責任[12]。而舉證責任的倒置在一定程度上也給過度醫(yī)療行為的衍生提供了便利空間。
在許多交通事故的理賠過程中,經(jīng)常會發(fā)生肇事者及保險公司以“過度醫(yī)療”為由拒付高額醫(yī)療費用的情況,這種情況下患者只能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quán)利。而法院的審理多以司法鑒定結(jié)論為據(jù)。若鑒定結(jié)論認為訴求事實中“過度醫(yī)療”明顯,則判定被告醫(yī)院為過度醫(yī)療,需要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但是就醫(yī)院而言,可能會認為其診療過程完全符合醫(yī)療規(guī)范,因為臨床路徑規(guī)定可以“根據(jù)患者病情選擇某些項目”,不能因為檢查結(jié)果為陰性就判定檢查項目是過度醫(yī)療行為。因此,有關(guān)專家認為,只要實施的診療項目符合診療規(guī)范、指南的要求,就不應視為“過度醫(yī)療”[13]。這種情況下,“誰來界定”以及“以何為標準界定”過度醫(yī)療行為是其關(guān)鍵所在,也引發(fā)了新的司法問題。
過度醫(yī)療行為的“過度”必須要由專門機構(gòu)鑒定。在要求醫(yī)務人員不可以漏診、誤診患者,及時、恰當?shù)刈鞒鲈\斷,并及早實施相應的醫(yī)療措施的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沒有相對全面的檢查,許多疾病的診斷是難以確立的。因此,僅規(guī)范醫(yī)務人員及時、正確診斷的義務,而控制其進行相對全面的檢查權(quán)利,再以最終檢查結(jié)果來判定化驗、檢查的合理性、規(guī)范性,是不公平的做法。過度醫(yī)療行為的鑒定機構(gòu)由誰來組織實施,如何進行有效監(jiān)管,維護醫(yī)患雙方的合法權(quán)益,是目前面臨的一大難題。
綜上,從不同的視角下進行審視,過度醫(yī)療行為均會嚴重導致衛(wèi)生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會對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必要的損害[14]。然而在實踐中,界定過度醫(yī)療行為是一項非常復雜的世界難題,只能遵循這樣的基本準則,即對病人的治療總體上是趨好還是傷害,另外病人在經(jīng)濟上、心理上是否能承受得起,病人的權(quán)利是否得以體現(xiàn)[15]。盡快出臺有效措施,規(guī)范醫(yī)務人員的醫(yī)療行為[16],遏制過度醫(yī)療,降低群眾不合理的醫(yī)療費用,促進衛(wèi)生事業(yè)回歸公益性,從根本上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這也是后醫(yī)改時代,深化落實醫(yī)療改革措施的極好契機。
[1]周 淼,劉新蓀,陳日來.過度醫(yī)療的成因及其引發(fā)的思考[J].中國衛(wèi)生事業(yè)管理,2007,(10):663-664.
[2]張忠魯.過度醫(yī)療—一個緊迫的需要綜合治理的醫(yī)學問題[J].醫(yī)學與哲學,2003,24(9):1.
[3]周士逵,曾 勇.過度醫(yī)療行為的法律研究[J].川北醫(yī)學院學報,2007,22(2):186.
[4]王德國,繆典慶,王 敏,等.對過度醫(yī)療的醫(yī)學倫理學思考[J].衛(wèi)生經(jīng)濟研究,2004,(12):25-26.
[5]郭永松.關(guān)于過度醫(yī)療服務的倫理學審視[J].中國醫(yī)學倫理學,1998,12(4):47-50.
[6]NAYLOR C D.What is appropriate care[J].N Engl J Med,1998,338:1918-1920.
[7]李曉英.過度醫(yī)療的衛(wèi)生經(jīng)濟學思考[J].解放軍醫(yī)院管理雜志,2006,13(7):601-602.
[8]田文華.軍隊衛(wèi)生經(jīng)濟理論與方法[M].上海:第二軍醫(yī)大學出版社,1998.
[9]廖繼堯.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與構(gòu)建和諧社會若干問題的思考[J].中華醫(yī)院管理雜志,2005,(21):651-653
[10]杜治政.過度醫(yī)療、適度醫(yī)療與診療最優(yōu)化[J].醫(yī)學與哲學,2005,26(7):1-4.
[11]王 芳,于潤吉.淺談過度醫(yī)療加入《侵權(quán)責任法》[J].醫(yī)院院長論壇,2010,(2):57-58.
[12]陳 化.舉證責任倒置引發(fā)過度醫(yī)療的倫理思考[J].中國醫(yī)學倫理學,2006,19(2):24-26.
[13]大河網(wǎng).案例分析:法律層面如何界定過度醫(yī)療[EN/OL].[2011-02-15].http://health.dahe.cn/zt/2011/gd/201102/t20110215_61572.html.
[14]郭文麗.論過度醫(yī)療與適度醫(yī)療[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5,15(5):2955-2956.
[15]于莎麗.關(guān)于過度醫(yī)療倫理分析的再思考[J].中國醫(yī)學倫理學,2007,20(2):43-44.
[16]譚明桐.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醫(yī)院更應加強醫(yī)德醫(yī)風建設(shè)[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1,1(3):354-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