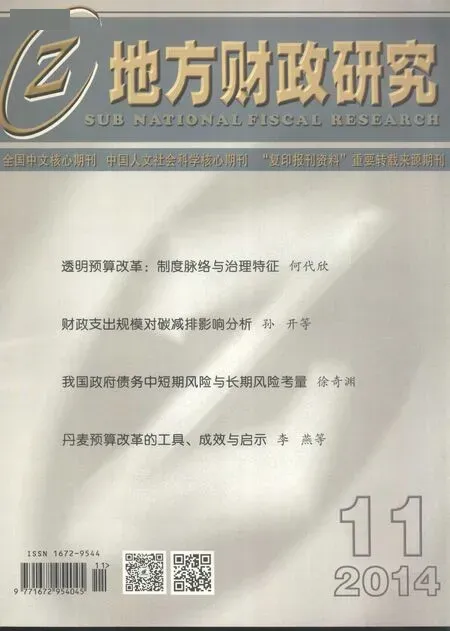論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新原則
王玉玲 潘 登 江榮華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1994年以來,我國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①“財政管理體制”是我國財政學界的傳統概念,與之對應的,是西方財政學的“政府間財政關系”。本研究認為,“財政管理體制”概念側重從中央層面進行“管理”,是由上而下的體制構建;而“政府間財政關系”則是對不同級政府之間財政關系的界定。因此,本研究使用“政府間財政關系”進行基本概念界定。同時,對于我國的實際狀況,仍使用“財政管理體制”概念。,其核心內容就是規范中央與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級政府)間財政關系。分稅制確立之初,提出“財權與事權統一”原則,后這一原則修改為“財力與事權相匹配”。本研究認為,對于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原則而言,“財權與事權統一”或者“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提法都比較籠統。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基本邏輯應為:在明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職責和支出責任的基礎上,匹配相應的財力,財權作為財力的基礎。此外,應逐漸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自治權,與財力共同形成“財政共治力”,以滿足其公共服務職責的需要,完成支出責任。因此,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新原則為“明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和支出責任,支出責任與財政共治力匹配”。
一、特殊的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要求特殊的原則
在我國,民族自治地方是特殊的地方,其與中央的關系也具有特殊性。特殊的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關系要體現為特殊的財政關系,而特殊的財政關系要求特殊的原則。
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關系的特殊性源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民族團結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研究認為,制度的活力,源于不斷充實和發展;而制度層面的充實和發展,依托于體制層面的完善。因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充實和發展需依托包括分稅制在內的諸多體制的不斷完善。從財政的角度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體現、落實于分稅制,才不會流于泛泛。
分稅制的確立,有效提升了“兩個比重”,對于穩定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帶動中國稅收高速增長①有研究認為,分稅制改革使得稅收分權向以分稅合同為主的契約轉變。與財政包干辦法相比,中央與地方稅權邊界比較清楚,稅收風險和收益基本由雙方自己承擔,稅收激勵比較明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動力提高稅收努力,并通過稅收信息化建設來提高征稅能力。由此,實現了稅收高速增長。參見呂冰洋、郭慶旺:“中國稅收高速增長的源泉:稅收能力和稅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釋”,《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促進地方財政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分稅制運行近二十年,始終是“分錢”重于“分權”,這一模式下,地方財政的主體性難以體現,其財政基本面也隨國家宏觀政策大幅波動,更催生出難解的“土地財政”困境,對其反思和改革也勢在必行。具體到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分稅制沒有承襲試點時給予民族自治地方(新疆)特殊地位的做法,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特殊性難以充分體現。雖然中央在后來的諸如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民族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等政策中給予民族自治地方一些特殊照顧,但相關規定呈零散狀,作用有限,且并未上升到理論層面進行探討,進而指導財政實踐。
分稅制將民族自治地方視為普通的地方的做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于克服中央與地方“一對一”談判的弊端是必要的,有助于分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但因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存在,民族自治地方畢竟不是普通的地方,其與中央政府的財政關系不同于非民族自治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財政關系。從理論上明確這一關系的特殊性,并探討其改革的方向,就成為現實的需要。
更深層次看,重視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特殊性源于對財政本質的認識。財政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與經濟的密切結合,是“政之財”、“財之政”。“以財行政,以政理財”是對財政概念的最好概括。“政”的基本,就是國家。②這一點上,在財政本質問題的討論中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國家分配論”是正確的,也是做出突出貢獻的。參見張馨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章“財政本質論”。財政是以國家為邊界和主體的,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認為財政是國家對經濟的掌控。財政作為政治與經濟的結合,起主導作用的是政治。因此,財政本質是國家以政治形式控制經濟的方式,是國家從經濟對社會的調控,它由收入和支出兩個基本方面組成,收入的依據是政治權力,支出的原則是維持國家政權及其政治統治。基于對財政本質的認識,本研究認為,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不單是“財”,且是“政”。應重視民族區域自治這一政治制度,以彰顯財政的本質,構建新型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實現國家對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的掌控和從經濟對其社會的調控。
本研究以“財政共治”概念界定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特殊的財政關系。本概念的提出,受到朱倫先生“民族共治”概念的啟發。在其2001年-2003年的三篇文章③這三篇文章分別是“民族共治論——對當代多民族國家族際政治事實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論民族共治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原理”(《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和“自治與共治:民族政治理論新思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中,朱倫先生提出并論證了“民族共治”概念。朱倫認為,所謂民族共治,就是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由各民族共同造就的以共和為目標、以權益平衡發展為取向、以民族關系良性互動為核心的政治結構、運作機制和實現工具。“民族共治”命題,來源于對當代多民族國家民族政治理性實踐的客觀總結,產生于對民族政治理性原則的深入認識,因此,它是一個值得進行理論提升的命題,應當成為當代多民族國家民族政治理論建設的核心思想。對此,還有研究者也提出,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內,區域自治的前提是在中央的統一管治之下針對地區的差異因地制宜特殊處理。共治是本,自治是末。④參見戴小明等:《公共財政與憲政——民族地區公共財政法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4頁。本研究認同上述觀點,并認為民族問題研究要突破單純從“自治”角度展開的局限。共治是一個比自治更寬、更高的概念,它不僅可以對自治做出方向性的規定,而且還因它本身就包含了自治,可以使自治的意義得到升華。⑤朱倫:“自治與共治:民族政治理論新思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上文已明確,財政的本質是國家以政治形式控制經濟的方式,是國家從經濟對社會的調控。這一本質落實于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就是“財政共治”。財政共治是指基于我國民族區域自治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建立在分稅制基礎上的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政府間財政關系。財政共治包含兩級政府——中央政府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①鑒于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特殊性,這里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主要指自治區政府。這與分稅制主要涉及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的體制構建是一致的。,其中,中央政府發揮主導作用。財政共治的構建基礎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自治,財政共治并不否定財政自治,而是財政自治基礎上的創新。財政共治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其基礎在于民族自治地方稅權的完善,方式是中央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首要與核心是對原則的規定,特殊的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財政共治”要求特殊的原則。我國目前分稅制的原則,即“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原則,將民族自治區與其他省同等對待,不能體現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特殊性,國家從經濟角度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調控無法真正落實,只能給予一些優惠政策,未從總體上考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財政出現的很多問題,諸如財政自給率低、高度依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難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都和未以特殊的原則體現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特殊性相關。
概括而言,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具有特殊性,可界定為“財政共治”,財政共治需要特殊的原則,本研究界定為“明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和支出責任,支出責任與財政共治力匹配”。
二、“事權”概念不準確
在上述“財權與事權統一”或者“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原則中,“事權”是一個重要概念,但本研究認為,“事權”概念并不準確。因此,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原則不使用“事權”這一概念。
“事權”是一個中國獨有的財政學概念,也是一個“熟知但非真知”的概念。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間財政關系中的“事權”是指各級政府對所轄國營企業與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權。許毅和陳寶森在1984年出版的《財政學》中,對于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基本經驗和應堅持的原則時指出:“財權和事權是聯系在一起的,我國的社會制度決定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國營企業與事業單位。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歸哪一級管理,即事權放在哪一級,財權也相應放在哪一級。……地方財權的大小和中央劃給地方的事權應當一致起來……地方財權的大小,表現在事權的劃分上,反映在各項支出的支配權上。”②許毅、陳寶森:《財政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年版,第587頁。可見,這里的“事權”是指各級政府對所轄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權,反映的是各級政府管理職能的劃分,突出的是按行政隸屬關系劃分財政收支的傳統體制設計思路。③張晉武:“中國政府間收支權責配置原則的再認識”,《財貿經濟》2010年第6期。與其同年代的財政學教科書中,也對事權進行了基本相同的表述。
改革開放后,伴隨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分稅制的實行,原有對事權的理解,因為缺失體制基礎而滯后了。但“事權”概念卻保留了下來,并加進了一些新的界定,表現為以責任和權力的統一來解讀事權。例如,有學者提出,所謂事權,為某一級政府所擁有的從事一定社會經濟事務的責任和權力,它是責任和權力的統一,單單把它理解為政府的責任或權力都是片面的。事權不等同于事責,事責只是從責任的方面來體現事權。④王國清、呂偉:“事權、財權、財力的界定及相互關系”,《財經科學》2000年第4期。還有學者認為,所謂事權,是指政府承擔辦事權力與職責,也就是確定政府財政支出范圍及管理權力的運用范圍。事權的大小取決于可支配資金數的多少。⑤譚建立:“論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關系”,《財政研究》2008年第1期。
顯然,上述認識還是以認可“事權”概念為前提,并加進“責任”來解讀事權。權力與責任確實存在貫通之處。責任是權力賦予的直接依據,權力是履行責任的必要手段。但權力與責任雖有聯系,卻不相同。責任是分內應做的事情,權力則是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權力要求的是利益,而責任突出的是義務,是社會、他人或某些情況對責任主體行什么事及如何行事的要求。⑥張晉武:“中國政府間收支權責配置原則的再認識”,《財貿經濟》2010年第6期。更重要的是,在分稅制下,“事”作為“權”很難理解。做事是為了攬權嗎?
本研究認為,“事權”概念界定上的眾說紛紜,源于概念本身的不準確。“事”無非兩類,管事和辦事。管事意味著對某事決策、指揮、控制;辦事則強調對某事的辦理。但“管事”也好,“辦事”也罷,都不是“權”,而是“責”。沿用“事權”概念會造成邏輯的混亂,并導致現實中的困惑。因此,應將“事權”明確為“事責”,管事與辦事不是“權”,而是“責”。并且,因為是“責”,就必須嚴格盡責。
對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在分稅制下,中央為了維護邊疆穩定,打擊分裂勢力,實現民族團結,改善各民族公民民生狀況,給予了民族自治地方轉移支付等方式的大量財政資金。但由于“事權”概念的不準確,這些財政支出支撐的似乎是地方政府的“權”,卻不能明確其“責”,是否盡責更難以考量。在這種背景下,只能通過強化對干部的政績考核來對其進行約束,“政績工程”層出不窮與此高度相關。體制本身的問題應首先從體制入手解決,反思“事權”概念,建立清晰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邊界,就成為必然。就財政共治而言,必須厘清中央政府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錢”、“責”界限,中央政府出“錢”要對應著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盡“責”。“事權”概念可以休矣!
三、明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和支出責任
以對管事與辦事的區分為基礎,政府責任應分為公共服務職責和支出責任①“支出責任”概念正在逐漸成為官方表述。例如,2013年7月17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第五輪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上發表講話,提出正在醞釀財政改革,將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適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保障市場更加統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全國均等化。參見《樓繼偉:中美加強合作共同對挑戰》,http://wjb.mof.gov.cn/pindaoliebiao/ldjh/201307/t20130716_966675.html。。所謂公共服務職責,是指各級政府承擔的應由本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供給的職能和責任,它決定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出資范圍;從政府收支角度看,就是各級政府承擔的出資責任。而所謂支出責任,是指各級政府承擔的組織落實財政支出的責任。公共服務職責(出資責任)與支出責任的主體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以明晰的公共服務職責和支出責任的區分,來取代不準確的“事權”概念,對于正確理解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原則,無疑是有益的。應根據支出受益范圍、職權下放、中央財政主導性等原則,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一是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國防經費、武警部隊經費、國家外交事務和援外經費支出,全國性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經費支出,全國性固定資產投資支出,各種補貼支出、支農支出,撫恤和社會救濟費、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支出,轉移支付支出,國內外債務還本付息支出等。二是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地方文化、教育、衛生、科學事業經費和其他事業經費支出,地方固定資產投資支出,各種區域性補貼支出和支農支出,撫恤和社會救濟費、社會福利保障支出,對下級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支出,地方(指省級)債務還本付息支出等。三是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承擔的支出。具有調節地區間、城鄉間重大收入分配性質的支出責任,應由中央財政承擔或由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共同承擔;對于在省級范圍內,但有“外溢效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跨地區的交通、郵電、空港、環保等項目,應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
在上述劃分的基礎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主要為三類:(1)自身公共服務職責的支出責任,如城市維護和建設、地方公共管理等。這類公共服務職責惠及轄區內居民,外溢性不強,可稱為“內部公共服務職責”。此類公共服務職責(出資責任)和支出責任的主體一致,都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2)代理性公共服務職責的支出責任。這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代理了本應由中央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責所帶來的支出責任。這類公共服務職責關系國家整體利益,有很強的全國范圍受益性質,需要中央政府承擔全部出資責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只承擔支出責任。代理性公共服務職責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顯性的,由中央政府以文件等提出明確要求,體現在諸如國家安全與穩定、公共突發事件處理、社會發展等領域;另一類為隱性的,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實際承擔了應由中央政府承擔的職責,包括自然災害應急處理、生態治理等。(3)外溢性公共服務職責的支出責任,如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這類公共服務職責的外溢性強,惠及轄區周邊乃至全國居民,需要中央政府按照外溢程度承擔相應份額的出資責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承擔支出責任。①關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代理性和外溢性公共服務職責,有研究以新疆為對象,做了細化分析。參見李學軍、劉尚希,《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研究———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0頁。
上述三類支出責任中,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都是支出責任主體。但后兩類并非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因此不能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承擔全部出資責任。中央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以財政轉移支付的形式全部或部分承擔出資責任,以幫助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更好地完成支出責任。另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作為支出責任主體,并非出資主體,在履行支出責任時,要嚴格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進行。
四、支出責任與財政共治力匹配
在明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基礎上,要求“支出責任與財政共治力匹配”。之所以提出“財政共治力”概念,是因為對于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其財政的內容既包括分稅制所確定的財權、財力,也包括《民族區域自治法》所明確的財政自治權。民族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是指在國家統一的財政體制下,自治機關根據憲法原則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的精神,依照自治條例的規定和當地民族政治、經濟及文化的特點,制定財政自治條例或有關法律的變通及補充規定等,組織財政收入,統籌分配財政資金,自主地管理本地區財政事務的權力。其內容包括:①財政自治立法。②自主組織和使用財政收入。③依法安排財政支出。④對屬于地方財政收入的某些稅收實行減稅或免稅。②參見戴小明:“財政自治及其在中國的實踐——兼論民族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因此,相較于其他地區而言,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需體現為特殊的概念,本研究將之明確為“財政共治力”。
簡單說來,單就分稅制框架分析,對于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其

其他省、直轄市的財權、財力同此。但對于民族自治地方而言,還需要加上“財政自治權”,這樣,其財力+財政自治權=財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其中,等號左邊我們稱之為“財政共治力”,因此,

上述以簡單等式表示各概念的關系,嚴格說來是不準確的,但可以相對清晰地闡明“財政共治力”的內容。我們以公式(3)來進行分析。在這個公式中,財政共治力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財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財政自治權,其中,財權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內容來自分稅制的規定;財政自治權則來自《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
上述兩方面缺一不可。只有財權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明確的財政自治權無以體現,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省、直轄市的財政管理體制的差別無法彰顯;而如果只有財政自治權,在分稅制下也是不現實的。
從滿足出資責任的角度看,財政共治力中的“財權”與“財政自治權”主要是滿足前述“內部公共服務職責”要求的出資責任;而“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則是滿足代理性和外溢性公共服務職責要求的出資責任。代理性和外溢性公共服務職責的存在,使得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出資責任與支出責任存在巨大差異,這一差異是其財政無力獨自承擔的。對此,中央政府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全部或部分承擔出資責任,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履行支出責任提供財力保障。這兩大類出資責任,最終都要落實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構成其支出責任。因此,要求“支出責任與財政共治力匹配”。
〔1〕張馨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朱倫.民族共治論——對當代多民族國家族際政治事實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3〕張晉武.中國政府間收支權責配置原則的再認識.財貿經濟,2010年第6期.
〔4〕王玉玲.民族自治地方稅權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5〕李學軍,劉尚希.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研究——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版.
〔6〕課題組.明晰支出責任:完善財政體制的一個切入點.經濟研究參考,2012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