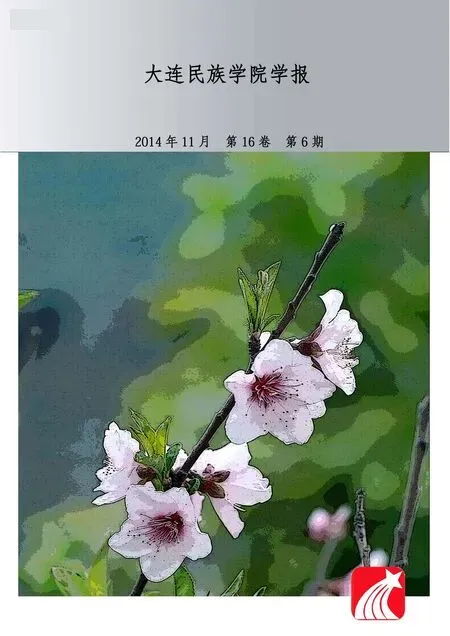黔東地區(qū)古戰(zhàn)場遺址之“囤”文化探賾
汪 興,王 芳
(1.玉屏縣文聯(lián),貴州 玉屏554000;2.大連民族學院 紀律檢查委員會,遼寧 大連116605)
“囤”是黔東地區(qū)一種獨特的古戰(zhàn)場文化,曾在清朝后期至民國初期這段時間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今,“囤”的作用在黔東地區(qū)少數民族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雖然消失了,但其無處不在的遺址仍然記錄著140 多年前那漫天血與火的歲月。本文結合黔東地區(qū)“囤”的形成及演變等實際情況深入探究了這一文化遺址的根源。
一、“囤”形成的時代背景
1.對“囤”“坉”“屯”字的釋義
其一,對“囤”“坉”“屯”的解釋。《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對“囤”釋義為:儲存、囤集、囤聚之意;“坉”在《辭源》中有三種解釋:(1)用草包盛土筑墻或堵水;(2)水不通;(3)田垅。《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僅釋義為“寨子”,并把“”歸為同一字義中。“屯”在《辭源》中有五種解釋:(1)艱難;(2)吝惜;(3)聚集;(4)駐守;(5)土阜。“囤”字在眾多史料記載中,用得相對較多的要數明萬歷年間湖廣總督李化龍所著的《平播全書》。
從上述“囤”“坉”“屯”的釋義來看,無論是“囤”還是“坉”,都是用來抵抗外來侵犯的防御工事。本文主要考證“囤”的歷史。有的史料存在“囤”“坉”“屯”混用的現(xiàn)象。尤其是“屯”字用得較多,容易與安居之地的“屯”相混淆。如:清《松桃廳志》卷之四“山川”記載:“云羅屯:城西南二里。形如天馬,頭尾高而中凸,四面石壁高百余丈,頂寬平,可容萬馬,僅有兩條小路可上,前人設卡于此,石墻在焉。雍正八年,逆苗滋擾,難民避處其上。乾隆六十年,逆苗再擾,鄉(xiāng)民仍就之避難,據屯札守。”這里的“屯”實應為“囤”。
其二,“囤”的地形和結構。據對黔東、湘西等地區(qū)的調查考證,“囤”一般都選址在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山頂上,在山頂的四周用大小不等的巖石(也有用土石合成)筑成圍墻,用來防御。在“囤”內部建有集吃、住、儲存等各類不同功能于一體的配套設施。“囤”的面積大小不等,有的山頂地勢較為寬闊。據調查,萬山區(qū)高樓坪鄉(xiāng)小灣村的鳳凰囤面積約為6 000 余平方米,曾居住過350 余人;有的囤面積相對較小,約為80 ~1 000 余平方米,居住人數僅為20 ~100 余人。
2.“囤”形成的時代背景
據有關典籍和史料記載,黔東地區(qū)“囤”的形成大致包括以下兩個時期。
初始期:1368 年,明王朝建立后,為了加強對西南各個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控制,洪武年間(1371 -1391),先后在貴州境內建立了貴州衛(wèi)、平溪衛(wèi)、清浪衛(wèi)、鎮(zhèn)遠衛(wèi)、威清衛(wèi)、偏橋衛(wèi)等24 個軍事組織。而各個衛(wèi)除下設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小旗外,還設立了堡、塘、訊、屯等軍事機構。尤其是屯的設置遍及黔東地區(qū)廣大鄉(xiāng)村。據《玉屏侗族自治縣志》第一篇第二章“行政區(qū)域”記載:“明代,平屯下轄48屯,有考47 屯。即平屯、青囤、大屯……”“屯”有軍屯、民屯、商屯之分,在明朝初、中期以軍屯為主。
明永樂十一年(1413),朝廷在平定“兩思”之亂之后,廢思州、思南兩府,重新設立了思南、思州、烏羅、石阡、銅仁、新化、黎平、鎮(zhèn)遠等八府,其轄地為現(xiàn)在的思南、思州(岑鞏)、石阡、銅仁、黎平、鎮(zhèn)遠、玉屏、天柱、三穗等廣大的黔東地區(qū),并強制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極大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從而激起了他們的反抗。據有關典籍記載,自明正統(tǒng)元年至崇禎六年,相繼發(fā)生、發(fā)展在黔東地區(qū)有苗族首領蒙能、松桃苗人石全州、銅仁苗人龍許保等、銅仁九股苗、思州田文澤等10 余次大小不同的少數民族起義。為了防備義軍的進攻,加強自我保護,平溪衛(wèi)、清浪衛(wèi)、鎮(zhèn)遠衛(wèi)等轄區(qū)除了加強對衛(wèi)城的防護外,還要求各千、百戶所等堡、屯等地選擇在部分易守難攻的坳、坡等要道設置或修建相應的防御工事。“囤”便由此初成。
形成期:進入清朝,為了維護統(tǒng)治者的利益,清廷對漢族及部分少數民族強制實行“剃發(fā)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等民族岐視、高利盤剝、政治壓迫政策。不僅傷害了民族感情,惡化了民族關系,而且致使其與其他各民族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到了清咸豐年間,長期集聚下來的民族矛盾大爆發(fā),全國各地由此曾先后舉行了多次民族起義。在咸豐四年(1854)至同治十一年(1872)間,在貴州的黔東南、黔東等地區(qū)曾先后發(fā)生了姜應芳、張秀眉、徐廷杰等多起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大起義,波及范圍大都在黔東、黔東南、黔北、黔中、黔南等地區(qū)。為了防范和抵御義軍的進攻,這些地區(qū)各個村寨在當地團練或宗族族長的組織下,主要選擇其地勢險要的山頂,大規(guī)模地組織修筑起“囤”作為防御工事。據《貴州通史》第三卷第三篇第二章“咸同各族人民大起義”記載:“從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起,冷水、皮廈、漢寨的‘中和團’改變了追剿義軍的方針而實行堅壁清野、‘結屯防守’的辦法。其余地主團練也相繼仿效,隔絕了起義軍與群眾的聯(lián)系,使義軍無法得到糧食和其他物資。同治六年(1867)二月,署貴州提督趙德光建議在全省范圍推廣天柱的‘結屯防御’辦法。”一時間,“囤”的建設在全省各地尤其是在黔東地區(qū)普遍興起。據對玉屏侗族自治縣各個鄉(xiāng)鎮(zhèn)的田野調查統(tǒng)計,在全縣517平方公里范圍內,共修建了大小不等的“囤”多達155 個,涵蓋全縣所有的村村寨寨。
二、“囤”的建設及管理
1.選址及建設
由于“囤”功能主要是防御,因此“囤”的選址非常有講究,一般大都選擇在離家村寨較近、地勢較高,且易守難攻的山頂修建。地處云貴高原的黔東大地,高山狹谷,溝壑縱橫、地勢險要之處比比皆是。于是,各個村寨便大都選擇在離家較近且地形險要的山頂上修筑大小不等的“囤”。也有少數村寨則選擇在地勢較高的山洞作為防御之所。玉屏侗族自治縣黃母沖村氽水洞組的瓜瓢洞囤就是因地制宜而設的,雖然洞內面積僅100 余平方米,但其防御設施卻一應俱全。
而“囤”的修建一般有三種形式:其一是由當地團練或宗族族長的組織下,通過鄉(xiāng)紳捐資和群眾投工投勞修建起來的。這種“囤”由于有經費保障,因此修建得較為規(guī)范一些。其二是群眾自發(fā)投工投勞修建,大多是將石塊堆砌而成,這種“囤”大多為“干打壘”,其內部結構、防御功能都較為脆弱。其三是由起義軍選址修建。大多義軍為了建立根據地而選址修建。內部結構較為完善,建筑較為牢固。
“囤”一般依地形地貌而建,較小的“囤”用時二個月或一年左右,較大一點的“囤”大約需三年左右或更長一點時間。玉屏侗族自治縣新店鄉(xiāng)老寨村的白巖囤修建前后用了近兩年的時間才完成。白巖囤建在地勢較為險峻的山頂,它分設兩重防護,即一道卡門和一道防護墻,第一道卡門是設在山腰的狹窄道口;其主要功能是對過往的人進行盤查;第二道防護墻是主“囤”外地勢相對較緩的山沿;防護墻是用石頭砌成,高約一米,圍墻外依山勢搭支架木棚,設滾木雷石。同時還密插竹簽,“囤”內則是其主要據點。白巖囤的外型為完全封閉的橢園形,高約5 米,囤內面積約8 畝,可供近千人躲藏。為了便于進出,在東西兩端各建了一個“囤”門。“囤”門設計十分巧妙,進“囤”都是從下往上,每個“囤”口各設兩道門,兩門之間是拐兩個九十度彎的“之”字形通道,通道寬三尺,兩邊石墻上留有若干個防衛(wèi)用的槍孔、炮孔和觀察小孔。炮是用棕樹特制而成的,內放火藥和鐵砂,其殺傷力較強。“囤”門是用厚約五寸的雜木枋特制,并在外面釘有一層鐵皮。同時,為了加強防衛(wèi),“囤”墻內還挖了有深三尺呈倒梯型的掩體墻,守“囤”的人蹲在掩體下,憑借預設的內大外小的孔觀察外面的動靜。
最初,“囤”僅是用作單純防御的軍事工事,后隨著義軍勢力的不斷發(fā)展壯大,單純的軍事工事難以抵御持久的軍事圍困。再加之有的“囤”被攻破后,又不得不重新考慮修建更加牢固的軍事設施問題。于是,各寨的民眾又在原有的基礎上及時修筑起集軍事防御、家養(yǎng)、居住等于一體的功能完備的“囤”。
2.組織與管理
“囤”建設好后,當地群眾便有了防衛(wèi)和新的隙居之所。那么,幾十甚至上千人從山下都搬到“囤”里來居住,是如何進行管理呢?
一是建立了團練組織。團練來源于保甲。即有事為團練,無事為保甲,是在官方的督導下由地方紳士組建,以村寨為基點,筑墻設防,堅壁清野,奉行寓兵于農,實施地方武裝自衛(wèi)。始于唐代,盛于清代,尤其是在清咸、同年間為最盛。這一組織在參與鎮(zhèn)壓太平天國、白蓮教、貴州少數民族起義等過程中發(fā)揮了作用。據《岑鞏縣志》軍事篇第二章“地方武裝”中記載:“清咸豐、同治年間,思州府城設團練總局,各保設團練分局,保下設若干團。團設團總(團首)。團以下設若干甲,甲設甲長;甲以為牌,牌設牌長;牌管到戶,每戶選派團丁1 名,自備刀、槍、矛、棍,農隙定期操練,有事調集參加防堵。坉內設董事、什長、大旗、刀矛手、炮手等。團練防堵經費,由鄉(xiāng)紳捐資和向民眾攤派。各地團練均為當地地主豪紳所把持。”
二是建立了相應的管理機制。從對黔東地區(qū)各個村寨建囤和住囤的實際調查情況來看,每個“囤”都是一個宗族或族親的聚集之所。如:玉屏侗族自治縣田坪鎮(zhèn)金竹村的銀子囤,該“囤”由當地嚴家村民組的村民興建,而住“囤”的人也僅為當地嚴氏宗族的人們。因此,在囤上的組織與管理均由宗族族長號領。有的“囤”則是由周邊幾個村寨不同姓氏的人們共同投工投勞興建。那么,在“囤”上管理則由當地團練負責擔任董事,各個宗族族長以及群眾按相應的職責進行分工,做到職責分明,分工合作,同心協(xié)力。
三是建立了良好的協(xié)同機制。“囤”的修筑并不等于每一天都面臨戰(zhàn)爭危險。于是,寨民們?yōu)榱司S持正常的農業(yè)生產,留下老人、婦女、小孩及幾個青壯年男子負責值守“囤”,大部分年富力強的男性勞動力往往在白天下山搶種農田。一旦有危險即將來臨,山上守“囤”的人即刻報送信息:派人快步傳送信息,在山頂燃起烽煙,敲響鼟鑼。一時間濃煙四起、鑼聲震天。這樣,山下勞作的人聞訊,則及時上“囤”,以確保安全;同時,也向附近的“囤”傳遞了信息。使“囤”與“囤”之間建立了信息共享的聯(lián)防聯(lián)動機制。
三、“囤”的攻防演變
“囤”在不同時期,其攻防情況也不同。據對黔東地區(qū)的走訪調查,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
一是清朝時期。“囤”由最初官府和團練的防御工事變成了義軍的據點,并在抗擊清軍鎮(zhèn)壓的過程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咸同年間(1854 -1872),黔東廣袤的地區(qū)先后發(fā)生或波及的農民起義有10 多次。為了防御義軍的進攻,在官府的召領下,由各個村寨的團練組織當地群眾通過筑“囤”來作為防御工事。但由于各路義軍針對的對象主要是官府和地方團練。據有關資料記載:侗族義軍首領姜應芳在率領侗族群眾起義時,就發(fā)布了討清檄文,提出“大戶人家欠我錢,中戶人家莫亂言,小戶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戶來分田”[1]的綱領。一些地方的少數民族群眾相繼加入了義軍隊伍,成為義軍中的一員。“囤”由此變成了義軍的據點,并在抗擊清軍鎮(zhèn)壓的過程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思州“五坉”會戰(zhàn)。據《岑鞏縣志》“軍事篇”第六章兵事第六節(jié)思州“五坉”會戰(zhàn)記載:咸豐九年(1859)七月,思州苗教軍與清軍在鳳崖等“五坉”的會戰(zhàn)揭開序幕。湖南巡撫駱秉章派遣兆琛、張由根復率湘軍數千人來思州,會合韓超、陳岳霖、張萬書等各部兵練共1 萬余人進行圍剿。清軍采取分進合圍、四面縱火、各個擊破的戰(zhàn)術,首先選擇鳳崖坉作為首攻目標。七月初三日,石阡軍功徐應魁與韓超率部進攻鳳崖。八月十五日,陳岳霖、張萬書、曹遠興等各挑練勇組成敢死隊,乘夜三更時分齊抵鳳崖坉下,施放火彈火箭,焚燒苗教軍營柵,乘勢攻進卡門,守卡義軍同官軍反復拼殺,犧牲數十人。義軍奮不顧身,英勇抗擊,殺得清軍傷亡慘重。二十四日黎明,清軍逼進坉墻,破坉而進,義軍同官軍短兵相接,展開肉搏戰(zhàn)。二十五日,清軍特別是湘軍在付出了殘重代價之后將鳳崖坉攻占。清軍和團練攻取鳳崖、唐家營、谷定、老鷹嘴四坉后,即云集于響鼓坉下,傾全力向響鼓猛撲,義軍拼死抵抗,浴血奮戰(zhàn)。守囤義軍勢孤力單,傷亡增多,難以抵擋各路清軍的猛烈攻勢,響鼓坪終于被清軍攻破。至此,鳳崖等五坉均落入清軍手中。
二是民國時期。“囤”在這一時期主要用于防匪患和兵患。
防匪患。黔東地區(qū)大部分是層巒疊嶂的山區(qū),自然環(huán)境十分險惡。同時,經濟條件貧弱不堪,又加之在軍閥統(tǒng)治下,苛稅百出,人民負擔遠比清代為重。以至于在災荒發(fā)生之時,廣大的人民常在交迫中過著悲慘的生活,人們常常不得不流離失所,四處逃荒,弱者乞討,強者和一些無正當職業(yè)的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殺人越貨,走上為匪的道路。
匪患的興起與發(fā)展,使黔東地區(qū)人民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無法得到保證。據《玉屏文史資料》第六輯記載:“民國十五年(1926),玉屏匪風四起,慣匪首楊松柏、楊松青、王龍章等橫行鄉(xiāng)里,民不聊生”。為了自保,他們在當地團練或宗族族長的號領下,只得再次以“囤”為據點,以提高自我防護能力。
防兵患。在民國初期,兵患之禍猛如虎,對黔東地區(qū)的群眾生產生活以及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危害。據調查,在民國元年(1912)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這22年間,玉屏境內曾發(fā)生各種兵患達7 次之多。如“民國十八年(1929),黔軍李筱榮率兵三師由湘返黔,與周西成爭奪地盤。周西成率兵堵?lián)簦莩觥畺|征之戰(zhàn)’,縣境兵集如山,湘省芷江冷水鋪至黔省鎮(zhèn)遠鎮(zhèn)熊關一線,是雙方爭奪的主戰(zhàn)場。今日周打下,明日李打上,拉鋸戰(zhàn)長達數月,玉屏是戰(zhàn)地中心,首當其沖,民遭此禍,蹂躪更劇。”[2]
四、“囤”在古戰(zhàn)場遺址中的文化意義
清咸同年間轟轟烈烈的貴州少數民族起義及民國初期的歷史階段,留下了人們刻骨銘心的往事,在這血與火的凝結中,“囤”成為了銘刻這段歷史的豐碑。
1.“囤”體現(xiàn)了戰(zhàn)爭背景與生存方式的統(tǒng)一
“囤”主要是清末民初的特殊產物,是黔東廣大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群眾不畏強權的強烈反抗意識的真實寫照。尤其是清咸豐、同治年間,在貴州大地上進行了長達二十余年的民族起義,這在貴州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絕無僅有的。它體現(xiàn)了在封建王朝的高度集權體制下,苗、侗等各族人民在“犯法可以賒死,忍饑則將立斃”[3]的情況下,不畏強暴,選擇了以戰(zhàn)爭方式去表達心靈的訴求,去體現(xiàn)一個民族的存在,去擴大自身的生存空間。民族起義戰(zhàn)爭所留下的精神永遠定格在歷史的天空里,留在了廣大苗、侗等各族人民的記憶里,永遠不會忘卻。
2.“囤”是軍事史學研究的標本之一
“囤”作為古戰(zhàn)場的軍事設施,是冷兵器時代的產物。它在清咸同年間貴州少數民族起義中,不僅是義軍抗擊朝廷官軍殘酷鎮(zhèn)壓的主戰(zhàn)場,而且也是朝廷官軍與地方團練用于防堵義軍的主戰(zhàn)場。在這兩個戰(zhàn)場中,“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于某一個村寨,它遍及黔東地區(qū)各個村村寨寨。“囤”與“囤”之間還建立了“烽火相應、鼟鑼相聲”的聯(lián)防聯(lián)動機制,使“囤”的集群防御效應得到了明顯增強。
與此同時,對“囤”的修筑也十分講究。據清龍緒昌纂的《兵燹志略》(古籍本,未刊印)對“囤”的修筑進行了非常仔細的描述,充分說明要修筑好一座“囤”作為有效的防御工事,達到既可攻,又可守的目的,的確非常不易,它儼然是集古代建筑藝術、軍事學于一體的完美構造。雖然140 多年過去了,但其無處不在、至今仍相對保持較為完好的“囤”營,不僅應成為古戰(zhàn)場遺址的標本之一,而且應是軍事史學研究的標本之一。
3.“囤”是同心協(xié)力、浴血奮戰(zhàn)、攜手共進精神的體現(xiàn)
黔東地區(qū)苗、侗等各族人民為了求生存、求進步、求發(fā)展,以“囤”為家,以“囤”為營,在長期的實踐中,集聚了苗、侗等各族群眾同心協(xié)力、浴血奮戰(zhàn)、攜手共進的民族精神。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集聚了義軍將士們以及苗、侗等廣大少數民族群眾奮勇抗敵的力量。在抗擊朝廷官軍和地方團練鎮(zhèn)壓過程中,踞守“囤”營的義軍將士們以及苗、侗等廣大少數民族群眾所表現(xiàn)出的那種頑強拼博、浴血奮戰(zhàn)的勇氣,可畏是驚天地,泣鬼神;二是集聚了各族民眾同心協(xié)力的力量。在修筑囤的過程中,寨民們都義無反顧自愿出工出力上山修囤;在危險來臨的時候,他們以囤為家,分工合作,忠于職守,實現(xiàn)了從一個單純的農民向“戰(zhàn)時為軍、閑時為民”大轉變。
“囤”在清咸同年間和民國時期,不僅淋漓盡致地發(fā)揮出了它獨特的防御作用,而且給當今社會留下了一筆不可復制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同時,“囤”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是生活在黔東地區(qū)苗、侗等各族人民不屈不饒的奮斗史的真實寫照。
[1]《貴州通史》編委會.貴州通史:第三卷[M].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350.
[2]玉屏侗族自治縣政協(xié)文史委.玉屏文史資料:第六輯[M].膳印本.1993:35.
[3]咸同起義[EB/OL].[2014 -05 -31]. http:∥gz. 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1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