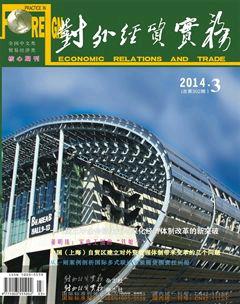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發展的新特征及其啟示
葉茂升 韓肖英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壓力下積極進行結構調整,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特征。主要表現在紡織與服裝細分產品更具差異化、企業規模微型化、生產技術柔性化以及貿易政策自由化等方面。在我國紡織服裝業面臨來自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壓力下,研究美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成功經驗,對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發展的新特點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的統計,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紡織品服裝進口國,紡織服裝產業對進口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進口紡織服裝產品并沒有對本國紡織服裝企業產生嚴重的沖擊,進口產品已經成為美國企業控制全球紡織服裝產業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外包企業與美國本土的紡織服裝企業之間的共生性已經遠遠大于競爭性,美國國內現有的紡織服裝企業大部分已經退出了產品生產環節,轉型成為貿易商和品牌制造商,他們的主要任務不再是負責產品的生產與制造,而是聚焦于協調和管理產品供應鏈上的各個環節,通過生產外包以及密布全球的分銷網絡形成了與發展中國家供應商之間綿密的協同合作關系。縱觀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服裝產業發展的新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總體呈現不斷萎縮的趨勢
根據BEA的統計數據,美國2008年國內紡織品總產值為578億美元,比2000年的851億美元下降了32.1%,服裝國內總產值下降的幅度更大,由2000年673億美元下降至2008年的342億美元,降幅高達49.2%。與此同時,紡織服裝產業對美國GDP的貢獻率也進一步降低,由2000年0.83%下降至2008年0.35%。從就業情況來看,2009年美國登記在冊的紡織和服裝產業從業人員分別為12.5萬人和17萬人,分別比2000年的行業從業人數下降了66.9%和65%,在整個制造業的從業人口中,僅有1.03%和1.04%比重分別來自紡織和服裝產業。
從貿易收支來看,美國對國外進口紡織服裝產品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美國紡織品進口滲透率(紡織品進口占國內總產值的比)從2000年的20.2%上升至2008年的29.1%,而同期服裝進口滲透率則從51.1%上升至76.5%。數據分析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和服裝產業對GDP和就業增長的貢獻率均呈不斷下降趨勢,紡織服裝產品市場需求主要依靠國外進口來滿足,行業萎縮趨勢較為明顯。
(二)美國紡織品服裝進口的來源地更加集中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印度、孟加拉以及越南等低工資成本的發展中大國成為對美國出口的最大贏家,尤其以中國最為矚目。2000-2009年間,中國對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增長率分別高達14.9%和13.6%,2009年中國占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市場份額分別為35.4%和39.1%,超過了印度、歐盟27國、巴基斯坦以及墨西哥對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規模的總和;另一方面,加拿大、墨西哥、CAFTA、EU-12、泰國等傳統主要進口來源市場由于受到多邊纖維協定(MFA)終止的影響,對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呈現大幅萎縮的趨勢。
(三)美國紡織品服裝進口的貿易條件明顯改善
按照北美行業分類系統NAICS分類,2000-2009年期間,美國纖維、紗線(3131)以及紡織纖維(3132)兩類產品的進口額分別下降了38.6%和29%,而織物整理制品(3133)、針織服裝(3151)和紡織纖維(3132)、服裝附件(3152)以及羊毛服裝(3152)四類產品的進口額分別增長了41.4%、59.5%、4.3%和22.5%。在進口金額下降的兩類產品中,纖維、紗線(3131)主要是由于進口價格上漲導致進口數量減少引起的,而紡織纖維(3132)主要源于進口價格的大幅下降。在進口保持增長的四類產品中,只有織物整理制品(3133)價格大幅上漲,其他三類產品均是由于價格下降引起的數量增長產生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占美國進口金額最高的紡織纖維(3132)和服裝附件(3152)兩類產品的進口價格指數2009年僅為45.4和89.1,而進口價格指數大幅上漲的織物整理制品(3133)在總進口中所占的比重僅為1%。表明盡管美國紡織服裝市場對進口依賴程度很高,但主要都是一些市場競爭激烈、價格彈性較高的終端消費品,而壟斷性強、價格彈性弱的織物整理制品(3133)進口需求很少。如果不考慮出口價格因素的影響,僅從進口價格變動趨勢來看,美國紡織品服裝的總體貿易條件在不斷改善。
(四) 美國紡織與服裝產品差異化特征更加突出
首先,從資本化特征來看,美國紡織相對于服裝企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美國紡織業的資本-勞動比率指數從2002年的100%上升至2007年的119%,而同期服裝產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卻下降為95%。美國紡織企業資本化比重提高的事實還可以從資本設備更新投資的增長得到印證。2004年-2008年,企業對紡織設備更新的投資額占到紡織品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2.92%增長到2008年的4.54%,四年翻了一番。而該期間,服裝企業無論是在設備更新還是企業生產規模上都呈現不斷萎縮的趨勢。其次,從勞動生產率的對比來看,美國紡織企業的生產率水平遠遠高于服裝企業。以人均產出為例,2009年美國紡織企業的人均產出為110890美元,超出服裝企業人均產出水平的56.3%。這表明紡織業的生產率在提升,而服裝產業的生產率水平卻在不斷下降。
(五) 美國紡織服裝企業的微型化特征更為明顯
從企業的規模分布來看,2008年紡織企業人數為0-4人、5-9人、10-19人、20-99人以及100人以上的比重分別為35.4%、15.9%、13.0%、20.3%和15.5%。與1998年相比,100人以上的企業比重下降了2個百分點,而0-4人的企業比重提高了3.5個百分點。在服裝產業方面,企業微型化的特征更加突出。2008年服裝企業人數為0-4人、5-9人、10-19人、20-99人以及100人以上的比重分別為43.7%、19.3%、15.9%、16.5%和4.5%。與1998年相比,100人以上的企業比重下降了7.6個百分點,而0-4人的企業比重提高了9.7個百分點。數據分析發現,美國大部分紡織服裝企業都是4人以下的微型企業,這與他們采用柔性化和個性化的生產技術是密不可分的。endprint
二、“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結構調整
(一)通過增強價值鏈的 治理能力來獲取更多的產業利潤
依據Humphrey and Schmitz(2004)所提出的有關全球價值鏈的四種分類(市場導向型、均衡網絡型、俘獲網絡型以及層級型),紡織服裝全球“價值鏈”屬于典型的“俘獲型”價值鏈。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紡織服裝零售商以及品牌經銷商作為價值鏈的主導者,控制著產品設計、質量標準、產品交貨、庫存以及價格等關鍵的“價值鏈”結點,并通過全球生產網絡主導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制造商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模式和利益分配。
一方面,他們加強對資本、技術以及品牌等高級生產要素的持續投入,在研發、設計、營銷等環節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企業的買方壟斷優勢;另一方面,充分發揮自身捕獲市場信息的能力,借助龐大的營銷網絡和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在消費終端和制造商之間構筑“護城河”,確保壟斷利潤最大化。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絕大多數服裝企業已經退出傳統的產品制造領域,轉而聚焦具有高附加值的非生產環節,通過強化設計、工藝、環境標準,增強國際競爭的軟實力,并創造源源不斷的利潤增長空間。
(二) 產品生產和銷售更趨柔性化和個性化
紡織服裝作為最具時尚性的傳統產業,市場需求具有多樣性和個性化的特點,大規模標準化的制造模式已經難以滿足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紡織服裝企業開始了柔性化和個性化生產模式的探索。他們通過價值鏈的空間分離,將設計、生產和營銷等各價值鏈環節分布于不同國家,并通過先進的通信技術手段將配置在世界各地的供應鏈“結點”進行有效整合,不僅能夠對市場需求的變動做出快速響應,而且利用不同國家的資源優勢有效降低了生產成本。
以耐克和阿迪達斯為例,棉花和氨綸的生產在美國、紡紗在印度、縫制在孟加拉、縫紉制衣機械來自德國、品牌設計在意大利、拉鏈來自日本、零售商是法國、貿易商在中國香港,而市場則遍布全球。事實上,柔性化和個性化生產已經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紡織服裝企業一種主導的生產模式,他們開發出了與之相適應的柔性制造系統(FMS),通過電腦、數控機械、機器人、自動化倉庫等先進工具實現自動化的加工、制造與管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自動化系統可以與互聯網連接,以實現網上“按需定制”。美國企業積極借助于信息和互聯網技術,成功地向數字化時代轉型。
(三) 通過區域性的貿易合作機制推動紡織原料出口的對外擴張
為了配合美國紡織服裝企業整合全球和區域生產網絡,美國政府通過區域性的貿易合作機制,對進口美國纖維、紗、線等原材料的外國產品給予特別優惠的進口關稅,以推動美國上游紡織品的對外出口。美國自1985年以來先后與其他國家簽訂了11個涉及紡織服裝產品的自由貿易協定;另外美國還通過簽訂《非洲增長與機會協定》、《加勒比海貿易伙伴協定》、《安第斯貿易促進和禁毒法案》以及《海底紡織品服裝貿易優惠協定》等特殊的貿易安排推動美國紡織服裝產品對上述地區的出口。
在一系列自由貿易機制的推動下,美國主要紡織原料的出口依存度呈直線上升趨勢。美國旨在推動紡織服裝區域貿易自由化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2008年,美國織物整理制品(NAICS3133)的出口依存度高達65.9%,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或優惠貿易安排的國家成為美國紡織原料的主要進口國。例如,墨西哥、加拿大、尼加拉瓜、塞爾瓦托、多美尼加、洪都拉斯等國對美國紡織品進口依存度分別高達81.7%、63.1%、92.4%、82.8%、74.8%和94%。美國通過簽訂有關紡織品服裝領域的自由貿易協議,有力地推動了上游紡織原料制品的對外擴張。
三、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調整對我國的啟示
第一,注重企業“價值鏈”整合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當前,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仍然處于“底端”,缺乏對產品標準以及市場價格的主導能力,全然淪為發達國家紡織服裝跨國公司的廉價代工者,整合價值鏈體系,提升“價值鏈”治理能力是我國紡織服裝企業面臨的最為緊迫的任務。大量研究表明,順延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構筑的全球價值鏈進行產業升級面臨價值鏈上游企業的殘酷“遏制”和“圍堵”,因而構建依托本土市場為中心的國內價值鏈體系將是提升我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一條可行路徑。而在這一產業升級過程中,依托本土市場所提供的需求空間積極培育和發展高級產品要素將是構建“國內價值鏈”最為核心和關鍵的一環。
第二,對紡織和服裝產業采取不同的結構調整政策
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紡織業相對于服裝產業具有更加密集的資本和技術特征和更頑強的生命周期。主要原因是紡織產業中資本與勞動之間要素的替代彈性更大,一旦因工資上漲導致成本壓力時,企業可以通過加快技術設備更新、提升生產過程的信息化水平等手段降低對勞動投入的依賴,從而有效彌補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而服裝產業所固有的勞動密集型特征很難通過強化資本投入進行替代。美國等發達國家即使在工資成本大幅高于發展中國家水平的情況下仍然保持著部分紡織原料產品(NAICS3133)的國際競爭優勢,但在服裝領域基本退出了生產制造環節這一事實即是印證。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面臨成本壓力的紡織企業可以通過資本設備更新和提升信息化水平實現對產品成本的控制,而服裝企業應該適時考慮將生產制造基地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從而蛻變為服裝貿易和品牌經銷商,通過產業鏈的整合來創造更多的利潤空間。
第三,采取更趨柔性化和個性化的生產技術
根據美國佛羅德-沙利文咨詢公司的調查,過去10年中,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平均批量生產已經下降了1/3。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必須適應消費者定制化時代的到來,積極采用柔性制造系統,通過信息和互聯網技術的大量應用,實現由生產者驅動向消費者驅動的市場需求模式的轉變。
第四,通過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促進紡織上游產品的對外出口
當前越南、孟加拉等部分東南亞國家在服裝生產領域已經對我國構成競爭壓力,未來我國服裝產業向上述地區轉移的速度還會加快。我國可以借鑒美國與南美洲國家簽訂優惠貿易協定的經驗,積極與周邊東南亞國家簽訂有關紡織和服裝產品的自由貿易協定,推動我國紡織上游產品對上述東南亞國家的出口,提升我國在區域紡織服裝生產網絡中的國際分工地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