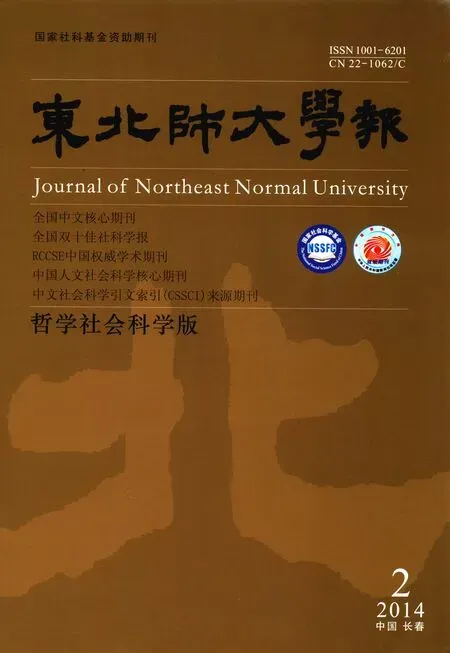財產權規則與外觀法理的沖突與協調
——基于股權轉讓糾紛司法裁判的實證視角
汪青松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重慶401120)
財產權規則與外觀法理的沖突與協調
——基于股權轉讓糾紛司法裁判的實證視角
汪青松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重慶401120)
股權轉讓蘊含多重社會關系,涉及的法律調整極為復雜,由此導致此類糾紛成為司法裁判中的一大難題。民法中的傳統財產權規則與公司法中的外觀主義規則之間的沖突是導致這一難題最為主要的制度性原因,二者在股權性質界定、股權歸屬判定和股權變動判定上都存在明顯沖突。法官在股權轉讓糾紛裁判中的認知差異正是這些沖突對實踐產生影響的直觀反映。相應的協調路徑既需要在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民事審判與商事審判在司法理念與規則運用上的區別,也需要在相應的制度設計上注重對民商事規則的銜接與協調。
股權轉讓糾紛;財產權規則;外觀法理;司法裁判
股權轉讓糾紛是商事領域中的一種常見糾紛類型,也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個歷久彌新的裁判難點。導致這一難題的原因主要在于股權轉讓糾紛涉及多種社會關系情景,因此需要多個法律領域加以調整,而這些法律領域的具體規則之間往往存在較大的差異與沖突。我們通過對大量的股權轉讓糾紛司法裁判文書的梳理分析發現,民法中的傳統財產權規則與公司法中的外觀主義規則之間的沖突是導致股權轉讓糾紛裁判難題最為主要的制度性原因。本文將在對股權轉讓情境下的社會關系及其法律調整的復雜性進行簡要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典型案例重點對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之沖突在股權轉讓糾紛法律適用中的具體表現進行類型化歸納,并在此基礎上從司法實踐與制度設計兩個方面提出協調這一沖突的相應建議。
一、股權轉讓情境下的社會關系及其法律調整的復雜性
易于引發糾紛的股權轉讓主要是基于約定原因的轉讓,本文的研究也是以此類轉讓作為實證研究的基礎。從法律關系構成上看,基于約定原因的股權轉讓以買賣、贈與或者夫妻離婚財產分割為表現形式,以股權作為轉讓標的,但在這一看似簡單的標的背后實際上蘊含著多重社會關系,相應的法律調整需求也極其復雜。
(一)股權轉讓所蘊含社會關系具有多重性
1.出資關系構成股權生成的基礎關系。股權轉讓以既存的股權為標的,但股權本身并不是一種天然存在,而是要經由出資行為轉化而成。因此,股權生成的基礎性關系是出資人向公司的出資關系。盡管基于約定原因的股權轉讓在表面上看是一種立足于轉讓雙方合意的獨立社會關系,但在很多情形下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更為基礎的出資關系的影響和制約,比如用于出資的財產的實際歸屬與股權登記歸屬不一致的隱名出資[1]、共有財產出資以及虛假出資或不實出資等。
2.公司組織構成股權依存的結構關系。盡管關于公司本質的諸多學說存在明顯差異,但其共同之處在于都承認公司組織是一種關系型構造,無論是作為“合同聯結”的經濟結構還是作為“客觀實在”的法人結構。因此,作為股權轉讓之標的的股權本身也不是一種獨立存在,而是依存于公司組織這一結構關系中,這一結構既包括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關系,也包括股東與股東之間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股權轉讓正是引發公司結構關系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換言之,與其說股權轉讓的標的是一種財產權,毋寧說所轉讓的是一種寓于一定結構之中的特定關系。
3.契約關系構成股權變動的法律事實。從廣義上理解,我們可以將所有基于約定原因的股權轉讓都視為一種契約關系。如果說上述兩種社會關系是隱含在股權轉讓的背后,那么契約關系則是股權轉讓的外在表現。按照民事法律關系的基本原理,契約關系可以被理解為導致股權變動的法律事實。但需要指出的是,股權變動往往不能單獨依靠契約關系實現,因為其在很多情形下要受到來自上述兩種關系的相關因素的制約,如其他股東對外部轉讓的同意、公司股東名冊記載的變更等。
(二)股權轉讓所涉及法律調整的復雜性
1.股權轉讓要受到民法中的財產權規則的調整。股權轉讓一般被視為一種財產權轉讓,因而要受到財產權規則的調整。這些調整主要包括:(1)物權與債權二元劃分的財產權體系對股權性質判定的影響。眾所周知,民法領域的傳統財產權規則是基于物權與債權二元劃分而構建,因此關于股權性質的物權與債權之爭至今尚未完全塵埃落定。(2)調整用于出資之財產的法律規則對于股權歸屬判定的影響。如出資之財產的共有規則、委托代理規則,以及動產的善意取得規則等。(3)財產變動規則對于股權變動判定的影響。如物權變動的登記規則、一般債權變動的交付規則、共同共有財產處分的合意規則以及共有人的優先購買權規則等。
2.股權轉讓要受到公司法中的特定規則的調整。由于股權在客觀上依存于公司組織的結構關系中,因此公司法必然要對股權本身及其轉讓設定專門的調整規則。這些調整規則主要包括:(1)關于股權成立及其歸屬證明的規則;(2)關于股權內容及其行使方式的規則;(3)關于股權轉讓途徑及其限制的規則;(4)關于股權變動程序及其效力的規則等。
二、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沖突的理論分析
上文的分析表明,股權轉讓既要遵循民法的財產權規則,又要受到公司法相關規范的調整。而如果從法理基礎上看,民法的傳統財產權規則與公司法相關規范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如果說前者構建是以權利客體的實際歸屬為基礎的話,那么后者的構建則是基于外觀主義。當兩種分別基于不同法理基礎的規則共同調整同一社會關系時,就難免會產生沖突。
(一)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在股權性質界定上的沖突
從直觀的邏輯上看,股權是作為股東向公司出資財產的對價,因而其本身也應當屬于一種財產權。但同時,股權有別于傳統財產權的特性在于其在外觀上體現為一種綜合性、關系性的權利,具有一定的非財產性和涉他性。如果從傳統的二元財產權規則體系出發,股權的性質要么是一種物權,要么是一種債權。而無論是“物權說”或者“債權說”都無法完全反映出股權的特質,特別是無法包容股權的非財產性內涵,如股東所享有的各種參與性權利。公司法立足于股權的綜合性、關系性的實際外觀,將其界定為公司法上的一種獨立權利,這種界定有助于克服傳統財產權規則的上述缺陷,但又面臨著如何與財產權規則進行銜接協調的問題。
(二)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在股權歸屬判定上的沖突
民法中的傳統財產權規則基于所有權神圣理念,較為注重財產的實際歸屬,當財產歸屬的外觀與其實際不符時,實際所有人的利益一般會被置于優先保護的地位,諸如無權占有、無權處分、物權法中的登記更正等規則都體現了這一理念。當然,傳統財產權規則也對善意第三人基于權利外觀而產生的信賴利益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不過這種保護仍然是屬于一種“真實優于外觀”的消極信賴保護,即賦予外觀信賴人因信賴權利外觀而產生的損害以賠償請求權,而非履行請求權。當然,對于不需要進行登記的動產,也允許在具備嚴格的構成要件時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但這一制度對于需要登記的財產權并不適用。因此,根據傳統的財產權規則,股權歸屬的判定應當以其出資的實際所有為依據,即如果用于出資的財產所有人與持股人不一致,股權應當歸屬實際出資人;如果用于出資的財產為共有而持股人僅登記為一人,股權也應當屬于共有財產,需要遵循共有財產的管理與處分規則;如果名義持股人向第三人轉讓股權,第三人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獲得股權,不過獲得的依據并不是名義持股人的有權處分,而是作為無權處分之特別情形的善意取得。
與傳統財產權規則不同的是,公司法在判定股權歸屬時一般并不考慮作為出資的財產的來源和歸屬,而是依據股權在相關文本上所表現出來的持有外觀。比如,中國《公司法》第33條第2款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這實際上是明確了公司法對于股權歸屬的判定是以持有外觀為基礎,采用股東名冊記載標準。商法學者一般也認為工商登記、公司章程記載、股東名冊記載等形式條件對于公司股東資格的認定具有決定性意義[2]。財產權規則與外觀法理在判定股權歸屬上的這種差異在出資財產所有人與登記持股人一致的情況下一般不會產生問題,而當股權的持有外觀與作為其生成基礎的出資關系不一致時就會引發沖突。這種沖突主要表現在:(1)代理規則與登記持有規則的沖突,如實踐中大量存在的隱名出資、代為持股等情形;(2)共有規則與登記持有規則的沖突,如以夫妻或家庭共有財產出資的情形;(3)善意取得規則與變更登記規則的沖突。
(三)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在股權變動判定上的沖突
關于權利的變動,傳統財產權確立了不動產轉讓的登記主義、動產轉讓的交付主義以及債權讓與的通知主義等一般性規則。而由于股權在傳統財產權體系下面臨著性質界定的困境,對于其變動的判定標準選擇自然也就成為一大難題。對此有些學者認為股權與物權差異較大,而與債權較為接近,因而以債權讓與的理論為參考分別提出了“轉讓合同生效”標準、“轉讓合同生效+通知”標準、“轉讓合同生效+履行”標準等,而這些主要立足于轉讓雙方當事人之合意的標準或多或少都存在對股權的關系性、涉他性等特殊性未能予以充分考慮的不足。與傳統財產權規則不同的是,公司法對于股權變動的標準選擇考慮到了其作為關系性、涉他性權利的外觀,規定股權的變動除了要依據轉讓雙方的合意之外,還需要完成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的變更程序。
三、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沖突的實證分析
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在理論層面的沖突必然會對司法實踐中的法官認知產生直接影響。本部分將從實證的角度,結合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案例來對法官的認知差異與沖突進行深入分析。
(一)關于股權性質的認知
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在股權性質界定上的沖突直接導致了司法實踐中對于股權性質認知的模糊不清。根據我們對司法裁判文書的分析,絕大多數裁判文書沒有對股權的性質進行探討,其隱含的理念仍是將股權視為一種與傳統的財產權并無實質區別的一般財產權。有少數裁判文書關注到了股權性質的特殊性,但具體認知與表述也不一致,如有的認為“股權是具有包括財產權等多種權利在內的綜合性權利形態”①詳見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2008)長民二(商)初字第1020號民事判決書。;有的認為“股權可以概括為具有財產權、身份以及管理權為主要內容,集身份、財產與管理等權利于一體的一種獨立的、綜合性的權利形態,既不同于物權,也區別于債權”②詳見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2010)昌民初字第4654號民事判決書。;有的認為“股權在性質上屬于社員權,股東出資創辦作為社團法人的公司,成為該法人成員,因而取得社員權。”③詳見河南省鶴壁市山城區人民法院(2011)山民初字第1838號民事判決書。而不論是“綜合性權利”還是“社員權”,其法律內涵上都與“公司法上的獨立權利”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沒有能夠清晰反映股權所具有的關系性特征。
(二)關于股權歸屬的判定
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沖突在司法實踐中體現得最為突出的領域就是股權歸屬的判定。根據我們對司法裁判文書的梳理分析,審案法官關于股權歸屬判定的認知差異主要包括:
1.當實際出資人與登記持股人不一致時,誰應當享有股東資格?立足于傳統財產權的實際所有標準的法官一般認為實際出資人應當享有股東資格,其有權處置登記于持股人名下的股權;而立足于公司法所確立的持有外觀標準的法官則會傾向于認為實際出資人由于不具有公司法所規定的股權享有的外觀要件,因而不應當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股東。
2.當實際出資證明書、股東名冊與工商登記不一致或者沒有同時具備時,如何確認股權的歸屬?立足于傳統財產權的實際所有標準的法官一般認為出資是確認股東資格和股權歸屬的實質要件,其效力高于股東名冊與工商登記等形式要件以及參與公司決策等表象特征;而立足于公司法所確立的持有外觀標準的法官則會傾向于認為在股權轉讓情境下,出資屬于另一法律關系,股東的實際出資情況不應當影響股權對外轉讓,即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資料上記載的持股人應當被視為股權的歸屬人。
3.以共有財產出資而僅登記于一人名下的股權是否屬于共有,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是持有人能否單獨對其名下股權予以處分?司法實踐中的觀點可以分為三種:一是肯定論,即認為共有財產出資形成的股權即使是僅登記于一人名下,也應當屬于共有財產,此種觀點顯然是基于傳統財產權的實際所有標準;二是否定論,即認為共有財產出資形成的股權只能歸登記持有人所有,能夠構成共有的最多只能是股權的收益,此種觀點顯然是基于公司法所規定的持有外觀標準;三是折衷論,即認為共有財產出資形成的股權應當屬于共有,但從管理權的角度來看,登記的股東應是共同權益的代表,可以單方處分。
(三)關于股權變動的判定
司法實踐中關于股權變動的判定所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股權變動判定標準的選擇方面。根據我們對司法裁判文書的梳理分析,審案法官在確定股權變動時所選擇的判定標準主要包括:
1.合意達成標準。如在“天津港保稅區潤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與中國汽車貿易總公司、中兆源(北京)典當有限公司、中兆源(北京)拍賣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股權轉讓屬財產權利轉讓,其與實物轉讓中的即時交付有別,自拍賣成交當日相應股權即已發生轉移。”①詳見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0)豐民初字第1660號民事判決書。在“徐向一與大連吉遠輪船有限公司、香港萬通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二審法官認為“上訴人已于2002年12月24日將其全部股權轉讓,故上訴人自轉股協議生效后即喪失吉糧公司股東資格。”②詳見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遼民三終字第51號民事判決書。在“張某某與趙某、上海新瑞禾建設工程造價有限公司、任某某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二審法官認為:“張某某、任某某將股權轉讓給趙某,張某某、任某某并收取股權轉讓款是各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表明有關新瑞禾公司的股權轉讓事宜已經完成。雖然目前為止工商登記的股東仍為張某某、任某某、趙某,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變更登記是一種公示行為,其本身不能否定新瑞禾公司股權轉讓事宜已經完成的事實。”③詳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1)滬二中民四(商)終字第292號民事判決書。
2.股權憑證交付標準。如在“林微與何斌、金悅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中,被告方一股二賣,一、二審法官均認為:被告將股權憑證交付后一受讓人,致使簽訂在前的《股權轉讓協議書》的合同目的已無實現之可能④詳見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南市民二終字第150號民事判決書。。
3.股東名冊變更標準。如在“徐向一與大連吉遠輪船有限公司、香港萬通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一審法官認為:“股東名冊是公司依照法律規定登記對本公司進行投資的股東及其出資情況的簿冊,股東名冊作為公司的法定置備文件,具有辨別股東身份的重要作用。”⑤詳見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遼民三終字第51號民事判決書。在“余茂成與雷起航、第三人雷明章、張高泉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審案法官認為:“合同簽訂后,重慶雙江焊接材料有限責任公司對原告的股東身份進行了認可,余茂成也實際參與公司的重大事項決策及生產經營管理活動,行使股東權利。因此,原、被告之間的股權轉讓合同已經生效并實際履行。雖然公司至今未辦理相應的股權變更工商登記,但并未影響原告實際行使其在公司的股東權,更不能直接導致原、被告間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⑥詳見重慶市榮昌縣人民法院(2010)榮法民初字第769號民事判決書。
4.工商登記變更標準。如在“周兵與張保衛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二審法官認為:“周兵與張保衛經協商一致由周兵將其持有的村里人家公司部分股份轉讓給張保衛,張保衛亦按約支付了相應的股權轉讓款,但周兵并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股權變更手續,并在嗣后又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轉讓給他人并辦理了工商變更手續,為此周兵應將前期收取的股權轉讓款返還給張保衛。”⑦詳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終字第09827號民事判決書。
另外,與股權變動判定密切相關的問題還有股權的善意取得,該制度的適用也是股權轉讓糾紛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適用難點。根據我們對所收集的司法裁判文書的梳理,善意取得制度在股權轉讓糾紛裁判實踐中的適用狀況存在以下特點:一是由于存在《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8條的規定,司法實踐中的法官一般并不否定股權可以適用善意取得;二是司法實踐中真正適用該制度的案例極少,一些案例即使具有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情境條件,審案法官一般也是選擇用后一股權轉讓已經完成登記程序的理由來支持后一受讓人獲得股權;三是該制度在實踐中的適用難點主要表現在對受讓人“善意”的認定上,如有的法官采取的是“推定善意”原則(即需要主張轉讓無效一方證明受讓人存在惡意),有的法官則是采取“推定惡意”原則(即需要受讓人主張和證明自己的受讓是基于善意)。
四、股權轉讓情境下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沖突的協調路徑
通過前文的論述不難發現,股權轉讓糾紛難題的形成既有源于該類糾紛自身復雜性的客觀因素,也有源于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沖突的制度因素,以及由此導致的司法裁判中的理念不清的主觀因素。因此,相應的協調路徑首先需要尊重商法不同于傳統民法的特殊思維[3],要了解商事審判的特殊性[4],進而在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民事審判與商事審判在司法理念與規則運用上的區別[5];其次需要在相應的制度設計上注重對民商事規則的銜接與協調。
(一)對股權轉讓情境下的商事領域與傳統民事領域進行準確界分
盡管股權轉讓糾紛中存在著商事領域與傳統民事領域相互交織的客觀情形,但司法實踐中在處理此類糾紛時仍然要特別注意兩個領域的區分,并以此來指導具體的法律適用。基本的區分規則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傳統民事領域以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為邊界,以不直接涉及第三方利益為前提。因此,如果是實際出資人與名義持股人之間因對股權收益歸屬發生糾紛,或者是共有人之間因對共有財產出資股權的處置發生糾紛,一方起訴另一方要求返還其應得款項或者予以損害賠償而不涉及對轉讓協議效力的認定,則應當以傳統民事領域的基本規則來指導法律適用。其二,商事領域以當事人之外的第三方關系的融入為基礎,以直接涉及第三方利益為條件。因此,如果實際出資人與名義持股人之間的糾紛或者共有財產出資股權糾紛直接指向以第三人為受讓人的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問題,則應當以商事領域的基本規則來指導法律適用。
(二)對股權轉讓情境下的合同效力與合同履行的判定適用不同標準
正如前文所述,股權不是對某種具體有形物的占有,其實質上是一種與其他股東和公司法人之間的特定關系。這種涉他性決定了股權轉讓合同從訂立到履行的全過程不可能完全依賴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來完成。為協調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之間的沖突,應當采取合同效力判定與履行判定相分離的立場。即對于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判定應當置于合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情境來考量,可以依據當事人之間的合意,不得以股權變動尚未發生為由否認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而對于股權轉讓合同能否履行的判定應當置于合同當事人與公司和其他股東之間的關系情境來考量,有效股權轉讓合同僅產生賣方將股權讓渡買方的合同義務,而非導致股權的自動、當然變動[6]。
(三)注重對股權轉讓情境下的商事交易安全與信賴利益的保護
傳統民法中的財產權經由出資轉化為股權,在性質上也就變成了商事權利[7]。當這種商事權利在商事領域發生動態的轉移(如向第三人轉讓),有關商事交易的基本規則應當優先適用。基于商事交易安全和信賴利益保護的需要,商法對于商事權利歸屬的判斷非常注重外觀主義。因此,在隱名出資形成的股權或者共有財產出資形成的股權向第三人轉讓時,應當基于維護交易安全的基本理念,以商法的公示主義與外觀主義原則為指導嚴格貫徹股東資格認定的形式主義[8]。即在股權轉讓情境下,應當將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資料上記載的股東視為股權的獨立所有人,由其和第三人之間進行的股權轉讓,不能夠僅僅以未經實際出資人或者出資財產共有人同意為由而認定為無效。
(四)從公司法制度設計上注重財產權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的銜接協調
首先,要合理解決共有財產出資股權的歸屬問題。從前文所述及的共同財產出資股權是否屬于共有的爭論中不難發現,簡單的肯定抑或否定都缺乏明確具體的實在法依據,在價值判斷上也都難免有失偏頗。因此,最為有效的解決方式應當是從公司法的制度設計上予以明確規定。我國《公司法》對于共有財產出資所形成股權的共有問題并沒有明確規定,但同時也沒有禁止有限公司將共有關系體現在股東名冊中,即將某一份出資及其所形成股權的對應股東登記為兩個共有人。因此,為避免共有財產出資股權在處分時所出現的共有規則與外觀主義規則的沖突,可以允許出資人在向有限公司出資時表明是以共有財產出資,并在股權登記環節注明,未標明者推定為以個人財產出資。對于已表明是以共有財產出資的股權,在處分時應當適用共有財產的處分規則,即應當取得全部共有人的同意;在共有人就共有股權進行分割時,關于股權歸屬于非登記持有一方的分割協議不視為外部轉讓,其他股東不可以主張優先購買權①法國公司法并不將一方登記持有的股份在夫妻之間的轉移或者轉讓視為外部轉讓。按照《法國公司法典》第223-13的規定,在公司章程沒有另行規定的情況下,“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通過繼承自由轉移,或者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清算的情況下,在夫妻之間自由轉移,并且可以在夫妻之間,尊、卑直系親屬之間自由轉讓。”參見羅結珍譯:《法國公司法典》(上冊),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頁。。
其次,要進一步明確股權變更的判定標準問題。應當通過司法解釋明確將股東名冊變更作為股權變更的判定標準,同時也要明確股東名冊變更與工商登記變更之間的關系。公司股東的工商登記屬于宣示性的登記,而不是設權性登記。因為公司將其確認的股東向工商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公司的確認已經實現,股東的身份已經確定,股東的權利也已經產生,股東的工商登記僅僅是一種宣示而已。兩者之間的關系決定了在發生差異的時候,即工商登記的內容與公司股東名冊登記內容不一致的時候,作為一般原則,公司股東名冊的登記內容應作為確認股權歸屬的根據;在股權轉讓合同的當事人之間、股東之間、股東與公司之間因為股權歸屬問題發生糾紛時,當事人不得以工商登記的內容對抗公司股東名冊的記錄,除非有直接、明確的相反證明。
最后,要妥善處理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問題。由于股權不同于一般的動產,雙重登記規則導致其無法真正形成所有與占有分離的外觀,因而缺乏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客觀基礎。另外,在共有財產出資股權的轉讓情形下,善意取得與外觀主義規則存在明顯沖突,即該制度的適用需要首先承認單方持有的股權構成共有財產,而這是與股權歸屬的持有外觀相矛盾的。因此,現行的《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8條在某種程度上說并非是基于審判經驗,也不符合順應立法政策的取向原則[9],應當予以修正,即如果股權轉讓后尚未向公司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原股東將仍登記于其名下的股權再行轉讓,后一受讓人獲得該股份的法律依據并不是基于作為無權處分之特例的善意取得,而是基于有權處分。
[1]趙旭東,顧東偉.隱名出資的法律關系及其法律效力[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1(2):141-148.
[2]周友蘇.淺析股東資格認定中的若干法律問題[J].法學,2006(12):78-84.
[3]王保樹.尊重商法的特殊思維[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2):28-30.
[4]葉林.商法理念與商事審判[J].法律適用,2007(9):17-20.
[5]趙萬一.商法的獨立性與商事審判的獨立化[J].法律科學,2012(1):54-64.
[6]劉俊海.論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J].法學家,2007(6):74-82.
[7]王艷梅,龐昀曦.日本空白票據規則及對我國的啟示[J].現代日本經濟,2013(1):35-42.
[8]范健.論股東資格認定的判斷標準[J].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6(2):66-73.
[9]陳甦.司法解釋的建構理念分析——以商事司法解釋為例[J].法學研究,2012(2):3-19.
Harmoniz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Property Rule and Surface Jurisprudence in Judging Transfer Dissension of Shares
WANG Qing-song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The transfer of shares includes multipl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involves complicated law adjustment,which makes it become one difficulty of judicial judgment.The conflict between property rule in traditional civil law and surface jurisprudence in commercial law exists in how to estimate the character and possession or alteration of shares,which is the primary institutional reason to result in that difficulty.The influence of that conflict reflects the cognizing difference between judges.To harmonize it,we need grasp the differences of judicial ideas and rule application between civil trial and commercial trial and pay attention to linking up and harmonizing civil rule and commercial rule.
Transfer Dissension of Shares;Property Rule;Surface Jurisprudence;Judicial Judgment
D922.291.91
A
1001-6201(2014)02-0009-06
[責任編輯:秦衛波]
2012-11-19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CFX068);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12YJA820068);中國博士后基金項目(2012M510720);西南政法大學資助項目。
汪青松(1974-),男,安徽懷遠人,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