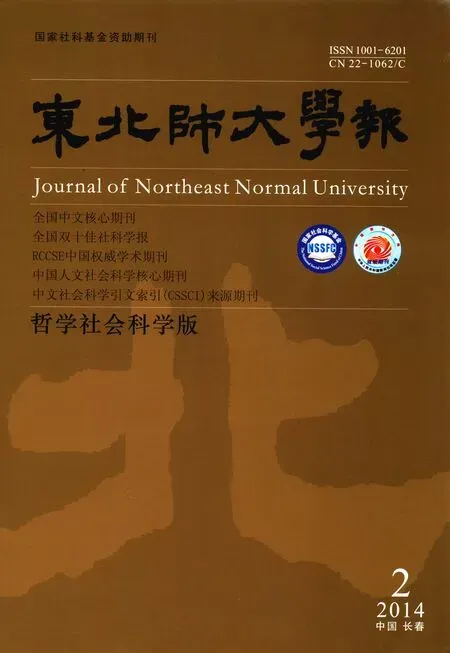兒童權利觀的合理意蘊及啟示
(東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學前教育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兒童權利觀是人們對兒童應享有的權利的根本看法和態度,是兒童觀的重要構成部分,是社會及各個構成群體對兒童作為自然人、社會人和文化人應享有的權利的認可,是對兒童個體存在和社會存在的整體態度,直接影響到兒童的健康快樂成長。兒童權利觀的科學認識始于18世紀盧梭提出的發現兒童,到198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以法律文件形式規定兒童享有多種權利,標志著兒童權利觀發展到新階段。然而在教育乃至社會領域,尚存在束縛和壓迫兒童,忽視兒童權利的現象,兒童的權利未得到充分認可和保障。因此“重新認識兒童、發現兒童、尊重兒童和解放兒童,把人的東西還給人,以人的方式教育人,是中國乃至人類教育最迫切需要進行的一場革命。”[1]
一、兒童權利觀的發展背景
兒童權利觀是在社會歷史的演進中,在社會經濟、文化、科學發展背景下,隨著人們對兒童認識的不斷進步而孕育、發展和完善的。古代社會人們對兒童的普遍認識是,兒童是小大人,是成人的附屬品,是家庭的私有財產,并未認識到兒童的特殊性,更未認識到兒童的權利。到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人們開始重新認識人存在的自身價值,肯定人的價值、地位、尊嚴,在對人的重新認識過程中,開始關注兒童存在的價值,這為兒童權利觀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在社會對人的價值認識的基礎上,西方自然權利理論得以產生,該理論強調人作為生命體所具有的自然權利,反對人們觀念中普遍形成的父權觀念和君權觀念,主張天賦人權,認為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可讓渡和剝奪。自然權利理論是對人權的倡導,為兒童權利的科學認識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社會關注人的價值、尊嚴與權利的背景下,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了自然主義教育思想,主張兒童具有自然稟賦和發展的自然過程,應尊重兒童的天性,尤其是他提出在人生中兒童期有兒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須把兒童當作兒童看待,這一思想標志著“兒童的發現”,標志著現代兒童觀的產生。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國家工業和經濟迅速發展,新的科學技術廣泛應用,人們對兒童的認識和態度日趨科學化。正如瑞典教育家愛倫·凱1899年在《兒童的世紀》一書中,提出20世紀將成為兒童的世紀這一期待,期待將兒童從傳統的誤解中解放出來,將兒童與成人區別開來,認識兒童的特殊性和童年價值。從這一時期開始,兒童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兒童教育的普及化和民主化把兒童從蒙昧狀態解放出來,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充分發展的機會。20世紀上半葉,在歐洲新教育運動思想的影響下,美國教育家杜威提出兒童中心論,強調以兒童為起點、為中心,并且以兒童的生長為教育的目的。意大利教育家蒙臺梭利則認為兒童具有與生俱來的內在潛力,成人不應干涉和限制兒童的自由發展,應為兒童提供有準備的環境,促進兒童的健康成長。“兒童的發現”和現代兒童觀的產生為人們理解和認可兒童權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社會對人的價值的認可、對人權的關注、對兒童的發現的基礎上,人們開始自覺、理性和科學地認識兒童的權利,形成認可和保障兒童權利的普遍意識。人們的兒童權利觀在一系列國際宣言和公約中更充分地得以體現:1924年國際聯盟通過了《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強調兒童與成人是平等的,擁有與成人一樣的權利與價值;1948年聯合國通過了旨在維護人類基本權利的《世界人權宣言》;1959年通過了明確各國兒童應當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的《兒童權利宣言》;1989年通過了第一部保障兒童權利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性約定《兒童權利公約》。這些國際宣言和公約體現了人們對兒童固有尊嚴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對自由、正義與和平的追求,對兒童生存權、發展權、受教育權和參與權等多種權利的重視。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兒童權利觀也會更為豐富和全面。因此,需要我們深刻地理解兒童應具有哪些權利,為什么具有這些權利等問題。
二、兒童權利觀的合理意蘊
兒童權利觀的合理意蘊包含兩個思考范疇:其一是如何理解兒童權利觀的本質規定性,即兒童權利的內核是什么;其二是兒童權利的合理性。基于兒童的屬性是自然的存在、社會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兒童權利的合理性要滿足合目的性、合規律性和合倫理性;合目的性是指合乎兒童發展的目的;合規律性是指合乎兒童發展的規律;合倫理性是指合乎兒童發展的社會倫理。可見兒童權利觀的理解涉及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多個領域。
(一)兒童權利觀的哲學意蘊
哲學視閾下的兒童權利觀是基于對兒童個體存在的價值和規律的理解,強調兒童具有主體發展、自由發展和豐富精神世界等權利。
首先,兒童作為一個生命體,具有主體價值,應享有自然生存權,包括生命權、存活權和獲得醫療、衛生保健的權利。兒童作為一個生命體,不僅具有不同于動物的生理結構,還具備了成為自然人的主體價值,即關注自身生命、存活等諸多主體性內容。一方面兒童具備自主發展的獨立性,能夠成為獨立的個體,具備人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兒童發展存在未確定性,“自然并沒有把人制造完整,便把人放在世界上了,自然沒有最終決定人,而是讓人在一定程度上尚未決定”[2],需要依賴周圍的環境提供各種資源和照顧。正如哲學家康德認為:“兒童有獲得父母細心撫養,直到他們有能力照顧自己為止。”[3]《兒童權利公約》同樣指出“每個兒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權”,應最大限度地確保兒童的存活與發展[4]。可見,在尊重兒童自然生命權的同時,必須保障兒童的存活權和獲得醫療衛生保健的權利,保障兒童獲得同父母親近和獲得照顧的權利,促進兒童作為生命體的健康成長。
其次,兒童具有自然發展的規律,具有自然天性,應享有自由選擇和自由游戲的權利。兒童是自然的存在,存在的合理性離不開自然發展規律,兒童的天性不可違背,“天性是人自身的自然,因而尊崇天性,就意味著看重人的身心發展自然規律,就意味著尊自然、去枷鎖、崇個性、尚自由。”[5]對于兒童來說,“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了這個秩序,我們就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實,它們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會腐爛:我們將造成一些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態龍鐘的兒童。”[6]順應兒童的天性,需要賦予兒童自由的權利,尤其是需要賦予兒童自由選擇和自由游戲的權利。正如《兒童權利公約》指出“確認兒童有權休息和閑暇,從事與兒童年齡相宜的游戲和娛樂活動,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和藝術活動”[4]。可見不應束縛和壓抑兒童,應讓兒童在發展過程中享有自由選擇和自由游戲的權利。
再次,兒童作為豐富精神生活的擁有者,有自由表達內心想法的權利和理性思考的權利。兒童具有思維能力、獨立人格和豐富的情感,兒童在發展過程中離不開豐富精神世界的支撐,其言語和行為多為其精神狀態的投射,兒童在發展過程中有需求也有個性。正是由于兒童具有這樣的發展需要和特點,應讓兒童敢于走出自己的內心世界,去思考、表達。兒童應當具有獲得信息的權利,自由不受干擾思考的權利,對自己和周圍的人或事發表言論的權利以及表達內心情感世界的權利。
(二)兒童權利觀的心理學意蘊
心理學視閾下的兒童權利觀主要從兒童發展、兒童需要角度詮釋了兒童期的重要價值以及兒童應有的發展、受保護等權利。
首先,兒童具有身心發展規律,兒童期具有獨特價值,應當享有受尊重和受照顧的權利。兒童從出生就有了各種條件反射,隨著對環境的適應逐漸用同化、順應、平衡來認識世界,進而適應內外環境,實現早期智慧的增長。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發展具有內在主動性和建構性特點,根據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將兒童的認知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直覺行動階段、前運算階段、具體運算階段和邏輯運算階段。并且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強調:“兒童期經驗更有重視的必要,因為它們發生于尚未完全發展的時候,更容易產生更大的結果。”[7]因而兒童有受尊重的權利,應尊重兒童認知發展規律、尊重早期經驗、尊重童年期不可替代的價值。
其次,兒童具有發展的潛能和需要,是發展的個體,且具有差異性,應享有發展的權利和受保護的權利。發展的權利主要表現為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和受特殊保護的權利。兒童在心理發展過程中有發展的潛能,例如腦科學研究表明,腦的發育存在最佳期,嬰幼兒時期是大腦發展最快的時期,腦的結構和功能的可塑性最大,即腦被環境和經驗修飾的可能性最大。因而兒童的發展潛能巨大,且這種潛能不同的兒童發展和完善的程度也不相同,因而呈現出個體差異。并且,兒童的發展是受興趣和需要影響的,“兒童是一個能動物,他的行動是受興趣和需要的規律所控制的”[8]。因此,兒童應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興趣和需要得到保護的權利和個體差異得到尊重的權利,尤其是特殊兒童應享有更多的保護和支持。
(三)兒童權利觀的社會學意蘊
社會學視閾下的兒童權利觀是基于兒童的社會性,強調兒童應享有的社會權利。兒童作為社會中的個體,其健康發展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群體,并在這個大環境中形成了不同于成人的兒童文化。兒童在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參與社會活動過程中,發展了自身能力,同時也需要社會從人類需要角度出發去保障兒童作為人的權利,讓兒童獲得獨立、平等參與社會活動、游戲等權利,確保兒童與社會和諧健康發展。
首先,兒童是發展中的社會人,具有全面發展、受保護和與成人平等的權利。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強調了人類與社會的相互作用關系,尤其重視社會對兒童的作用。兒童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展、完善自己,兒童需要在成為社會人的過程中獲得發展的條件和能力。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則從生態環境和兒童的互動關系角度提出了微小系統、中間系統、外部系統、宏大系統和動態變化系統5個不同層面的生態系統,充分闡釋了兒童是如何在社會中互動和發展的。在這個互動發展的過程中兒童作為重要的一員要得到和成人平等的權利,得到成人和社會保護的權利,這樣才能促進兒童全面發展,并與社會良好互動。
其次,兒童用自己的獨特方式參與社會活動,具有參與社會活動、游戲和閑暇的權利。由于兒童的身體、心理發展的特殊性,他們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不同于成人,參與社會活動的過程主要是有機會獲取信息,參與那些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決策,能夠用自己的言語或者行為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結合兒童的自身特點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參與活動方式,這種方式是多樣的和可實現的,不能用成人的參與方式來衡量兒童。尊重兒童特點,保障他們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游戲的權利,保證兒童有足夠的時間和閑暇來獲取信息、整理信息和傳達信息。
再次,兒童擁有自己的文化,具有質樸的特點,應當享有特殊保護和自由表達、表現的權利。兒童的文化不是簡單的復制和繼承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自己的想象、探索和好奇,兒童獨特的視角構成了自身文化的特點。“童年遠不是只有些許重要性的生物需求;它有史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成長階段而出現,而且變得日益重要”[9],兒童文化有其獨特的價值,這也就要求保護和傳揚兒童的文化,即根據兒童的發展和時代需要對兒童的這些文化財富進行保護。具體而言就是保護兒童探究探索的欲望,提供并支持兒童自由表達和表現,不要遏制兒童的奇思妙想和獨特的思維方式。
三、對兒童教育的啟示
兒童權利觀在不同視閾下意蘊豐富,合理的兒童權利觀強調兒童享有生存權、全面發展權、受教育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這些權利不應因兒童的出身、民族、性別等不同而有所差別。那么在教育領域如何踐行合理的兒童權利觀,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和學校的共同努力。
(一)立法保障兒童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法律具有全局性、權威性與強制性。從世界各國對兒童權利保障的經驗來看,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教育基本法、專門法、行政法規規章等構成的國家法律體系已成為普遍趨勢。例如美國1994年《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中提出讓所有兒童都能夠接受高質量的學前教育項目;2001年《不讓一個兒童落后法》中提出要確保所有兒童都擁有獲得高質量教育的公正、平等和重要的機會[10]。同時還專門制定了《防止虐待兒童和待遇法》、《殘疾兒童教育法》、《兒童網絡保護法》等法律,保障兒童的合法權利。我國1991年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1992年簽署《兒童權利公約》,積極推進兒童的權利保護。然而從現實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體罰虐待兒童、傷害兒童尊嚴、忽視兒童生命安全等損害兒童權利的現象。因此,應以我國《憲法》為依據,制定全方位保障兒童各項權利的國家法律體系,包括保障兒童生存權、全面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全面參與權等相關法律,還要包括保障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兒童受教育機會的教育權等相關法律。
(二)尊重兒童天性,促進兒童全面和諧發展
兒童的天性是兒童自身的自然,尊重兒童天性意味著尊重兒童發展的自然規律,尊重兒童的主體性,尊重兒童的內在發展潛能。然而現實中存在限制或違背兒童天性,過度開發兒童智力,剝奪兒童游戲、玩耍、閑暇時間的現象,因而兒童教育應尊重兒童的天性,尊重好奇、探索和創造的特點,賦予兒童自由、主動發展和游戲的權利。并且,兒童的生命是整體性生命,其身心發展具有系統性,表現為兒童的身體、智力、社會性和情感各方面整體發展,并且這些方面的發展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因此,兒童教育應尊重兒童天性,重視兒童的長遠發展和長遠利益,促進兒童全面和諧發展。
(三)合理認識兒童的發展潛能,提供有質量的教育
兒童具有發展的潛能,但是應合理認識兒童的發展潛能:一方面要承認兒童具有發展的潛能,正如教育家蒙臺梭利所強調的兒童潛能;另一方面要認識到兒童的潛能不是無限的,是以兒童現有水平為基礎的有限度的潛能,并且兒童潛能的發揮需要依賴外界環境的作用,尤其是依賴教育的作用。因而學校、家庭和社會應提供給兒童有質量的教育,這就要求堅持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以兒童的身心發展規律為依據,尊重兒童的個體差異,合理認識兒童的發展潛能,創造兒童全面和諧發展的有利條件。
(四)肯定兒童文化,珍視兒童期的獨特價值
兒童的生命是人的生命最先奏起的樂章,兒童具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在兒童的世界里,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天真爛漫。兒童正是以其獨特的精神生活和行為方式構建了獨特的兒童文化。兒童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瑰寶,需要得到社會的肯定。兒童文化存在于整個兒童期,賦予兒童期以獨特價值,而在現實中,“他們總想把兒童期縮短,將成人的知識經驗裝進去。他們認為兒童期是完全白費了的,哪里知道這是真正的教育基礎!”[11]因而肯定兒童文化,珍惜童年生活的獨特價值,為兒童提供充分、自由的表達機會,讓兒童擁有健康快樂的童年生活應是兒童教育的追求。
(五)關注兒童個體差異,重視弱勢兒童權利
兒童的發展具有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既體現為不同于成人的群體性差異,又表現為兒童群體內部的差異。兒童既與成人在身心發展水平、擔負的責任和義務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同時兒童之間因出身、經濟條件、民族等因素、身心發展水平的不同也存在著差異。因這些差異性衍生出來的兒童權利包括生存權、受保護權、與成人平等的社會參與權,還包括弱勢兒童的平等權利等。兒童的未來即是社會的未來,兒童教育應遵循兒童利益最大化和無歧視的原則,保障兒童的這些權利,尤其是要保障弱勢兒童的權利。例如美國“提前開端”(Head Start)和英國“確保開端”(Sure Start)計劃都是為經濟困難兒童提供免費公共教育服務的,而我國可以走“投資教育,增進人力資本,改變貧困現狀”的方式[12]。
總之,合理的兒童權利觀強調兒童作為自然、社會和文化的存在,具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等多種權利,兒童教育應踐行合理的兒童權利觀,保障兒童的合理權利,提升兒童的生命價值,使兒童的發展日臻完善。
[1]鄔志輝.教師教育理念的現代化及其轉化中介[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3):80-86.
[2]藍德曼.哲學人類學[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46.
[3]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98.
[4]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EB/OL].http://syzx.mca.gov.cn.
[5]劉曉東.論教育與天性[J].南京師大學報,2003(4):69-75.
[6]盧梭.愛彌兒[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91.
[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289.
[8]皮亞杰.教育科學與兒童心理發展[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155.
[9]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72.
[10]張憲冰.論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與政府責任[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188-191.
[11]杜威.教育哲學[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92.
[12]劉秀麗.城市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家庭投入研究[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18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