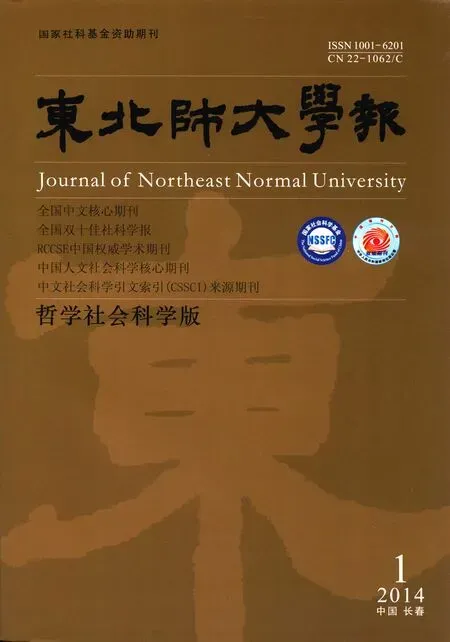格賴斯“自然意義”及其與“所言”的內在關系研究
仇云龍,張紹杰
(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格賴斯(H·P·Grice)是美國著名哲學家、語言學家,以其“非自然意義理論”和“會話含義理論”著稱。他于1957年在《哲學評論》(Pilosophical Review)雜志上發表了《意義》(“Meaning”)一文,將語言哲學范疇內的意義分為“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并著重論述了二者的區別,該文的發表標志著格氏“非自然意義理論”的形成。在1982年發表的《再論意義》(“Meaning Revisited”)一文中,格賴斯對“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的關系進行了重新定位,將二者的關系比作祖先(ancestor)和后裔(descendant),提出“非自然意義”可由“自然意義”派生而來的“祖先/后裔說”。格賴斯意義理論是其“會話含義理論”的基石。從目前的研究現狀看,學界對“非自然意義”的內涵認識較為明確,對“非自然意義”與“所含”概念之間的理論聯系較為關注;但對“自然意義”的內涵認識有些模糊,對“自然意義”與“所言”之間的內在關系重視不足,造成了含義分類理據性不強的后果[1]758。本文將基于格賴斯的意義和交際理論著重闡發“自然意義”的內涵及其與“所言”之間的內在關系。
一、格賴斯“自然意義”的內涵
要進一步澄清和詳解格賴斯意義理論前期中“自然意義”的內涵,我們應以格賴斯在“意義”一文中對“自然意義”核心特征的描述為依據。格賴斯用五條標準對“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進行了區分,具體如下[2]214:
(1)句子中 mean前面的成分是否蘊涵(entail)其后面的成分?如蘊涵,則該句子表達自然意義;
(2)句子中mean前后的成分是否可以分別嵌入“What is(was)meant by...is(was)...”結構中的空缺處?如可以,則該句子表達非自然意義;
(3)句子中mean前后的成分是否可以分別嵌入“Someone meant...by...”結構中的空缺處?如可以,則該句子表達非自然意義;
(4)句子中mean后面的成分是否可以嵌入引號中?如可以,則該句子表達非自然意義;
(5)句子中mean前后的成分是否可以分別嵌入“The fact that...means...”結構中的空缺處?如可以,則該句子表達自然意義。
在這五條標準中,蘊涵特征和事實性特征的區分性最強。有關蘊涵特征,格賴斯未進行詳解,但我們可以根據其提供的范例探出究竟。格賴斯認為“冒煙意味著著火”表示蘊涵關系,但“紅燈意味著交通停止”則不表示蘊涵關系。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不存在或然性,后者則存在或然性。這就說明,格賴斯在論述“自然意義”時所說的“蘊涵”指涉必然聯系。有關事實性特征,格賴斯一再強調其作為“自然意義”最核心特征的重要性,但并未明述自己所說的“事實”究竟意味著什么。按上文論述,“自然意義”體現必然性,因而,格賴斯所說的“事實”屬于塞爾所說的“非理性事實”[3]25。那么,“非理性事實”的載體又是什么呢?格賴斯認為,“自然意義”與自然符號密切相連(如“烏云意味著下雨”)[2]231。“與自然符號密切相連”意味著什么?是“自然意義”應與自然現象有關,還是自然現象生成的意義就是“自然意義”呢?此問題有必要詳解。“自然意義”是否應與自然現象有關呢?對自然現象的認知是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結果,憑直覺即可自動判斷,因而,自然現象具有成為“非理性事實”的潛勢;而那些體現“制度性事實”的非自然現象不生成“自然意義”①格賴斯給出的表示“自然意義”的個別范例也與自然現象無關,這表明他在“自然意義”內涵的厘定上仍留有余地,而這種立場正是“祖先/后裔說”提出的一個重要原因。。那是不是自然現象生成的意義就是“自然意義”呢?比如,“雷電是鬼神發怒”、“干旱是龍王生氣”等。有評論認為這些現象會生成“自然意義”[4]89,但本文并不認同。這些命題均與自然現象有關,屬于人類科技水平不高時的早先經驗,但卻與科學相悖,其前面的成分不蘊涵后面的成分,故而,它們不體現“非理性事實”,也就不具有“自然意義”。因而,由自然現象引發的,但不體現必然聯系的意義也不是“自然意義”。經過以上的澄清和詳解,我們可以發現,在格賴斯意義理論前期,“自然意義”表征必然聯系,體現“非理性事實”,與自然現象有關。
要明確格賴斯意義理論(后期)中“自然意義”的內涵,我們應以格賴斯在《再論意義》一文中對“祖先/后裔說”的闡述為依據。格賴斯“祖先/后裔說”的核心觀點即“非自然意義”由“自然意義”派生而來,他以表現“自然意義”的“某人X無意志地(nonvoluntarily)實施某種行為α意味著X疼”如何派生出“非自然意義”為例進行觀點闡釋[2]292-295:
(1)某人X有意志地(voluntarily)實施某種行為α;
(2)Y意識到(1);
(3)Y意識到X希望(2);
(4)Y猜測X希望(2)的動機并為該動機的實現做出努力;
(5)Y認為X的動機是讓自己相信X疼。
因為格賴斯意義理論(后期)中的“自然意義”概念是對前期“自然意義”概念的拓展和補充,所以要明確格賴斯意義理論(后期)中“自然意義”的內涵,仍以蘊涵特征和事實性特征為觀測點與上文進行對照詮釋較為妥帖。在闡述“祖先/后裔說”的過程中,“自然意義”概念的內涵發生了演化。格賴斯認為,“自然意義”不一定都與自然符號相關[2]295。那么,這部分不是由自然符號生成的“自然意義”是否也具有蘊涵特征呢?格賴斯對此類“自然意義”的性質進行了限定,并指出此類“自然意義”的生成具有兩個關鍵要素:一是行為與信息之間的聯系“可被感知”,二是人們認可行為與信息之間的聯系[2]295-296。什么意義可被感知又廣受認可呢?可被感知又廣受認可體現集體意向的達成,而表征集體意向的意義則是規約意義,因為“規約性(conventionality)是一種為事方式,這種為事方式建立在各方達成的協定或契約的基礎上”[5]79。規約意義體現真值意義上的語義關系,具有蘊涵特征。同時,“規約意義”已經約定俗成并被普遍接受為“事實”,只是這種后天約定的“事實”作為社會化的產物屬于“制度性事實”,而這種“制度性事實”的載體則廣泛涵蓋社會現象的林林總總。經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格賴斯意義理論后期,“自然意義”側重指規約意義,其涉及的事實主要是指“制度性事實”,其載體包羅諸種社會現象。
二、格賴斯“自然意義”與“所言”的內在關系
格賴斯“自然意義”與“所言”的內在關系可從兩個維度進行考察,一是“自然意義”概念與“所言”內涵之間有何關系,二是“自然意義”/“非自然意義”關系與“所言”/“所含”關系有何聯系。
考察“自然意義”概念與“所言”內涵之間的關系需要明確格賴斯會話含義理論中的“所言”究竟指什么以及它是如何確定的。在《邏輯與對話》(Logic and Conversation)一文中,格賴斯的兩處表述對“所言”內涵的確定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所言”與語詞的規約意義緊密相連;二是“所言”內容的確定除考慮字面意義外,還需明確指示成分、進行語義去歧[2]25。在《說話人意義與意圖》(Utterer's Meaning and Intention)一文中,格賴斯對“所言”進行了界定,即“說話人言p”是指:“說話人做某事x”(1)以此 U主要意味著p,(2)它屬于一個句子類型,而‘p’是該句子類型中的一個意思[2]88。以上表述說明,格賴斯認為“所言”的內容是確定的。那“所言”又是怎樣確定的呢?格賴斯的觀點不同于列文森所秉持的“所言”的確定依賴于“所含”[6]171-172的觀點。格賴斯認為,“所言”內容的確定是對規約意義進行選擇的過程,這種選擇需要參照上下文,但上下文的作用是對指示成分的確定和語義去歧進行限定。“所言”內容的確定依靠的是語句本身的規約意義而非“會話含義”產生過程中依靠的個體意向性。故而,“所言”內容的確定不依賴于“所含”,而“格賴斯循環”(Grice's Circle)因其對話語理解造成的阻礙以及難以化解的“雞”/“蛋”之爭亦不能成立[7]20。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格賴斯“會話含義理論”中的“所言”是一種真值條件內容,它是確定而唯一的;“所言”內容的確定依托上下文,但其表達的意思因其自身規約意義而生,不由“所含”建構而成。這與格賴斯“自然意義”中一以貫之的總體特征一脈相承:“自然意義”的“事實性”特征決定了它是一種“真值意義”,而這種“真值意義”是一種群體默認的穩定存在。“自然意義”概念與“所言”內涵的對應關系折射出格賴斯作為一名最簡論者(minimalist)所持有的基本立場,即“句子的語義內容即是句子全部話語共有的語義內容”,但也承認“語言中只存在少量的對語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的表達形式,需要在話語的語境中確定它們的語義價值”,只是“除了確定語境敏感表達形式的語義價值外,話語的語境對語義表達的命題沒有任何影響”[8]8。
考察“自然意義”/“非自然意義”關系與“所言”/“所含”關系之間有何聯系應從動態視角著眼,從格賴斯意義理論前、后期兩個階段著手。格賴斯對“所言”/“所含”關系的探述始于《邏輯與對話》一文,該文的關注焦點是“特殊會話含義”,文中指出:影響“特殊會話含義”推斷的主導因素是說話人意圖以及與其相關的語境,而影響“所言”內容的主導因素是其規約意義。故而,“所言”/“所含”關系不是一個鏈條上的連續體。這種“所言”/“所含”關系受格賴斯意義理論前期“自然意義”/“非自然意義”關系的影響。在其意義理論前期,格賴斯對“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區別的強調促成了“所言”、“所含”在疆域上的二分,“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的區別性特征導致了“所言”、“所含”的推導受不同因素制約。
格賴斯對“所言”/“所含”關系的探述又隱現于《再論意義》一文,其中的“祖先/后裔說”實質上就是在闡述一種新的“所言”/“所含”關系。上文提過,格賴斯意義理論后期的“自然意義”主要是指規約意義,而“非自然意義”是指非規約意義。“祖先/后裔說”旨在說明規約意義是非規約意義推斷的起點。具體地說就是:無論施動者的意圖是什么,意圖怎樣實施,聽話人怎樣識解,成功交際得以實現都依存于一種穩定不變的源頭。用格賴斯的比喻可以解釋為,后裔可以有很多,但祖先只能有一個;后裔不管有多少個體特征,但血統是不可變更的。這種主張實際上是在闡述一種新的“所言”/“所含”關系,即“所言”是“所含”推導基礎的語義優先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所言”又是怎樣推導“所含”的呢?《再論意義》中論述的“某人X無意志地(nonvoluntarily)實施某種行為α意味著X疼”由“自然意義”派生“非自然意義”的過程實際就是說話人遵循會話準則,通過理解真值條件內容的方式,衍生“標準含義”的過程[2]292-295;而格賴斯所說的與“自然意義”聯系較為松散的“非自然意義”的推導過程就是說話人違反會話準則,不同程度地偏離真值條件內容,衍生“非標準含義”的過程[2]296。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格賴斯意義理論的前、后期,“所言”/“所含”之間的關系呈現不同的特征。在其意義理論前期,“自然意義”、“非自然意義”的分野導致了“所言”、“所含”之間的清晰劃界;在其意義理論后期,“自然意義”、“非自然意義”的連貫一體使“所言”、“所含”構成意義連續體(continuum)。在其意義理論前期,格賴斯主要解釋了說話人意義在交際過程中如何被識解的問題,并未明確傳遞語義優先的思想;在其意義理論后期,格賴斯主要回答為什么說話人意義能被聽話人識解的問題,體現了語義優先的思想,說明“所言”是理解“所含”的基礎和源泉,鮮明反映出格賴斯在含義推導中重視語言規約性的語言哲學觀。
綜上所述,本文綜觀了格賴斯有關“自然意義”的論述,對格賴斯意義理論的前、后期進行了整體關照,并對“自然意義”的內涵進行了重新厘定;關注了“自然意義”概念與“所言”之間的關系,并從“自然意義”概念與“所言”內涵之間有何關系以及“自然意義”/“非自然意義”關系與“所言”/“所含”關系有何聯系兩個方面進行了闡釋。通過對格賴斯“自然意義”內涵的厘定及其與“所言”內在關系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結論:(1)格賴斯“自然意義”的內涵在其意義理論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指表征必然聯系的真值意義,后期指規約意義;(2)格賴斯“自然意義”的“事實性”特征決定了“所言”的確定性,格賴斯概念下“所言”內容的確定過程不依賴于“所含”;(3)格賴斯意義理論前期對“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區別的強調剝離了“所言”與“所含”,“所含”推導的主導因素不是“所言”,這說明語言規約性在格賴斯前期語言哲學思想中并未得到足夠重視,因而受到塞爾等人的質疑[9]79;格賴斯“祖先/后裔說”的提出連接了“所言”與“所含”,“所言”被推至“所含”推導源泉的高度,這說明語言規約性在格賴斯后期語言哲學思想中地位得到彰顯,承繼了亞里士多德以降多位語言規約論者一以貫之的思想[10]75-76,這些發現將為意義不確定性等問題的討論[11]108-111提供新的視角。
[1]Yunlong Qiu,Jinou Li.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Implicature Classif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A].Lisa Thomas,Jin Zhang,Fang Qi.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C].Georgia:American Scholars Press,2012.
[2]Herbert P.Grice.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塞爾.社會實在的建構[M].李步樓,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段維軍,張紹杰.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之哲辨[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
[5]Louise Cummings.The Pragmatics Encyclopedia[M].Abingdon:Routledge,2010.
[6]Steven C.Levinson.Presumptive Meanings: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M].Cambridge:MIT Press,2000.
[7]唐瑞梁.列文森一般性會話含義理論中的缺陷 [J].外語教學,2008(2).
[8]張紹杰等.后格賴斯語用學研究 [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9]Siobhan Chapman.Paul Grice,Philosopher and Linguist[M].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5.
[10]張紹杰.語法和語用:基于語言使用的互動視角 [J].外語學刊,2010(5).
[11]于林龍.隱喻思維與意義的不確定性[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