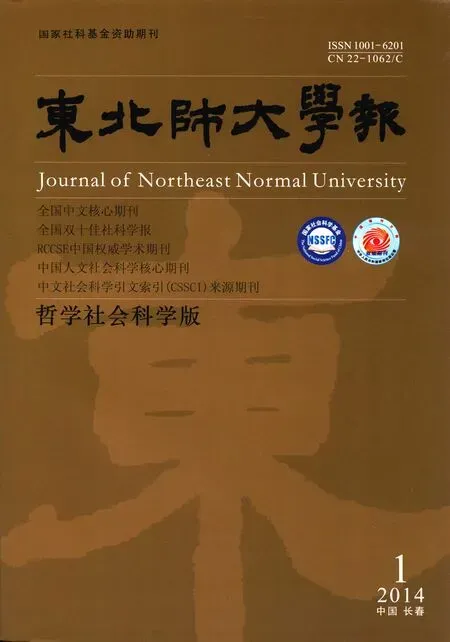新課程下教師課程決策的變革
李水霞,熊 梅
(1.東北師范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部,吉林 長(zhǎng)春 130024;2.天津師范大學(xué) 初等教育學(xué)院,天津 300071)
新課程改革提出:“要改變課程實(shí)施過于強(qiáng)調(diào)接受學(xué)習(xí)、死記硬背、機(jī)械訓(xùn)練的現(xiàn)狀,倡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dòng)手,培養(yǎng)學(xué)生搜集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shí)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1]新課程理念的踐行無疑需要教師角色的相應(yīng)轉(zhuǎn)變。在課程實(shí)施的過程中,教師不是一個(gè)被動(dòng)的執(zhí)行者而是一個(gè)主動(dòng)的決策者。因此,審視當(dāng)前新課程改革下教師課程決策存在的主要問題,實(shí)現(xiàn)教師課程決策的變革對(duì)于我們踐行新課程教學(xué)理念,提升教育教學(xué)質(zhì)量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課程下教師課程決策的內(nèi)涵
“課程決策”是人們對(duì)有關(guān)課程問題所做的判斷和選擇。課程設(shè)計(jì)與實(shí)施的復(fù)雜性決定了在課程發(fā)展的不同水平和階段都伴隨著不同的人所做出的決策。因此,在課程發(fā)展的不同水平和階段都伴隨著不同的人所做出的決策[2]44。國(guó)外學(xué)者Obger認(rèn)為,課程決策是對(duì)有關(guān)教育或社會(huì)化的目的和手段的一種判斷,往往在學(xué)校范圍內(nèi)采用,并且以教學(xué)大綱為中心(而不是人事、預(yù)算等)。判斷是一種有意識(shí)思考的結(jié)果,代表了以一種特殊形式去行動(dòng)或產(chǎn)生一個(gè)預(yù)期結(jié)果的意向[3]。也有學(xué)者將課程決策分為三層次說和四層次說,課程決策可以在以下幾個(gè)層次進(jìn)行:分別是課堂教學(xué)層次的決策,教學(xué)機(jī)構(gòu)的決策以及社會(huì)層次的決策、個(gè)人層次的決策[2]44。從課程基本要素的角度來分析,課程決策涉及課程目標(biāo)的決策、課程內(nèi)容的決策、學(xué)習(xí)經(jīng)驗(yàn)和教學(xué)策略的決策、課程媒介或資料的決策以及課程評(píng)價(jià)的決策等幾個(gè)方面。
教師課程決策是課程決策的下位概念。馬云鵬教授認(rèn)為在課程實(shí)施過程中,教師應(yīng)是一個(gè)主動(dòng)的決策者,教師需要對(duì)隨時(shí)可能出現(xiàn)的課程問題作出專業(yè)的課程判斷,這種專業(yè)判斷就形成了教師課程實(shí)施過程中的決策[2]44。也有研究者認(rèn)為教師的課程決策主要發(fā)生在課堂層面,是教師在對(duì)課程文件、課程標(biāo)準(zhǔn)和教科書等進(jìn)行理解的基礎(chǔ)上為更好地實(shí)施教學(xué)而進(jìn)行的課程調(diào)適。教師的課程決策貫穿于課程實(shí)施的整個(gè)過程[4]。也有學(xué)者指出教師在教學(xué)計(jì)劃階段和課堂教學(xué)階段都要面對(duì)以下五方面的問題,即有關(guān)學(xué)習(xí)和行為目的或目標(biāo)、現(xiàn)有的狀態(tài)、可選擇的教學(xué)行為、學(xué)生要達(dá)到的結(jié)果、教師對(duì)這些結(jié)果的應(yīng)用。綜合各位學(xué)者的觀點(diǎn),我們可以把教師課程決策理解為教師在課程教學(xué)的各個(gè)階段針對(duì)教學(xué)情境中的具體問題在眾多可能性選擇中作出的選擇和判斷。而教師的這種選擇和判斷直接決定了新課程實(shí)施的實(shí)效性。
二、新課程下教師課程決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任何一種理念的課程以及按照這種理念編制的課程,最終都要依靠教師在具體的課堂層面上的實(shí)施,在實(shí)施中必然要伴隨教師作出的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決策。因此,關(guān)注在課程實(shí)施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教師在課程決策中究竟存在哪些問題尤為重要。
(一)課程決策的經(jīng)驗(yàn)取向
審視新課程實(shí)施以來,教師在課堂中的決策經(jīng)常存在著低效甚至無效的經(jīng)驗(yàn)主義決策。經(jīng)驗(yàn)主義的課程決策不是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否定,而是由于經(jīng)驗(yàn)的僵化、“繭化”導(dǎo)致原本有意義的經(jīng)驗(yàn)質(zhì)變?yōu)榻處煕Q策的制約和阻礙因素,使得教師決策呈現(xiàn)出經(jīng)驗(yàn)主義的現(xiàn)實(shí)形態(tài)[5]。從一般意義上說,當(dāng)教師的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不能適應(yīng)新的教學(xué)情境,脫離了具體的實(shí)踐或者教師僅僅拘泥在過去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中,不能正視新課程理念下不斷變化的教學(xué)變革時(shí),經(jīng)驗(yàn)就失去了它在教師的成長(zhǎng)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教師的經(jīng)驗(yàn)主義取向經(jīng)常表現(xiàn)為如下現(xiàn)象:教師對(duì)決策經(jīng)驗(yàn)的“抱殘守缺”;教師對(duì)零散累積或借鑒的經(jīng)驗(yàn)缺乏本質(zhì)上的分析和概括,沒有對(duì)教師所積累經(jīng)驗(yàn)的應(yīng)用情境、課程內(nèi)容等因素進(jìn)行充分了解和判斷,盲目因循慣例與規(guī)則。
(二)唯知識(shí)傳遞為主的取向
理智教學(xué)思想源于捷克的大教育家夸美紐斯,到赫爾巴特那里逐步發(fā)展為主知主義教學(xué)理論。他們都主張教學(xué)要通過教師主導(dǎo)的、對(duì)教材知識(shí)的傳授發(fā)展學(xué)生的智力。夸美紐斯的課堂教學(xué)決策的落點(diǎn)在于提供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教材,他指出“我的計(jì)劃的成功,完全系于一種百科全書式的腳本的適當(dāng)供應(yīng),這種教本只能由幾位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精神飽滿的學(xué)者合作才能得到。”[6]赫爾巴特的教學(xué)決策立足于教學(xué)內(nèi)容的提供和傳遞上,他說:“教師不是盧梭所說的那樣是自然之助手,而是兒童觀念的提供者,多方面興趣的控制者。”[7]顯然,這種以“知識(shí)傳遞,知識(shí)技能的掌握”作為決策取向的觀點(diǎn),深入地影響著處在新課程理念下的教師決策——以“教”為中心。已有研究發(fā)現(xiàn),教師在84%的課堂中都扮演了主角。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綱要提出:“改變課程過于注重知識(shí)傳授的傾向,強(qiáng)調(diào)形成積極主動(dòng)的學(xué)習(xí)態(tài)度,使獲得基礎(chǔ)知識(shí)與基本技能的過程同時(shí)成為學(xué)會(huì)學(xué)習(xí)和形成正確價(jià)值觀的過程。”然而教師在面對(duì)新課程出現(xiàn)的決策過程中普遍重知識(shí)傳遞,輕情感態(tài)度價(jià)值觀。在學(xué)校教育還沒有真正實(shí)現(xiàn)從應(yīng)試教育到素質(zhì)教育轉(zhuǎn)換的今天,很多教師“依然把教材視為基礎(chǔ)知識(shí)和基本技能的唯一載體,把討論的、活動(dòng)的或探究的內(nèi)容改造成結(jié)論性知識(shí),而后灌輸給學(xué)生去掌握。這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吞噬教材的發(fā)展功能以及方法的、激活思維的乃至策動(dòng)創(chuàng)造精神的功能。”[8]新課程三維目標(biāo)的提出是為了克服當(dāng)前教育對(duì)知識(shí)目標(biāo)的片面追求,但是教師對(duì)知識(shí)能力目標(biāo)的偏重導(dǎo)致很多教師對(duì)“情感、態(tài)度、價(jià)值觀究竟讓學(xué)生獲得怎么樣的發(fā)展并不十分清楚。”[9]
(三)傳統(tǒng)教學(xué)思維方式影響
教學(xué)思維方式是人們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釋教學(xué)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組合方式和運(yùn)作方式[10]。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主要是以“給予型”為主,“給予型”的教學(xué)思維方式主要以學(xué)科為中心,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學(xué)科知識(shí)的掌握,視知識(shí)為絕對(duì)真理,推行學(xué)術(shù)精英主義,教師被視為學(xué)科專才,單向傳授式教學(xué),向?qū)W生提出的問題有已知的答案,課堂教學(xué)的決策權(quán)主要集中在教師手中。具有傳統(tǒng)“給予型”思維方式的教師在決策過程中主要表現(xiàn)出拼湊性、極端線性、迫降性和隨意性的傾向。思維方式的拼湊性主要體現(xiàn)在教師對(duì)教材提供的信息進(jìn)行轉(zhuǎn)化時(shí)是采取簡(jiǎn)單加減法的方式拼湊和堆積起來;思維方式的極端線性化主要是指教師在課前計(jì)劃階段對(duì)教材進(jìn)行選擇和抉擇的過程中,習(xí)慣性地按照教材對(duì)內(nèi)容的線性羅列信息的思維方式;迫降性是針對(duì)學(xué)生的思維性而言的,指處在思維高處的學(xué)生由于教師的某個(gè)交互決策而急速下滑到某個(gè)思維低處的感覺和狀況;隨意性是不假思索地進(jìn)行決策,對(duì)事件的判斷缺乏因果聯(lián)系,是對(duì)當(dāng)即發(fā)生事件的簡(jiǎn)單應(yīng)付[11]。
新課程改革倡導(dǎo)學(xué)校教育改變課程實(shí)施過于強(qiáng)調(diào)接受學(xué)習(xí)、死記硬背、機(jī)械訓(xùn)練的現(xiàn)狀,倡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dòng)手,培養(yǎng)學(xué)生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shí)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
然而具有傳統(tǒng)的教學(xué)思維方式的教師在進(jìn)行課程決策的過程中與新課程改革“以學(xué)生發(fā)展為本”的理念“背道而馳”。究其根本,具有傳統(tǒng)教學(xué)思維方式的教師,在課程決策過程中的弊端和問題,主要妨礙了學(xué)生學(xué)習(xí)知識(shí)的興趣性,弱化了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主體性”,阻滯了學(xué)生思維的發(fā)展,對(duì)學(xué)生能力的全面培養(yǎng)有一定負(fù)面效應(yīng)。其弊端和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無視學(xué)生的主體性,把知識(shí)直接灌輸給學(xué)生,延續(xù)傳統(tǒng)的教學(xué)狀態(tài)。忽視學(xué)生學(xué)習(xí)需要教師幫助的特點(diǎn),決策出的教學(xué)方案在上課前就埋下許多阻礙學(xué)生更好地學(xué)習(xí)和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隱患,不利于學(xué)生正確有效地理解知識(shí)[12]。
(四)教師決策的依賴
從人員參與角度來看,課程決策可以是一群人的決策,也可以是一個(gè)人的決策。新課程實(shí)施以來,教師決策的依賴主要體現(xiàn)為教師的集體決策依賴和教科書依賴。集體課程決策依賴主要體現(xiàn)在教師集體備課中[13]。新課程實(shí)施以來,很多學(xué)校為了充分整合本校的教師資源,出現(xiàn)了“集體備課”的形式,要求教師上課的“標(biāo)準(zhǔn)”統(tǒng)一化。教師集體備課的初衷雖好,但是教師在備課中的“應(yīng)付”現(xiàn)象卻屢屢存在。如:為了達(dá)到“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所寫教案與實(shí)際情形脫節(jié),或者利用其他備課組成員集體形成的“教案”直接進(jìn)入課堂授課,使得“集體決策”失去了本應(yīng)有的教師不同決策風(fēng)格的互補(bǔ),影響了新課程的實(shí)施。與此同時(shí),許多教師出現(xiàn)了教科書依賴的惰性決策心態(tài),大部分教師還是沿襲著原有對(duì)教材的應(yīng)用模式,把教材作為唯一需要決策的內(nèi)容。教師僅僅關(guān)心的是如何把教材的結(jié)論告訴學(xué)生,認(rèn)為沒有必要開發(fā)其他的課程資源,更沒必要太在乎來自學(xué)生的“奇思妙想”。
三、教師課程決策的變革走向
新課程改革已經(jīng)走過數(shù)十年的歷程,面對(duì)新課程實(shí)施效果的種種爭(zhēng)議,我們必須正視教師在新課程下課程決策中所遇到的問題,探尋出優(yōu)化教師課程決策的路徑。有研究表明,對(duì)教師課程決策產(chǎn)生影響的因素來自不同的方面。綜合以往研究成果,在教學(xué)層面影響教師課程決策的因素主要有教師的知識(shí)、信念、學(xué)生的情況、學(xué)校文化、家長(zhǎng)與社會(huì)等因素。因此,筆者結(jié)合當(dāng)前教師課程決策存在的問題對(duì)變革教師課程決策的走向做以下思考。
(一)加強(qiáng)課程政策的保障
政策是權(quán)威部門通過一定的權(quán)威(如領(lǐng)導(dǎo)權(quán)威或社會(huì)權(quán)威)方式制定的,因此具有一定的指導(dǎo)力、影響力和保障力。教師要走出課程決策的經(jīng)驗(yàn)取向必須充分發(fā)揮教師決策的主體性。實(shí)現(xiàn)教師決策的主體性回歸,必須在教學(xué)設(shè)計(jì)、實(shí)施以及反饋與評(píng)價(jià)的諸多環(huán)節(jié),重新對(duì)教師決策的主體地位加以確認(rèn)。1994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教師法》中明確規(guī)定教師享有“進(jìn)行教育教學(xué)活動(dòng),開展教育教學(xué)改革和實(shí)驗(yàn)”等權(quán)利。教師的課程決策是教師自主進(jìn)行教育教學(xué)活動(dòng)的體現(xiàn)。我們必須通過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外在的法律和制度賦予教師決策的主體地位。例如我們應(yīng)規(guī)定教師在課程決策中的權(quán)力,明確規(guī)定在課堂教學(xué)的各個(gè)方面的具體課程決策權(quán)限范圍,使得教師的決策權(quán)力不受侵犯。當(dāng)社會(huì)賦予教師在教學(xué)中擁有對(duì)課程決策的權(quán)力,決定“教什么,怎么教”時(shí),教師課程決策的主體地位便獲得了外在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二)變革教師傳統(tǒng)的課程觀
新課程實(shí)施雖有數(shù)十年之久,但是很多教師仍然把以“知識(shí)傳遞,知識(shí)技能的掌握”作為決策的取向。持這種取向的教師僅僅把課程實(shí)施理解為忠實(shí)地執(zhí)行課程方案的過程。教師必須積極變革傳統(tǒng)的課程觀,給課程實(shí)施賦予“生命力”,把課程實(shí)施看作是師生在具體情境中聯(lián)合締造新的教育經(jīng)驗(yàn)的過程。在締造的過程中,已經(jīng)設(shè)計(jì)好的課程僅僅是教師和學(xué)生進(jìn)行或?qū)崿F(xiàn)“再造”的材料或背景,是一種課程資源[14]。教師的作用,師生的關(guān)系都呈現(xiàn)出新的特點(diǎn)。師生不再是單向的“授受”關(guān)系,教師與學(xué)生成為合作者、互助者,課堂教學(xué)的過程是一種動(dòng)態(tài)生成的過程。教師課程觀念的變革將有助于教師教學(xué)思維方式的轉(zhuǎn)向,從傳統(tǒng)的“給予型”思維方式走向生成型思維方式,走出僅僅以“教材為中心”,“以知識(shí)傳授為中心”的模式,從而更加關(guān)注學(xué)生,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生與教師決策的共享。
(三)提升教師的課程決策能力
僅僅依靠外在對(duì)教師決策權(quán)力的保障并不能保障教師決策主體性的充分發(fā)揮。教師決策能力的提升不僅需要賦權(quán)而且需要增能。增能將有利于教師能夠根據(jù)具體的教學(xué)情境靈活決策,從而使得決策“依賴”的程度減小。利斯伍德指出,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是一個(gè)多維度發(fā)展的過程,教師的專業(yè)智能發(fā)展大體經(jīng)歷三個(gè)周期:一是首先獲得教學(xué)的基本技能;二是拓展其靈活性,能根據(jù)教學(xué)目標(biāo)、學(xué)生具體需要和教學(xué)情境適時(shí)、靈活地應(yīng)用這些教學(xué)基本技能;三是逐漸擺脫教學(xué)常規(guī)的羈絆,其專業(yè)活動(dòng)范圍超出其所在課堂、學(xué)校參與教育決策。培養(yǎng)教師的決策能力和意識(shí)理應(yīng)成為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一方面,從教師自身來,要不斷加強(qiáng)總結(jié)和反思課程決策的經(jīng)驗(yàn),同時(shí),也要充分借鑒他人的課程決策經(jīng)驗(yàn),實(shí)現(xiàn)“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四、創(chuàng)造課程決策的文化,實(shí)現(xiàn)學(xué)校文化的更新
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duì)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dòng),包括知識(shí)內(nèi)容的傳授、生命內(nèi)涵的領(lǐng)悟、意志行為的規(guī)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chǎn)留給年青一代……并啟迪其自由天性。”在教師進(jìn)行課程決策的過程中,表面上看是教師的個(gè)人行為,但實(shí)際上教師在課堂教學(xué)中所作的決策受其環(huán)境和周圍群體文化特征的影響很大。正如有研究者認(rèn)為開放與合作為規(guī)范的學(xué)校文化,能夠促進(jìn)學(xué)校課程變革[15]。學(xué)校文化可以對(duì)教師的各個(gè)方面產(chǎn)生影響,包括教師對(duì)課程的認(rèn)識(shí)、理解和決策。有研究表明,學(xué)校內(nèi)教師之間密切的合作關(guān)系,對(duì)教學(xué)活動(dòng)有極大的促進(jìn)作用,有利于學(xué)生的培養(yǎng)。因此,我們必須在學(xué)校中創(chuàng)造一種合作交流的文化,實(shí)現(xiàn)學(xué)校文化的更新。讓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專家、教師和學(xué)生家長(zhǎng)都能夠具有合作的意識(shí)和能力,讓教師在合作交流的氛圍中踐行課程決策。
五、構(gòu)建課程決策的支持系統(tǒng)
任何課程設(shè)計(jì),最終都要通過具體的教學(xué)工作才能得以完成。塞勒等人認(rèn)為教師作為決策者在準(zhǔn)備教案時(shí)要經(jīng)歷以下步驟,當(dāng)教師對(duì)新課程計(jì)劃進(jìn)行選擇時(shí),要經(jīng)過四個(gè)篩子的篩選,分別為當(dāng)?shù)厣鐓^(qū)的價(jià)值觀和期望,學(xué)生的需要,當(dāng)?shù)亟逃h(huán)境的影響——班級(jí)組織、教材、管理人員的支持或限制,教師最終對(duì)合適方案的抉擇。因此,為了優(yōu)化教師的課程決策,我們必須構(gòu)筑課程決策的支持系統(tǒng)。一方面,我們要提供相應(yīng)的物質(zhì)支持,比如說給教師提供多樣化的教材資源,創(chuàng)造豐富的課程資源來提高教師的課程決策成效。另一方面,我們要要加強(qiáng)相關(guān)管理人員的支持,鼓勵(lì)教師主動(dòng)地進(jìn)行課程決策,增強(qiáng)教師進(jìn)行課程決策的動(dòng)機(jī)。同時(shí)我們還可以取得多方群體的支持,充分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家長(zhǎng)的積極性,讓教師的課程決策在合作與溝通中提高成效。
[1]教育部.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S].2001-06-08.
[2]馬云鵬.課程實(shí)施探索——小學(xué)數(shù)學(xué)課程實(shí)施的個(gè)案研究[M].長(zhǎng)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1.
[3]Ober.A.A.Curriculumdecision..InT.Husan&T.N.Postlethwaite(ed.).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5:1154-1159.
[4]楊明泉.革新的課程實(shí)踐者[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132.
[5]張朝珍.教師教學(xué)決策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xué),2009:57.
[6]夸美紐斯.大教學(xué)論[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1999:238.
[7]張華.課程與教學(xué)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48.
[8]楊啟亮.教材的功能:一種超越知識(shí)觀的解釋[J].課程·教材·教法,2002(12):10-13.
[9]劉家訪.上課的變革[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7:60.
[10]李定仁,羅儒國(guó).教學(xué)理論應(yīng)用思維方式的變革[J].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5(5):124.
[11]楊豫暉,宋乃慶.教師教學(xué)決策的主要問題及其思考[J].教育研究,2010(9):368.
[12]鄧友超.重視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中教師思維失衡問題[J].教育發(fā)展研究,2006:22-26.
[13]陳蓉輝,馬云鵬.幼兒園教師課程決策的特征及保障機(jī)制[J].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3):185-188.
[14]汪霞.課程實(shí)施:一個(gè)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J].教育科學(xué)研究,2003(3):7.
[15]李洪修.學(xué)校課程改革的沖突與化解路徑[J].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1):17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