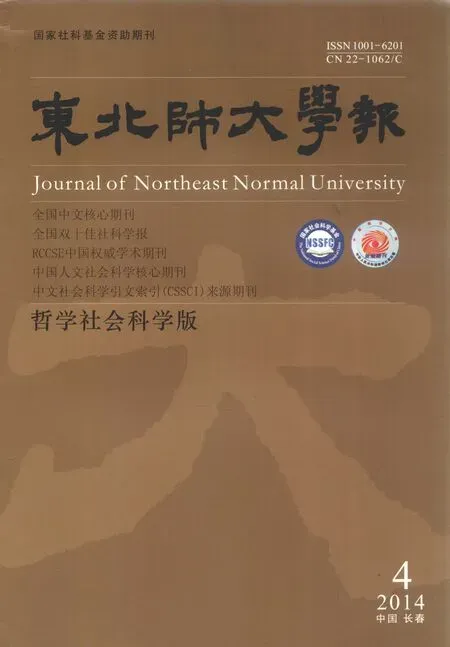全球化語境與歐美文學(xué)中國化進(jìn)程
周桂君
(東北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全球化”在人類信息技術(shù)和交通現(xiàn)代化的今天已經(jīng)深入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浸透到我們的經(jīng)濟(jì)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在21世紀(jì)的今天,全球化對文化領(lǐng)域的影響已經(jīng)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實。文化只有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才真正成為了“處在總體聯(lián)系中的動態(tài)有機(jī)體。”[1]
新時期,我們打開國門,主動擁抱經(jīng)濟(jì)文化的全球化。這個時期,從文化角度來講,全球化進(jìn)程給中國社會注入了許多新元素,引領(lǐng)諸多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一系列新變化,包括本文所涉及的歐美文學(xué)領(lǐng)域。
新時期初期,歐美文學(xué)在中國的譯介出現(xiàn)了十分火爆的現(xiàn)象。歐美文學(xué)作品的這種譯介熱和研究熱普遍被看成是中國政治領(lǐng)域巨變的附帶結(jié)果,這誠然是事實,但是,我們也應(yīng)意識到,這種熱潮更是全球化的必然結(jié)果。信息時代,發(fā)達(dá)的科學(xué)技術(shù)成為全球文化交流的催化劑。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變得輕而易舉,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使我們可以及時地了解地球任何一個地方的情況。就文學(xué)研究方面來講,互聯(lián)網(wǎng)在歐美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也使歐美文學(xué)的譯介和研究方式發(fā)生變革。首先,全球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加速了歐美文學(xué)作品翻譯的速度,改善了翻譯的格局。此外,對歐美文學(xué)的傳播手段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zhuǎn)變。再者,歐美文學(xué)的研究資源在大范圍內(nèi)實現(xiàn)了全球共享。
一、全球化使歐美文學(xué)研究走向動態(tài)化
我們可以即時接觸歐美文學(xué)新作,并且跟蹤歐美文學(xué)研究的動向,這種情形使我們可以研究文本在其原生地的狀況以及被譯介之后的狀況。這些信息的介入,不僅為歐美文學(xué)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資料,而且,還推進(jìn)了某些研究方式的改進(jìn)和發(fā)展。“文本旅行”研究就是在全球化時代興盛起來的一種有效的研究思潮。“文本旅行”一詞不僅形象地描述了文本的流轉(zhuǎn)過程,它還為文本流轉(zhuǎn)中的經(jīng)歷做了某種暗示。人的旅行使人接觸到許多新鮮的事物,“旅行”必然要遭遇新環(huán)境,跨越時間和空間,自身所攜帶的文化與旅游地的文化產(chǎn)生碰撞,旅行改變和塑造了旅行者。文本在其流轉(zhuǎn)過程中的遭遇與人的旅行是很相似的,它也要跨越時空,也要在新的地方停留,接受那里的文化環(huán)境的洗禮,最后讓自己融入新的環(huán)境中。
薩義德在出版于1983年的《世界、文本和批評家》一書中,論及到理論旅行問題。薩義德的“理論旅行”給予歐美文學(xué)研究中的文本旅行研究以啟發(fā)。“理論旅行”強(qiáng)調(diào)對理論進(jìn)行動態(tài)描述、追蹤其傳播和演化過程。薩義德把理論的傳播比喻成動物和人的遷徙。薩義德指出,理論傳播經(jīng)歷四個階段:理論在某處孕育,這是起點階段;在各種外力作用下,理論開始了時間和空間的跨越,去尋找新的棲息地;新的環(huán)境對于這種舶來的理論或者吸收或者抵制;那些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理論最后留存下來,不過已經(jīng)變異,融入了新的環(huán)境中。文本旅行變異的情形與文學(xué)理論旅行的變異情形很相似。
在全球化的今天研究文本的旅行才是可行的,只要看看研究文本旅行的條件就可以明確地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研究文本旅行和研究文本本身最大的不同是文本旅行研究具有很強(qiáng)的動態(tài)性。也就是說,我們只有把握住動態(tài)的信息才可能研究好文本旅行的問題。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這種要求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xiàn),這是文本旅行研究的必要前提。
此外,文本旅行研究涉及異質(zhì)文化問題,只有充分理解文化全球化的內(nèi)涵與意義,我們才可以真正做好文本旅行研究。文化全球化會引起文化焦慮,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們之所以焦慮,主要是因為,在文化全球化面前,大到一個民族,小到一個具體的人,都會產(chǎn)生一種迷失的感覺,一種認(rèn)同的危機(jī)。我們已有的文化之根使我們感到安全,因為,我們原有的這種文化給我們的存在定了位,并賦予我們的存在一種意義,但是全球化打亂了這一切,它把我們重新拋到一個新的環(huán)境中。在這個環(huán)境中,我們原有的文化與外來的文化在交接,在碰撞,在相互吸收或相互排斥,這是一個復(fù)雜的情形,一個讓我們感到無所適從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焦慮是不可避免的。消解焦慮的最佳提案就是用多元化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接受文化的多重性,容忍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的多樣性。
文本旅行的研究效果依賴于全球化的程度。全球化的程度越高,文本旅行的研究就會越容易深入下去。原因之一,文本旅行的研究把重點放在文本本身的變異上。文本的變異與讀者反映有直接的關(guān)系,還與文本所在地區(qū)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民族文化心理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文本研究要求繪出文本移居地的意識形態(tài)圖譜,圖譜中應(yīng)該包括移居地人民的心理狀態(tài)、思維方式、哲學(xué)思潮等,并在此基礎(chǔ)上考察文本在旅行中的變異。原因之二,全球化時代,我們與歐美文學(xué)直接接觸的機(jī)會越來越多。各種國際性研討會議在國內(nèi)外召開,研究人員國外考察項目、國家留學(xué)基金委項目的啟動使歐美文學(xué)研究者更直接地感受歐美文學(xué)成為可能。具有歐美文化體驗、掌握外語的研究人才的大量涌現(xiàn)為文本旅行的研究提供了人力條件。原因之三,新時期的中國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歐美文學(xué)研究獲得了充分的發(fā)展空間。有關(guān)“文本旅行”的研究所必然觸及的一些敏感話題不再讓研究者望而卻步。
二、全球化將歐美文學(xué)研究引入文化大視野
全球化將歐美文學(xué)研究引入文化大視野,帶動了比較文學(xué)的發(fā)展。全球化為世界各國文化的沖突和融合帶來了契機(jī)。全球化促進(jìn)了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往和文化共享以及異質(zhì)文化的交鋒。文化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共通性必然使人類的文化內(nèi)容表現(xiàn)出共性。而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不同的國家處在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上。全球化還把那些與我們社會制度相同國家的文化和不同國家的文化同時帶到我們面前。面對全球化的這種趨勢,歐美文學(xué)研究不由自主轉(zhuǎn)向文化研究。2006年6月在南京大學(xué)召開了“當(dāng)代英語國家文學(xué)研究的文化視角學(xué)術(shù)研討會”。會上探討了文學(xué)與政治、宗教、哲學(xué)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和影響,與會代表還探索了如何將東方文化視角融入外國文學(xué)研究中的問題。這些新思想、新思維的出現(xiàn)是與全球化的背景分不開的。正是全球化極大地調(diào)動了我們的比較意識和鑒別意識,我們是在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的世界性氛圍中生存的,我們的歐美文學(xué)研究也浸透著這樣的文化質(zhì)素。
此外,全球化帶來的焦慮感使研究者傾向于從比較文學(xué)的角度思考問題。全球化達(dá)到相當(dāng)?shù)某潭葧r,我們體驗到的便是文化的多元化、雜交化。新鮮事物層出不窮。比如,電子技術(shù)的發(fā)展日新月異,計算機(jī)更新,通信技術(shù)換代,新型家電不斷出現(xiàn)。這一切,都迫使人們不斷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變化是沒有止境的。被新事物新思想充斥的生活自然有它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人在變幻的生存環(huán)境中,必須不斷地調(diào)節(jié)自己,以適應(yīng)變化了的環(huán)境。人在調(diào)節(jié)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困難,而焦慮也便應(yīng)運而生。在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文學(xué)中,這種焦慮的意識是屢見不鮮的。詹姆遜在談到焦慮時指出,無論是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的《叫喊》,還是英國作家艾略特的《荒原》,無不表現(xiàn)出一種焦慮的特征。這種焦慮反映出現(xiàn)代主義文藝家對現(xiàn)實生活痛苦的一種體驗和對現(xiàn)實生活的不滿。因此在現(xiàn)代主義文藝中,“……在焦慮里,你仍然有一個自我,仍然感到孤獨,你想縮回到自我里保持自我的完整,也就是說你知道該做什么。而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耗盡(burn-out)里,或者用吸毒者的語言,‘幻游旅行’中,你體驗的是一個變了形的外部世界,你并沒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說,你是一個已經(jīng)非中心化了的主體。”[2]現(xiàn)代主義者的逃避,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耗盡”,都是人緩解焦慮的措施。
這些措施中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想找到自我,或者說,找到自我的認(rèn)同感。沒有認(rèn)同感也就失去了生存感,獲得了認(rèn)同感,也就獲得了對自身存在的證明。對歐美文學(xué)的東方視角的闡釋歸根到底是對認(rèn)同感的一種尋找。對于歐美文學(xué)作品,我們是陌生的。為了消除這種陌生感,我們就必須對其加以解釋,所有研究其實都是一種闡釋。伽達(dá)默爾說:“對于在自然和歷史中與我們照面的所有事情來說,最為直接地向我們說話的當(dāng)是藝術(shù)作品。它擁有一種神秘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把握了我們的整個存在,似乎沒有一點距離,似乎與它的日常遭遇就是與我們自己的遭遇。”[3]
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對歐美文學(xué)作品做比較研究,是在異質(zhì)文化的作品中尋找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并要給這種感覺以理性的解釋,而解釋的最終目標(biāo)是使我們可以給歐美文學(xué)作品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找到一個位置,使之安居下來,這個目的實現(xiàn)了,藝術(shù)作品的“神秘的親和力”才會發(fā)揮出來。對于完全陌生的東西,我們是不容易接近它的,而完全熟悉的東西似乎又索然無味。東西方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方法在歐美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即是以熟悉的事物闡釋陌生的事物。這種闡釋的結(jié)果是使焦慮得以化解,并產(chǎn)生認(rèn)同感。“研究方式”這個具體的問題就這樣和全球化的文化語境產(chǎn)生了關(guān)聯(lián)。
三、文化全球化語境的必然要求
運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研究問題是文化全球化語境的必然要求。哲學(xué)家費希特指出:“究竟我們把后退的步伐還是把前進(jìn)的步伐叫做正量,那根本是完全無關(guān)緊要的;而問題僅僅取決于究竟我們愿意把前一種步伐的數(shù)量還是把后一種步伐的數(shù)量建立為有限的結(jié)果。在知識學(xué)里,情形就是這樣。在自我中是否定性的那個東西,就是在非我中的實在性,反之,在非我中是否定性的那個東西,就是在自我中的實在性;通過相互規(guī)定的概念展示出來的就是這么多,別的再也沒有了。究竟我們現(xiàn)在把自我中的東西稱為實在性還是稱為否定性,完全隨我的便,這里談的僅僅是相對的實在。”[4]這段文字對于我們理解異質(zhì)的文化很具有啟發(fā)性。
在歐美文學(xué)的研究中,我們將異質(zhì)的文化和文學(xué)與我們自身的文化和文學(xué)進(jìn)行比較。這種比較并不是從我們開始研究歐美文學(xué)時出現(xiàn)的,而是自我們開始翻譯歐美文學(xué)作品以來就已經(jīng)存在的。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學(xué)類似于“自我”,而異質(zhì)的文化與文學(xué)類似于“非我”。“自我”和“非我”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語境。同樣的事物,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的闡釋是不同的。在這種不同中,必然涉及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觀念等問題,這就要求我們以辯證的態(tài)度去看待和處理問題。湯姆林森說:“如果依照同時的、復(fù)雜的相連進(jìn)程,在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技術(shù)等領(lǐng)域內(nèi)理解全球化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包含了方方面面的矛盾、各式各樣的反抗與抵制的力量。確實,把全球化理解為是包含了各種對立的原則與傾向——地方與全球、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一種 ‘辯證法’,現(xiàn)在是十分普遍的,特別是在有關(guān)文化問題的敘述方面更是如此。”[5]22-23
我們在文化問題敘述方面為什么要堅持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呢?對這個問題,湯姆林森進(jìn)一步解釋說:“對全球化認(rèn)識有好的與壞的方式。一個壞的方式,是從一個前提出發(fā),這個前提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討論的維度是主控話語(master discourse),是‘事物真正全部歸一’的領(lǐng)域,是能揭開所有其他推理的邏輯。一個更好的方式,則是確認(rèn)描述世界的具體方式,這個世界包涵在一個經(jīng)濟(jì)的、政治的或是文化的話語之中,并且試圖在這些術(shù)語之中引出對全球化的一種理解,同時,不斷否認(rèn)其概念先行的做法:它是在多維性自我意識的認(rèn)可中去追趕的一個維度。”[5]23-24
對于歐美文學(xué)研究而言,普遍性是我們在研究中要挖掘的一般性規(guī)律,而特殊性則是研究中對個體差別的認(rèn)識。全球化的文化語境要求我們構(gòu)建“多維性的自我意識”,正是這一點開發(fā)了我們歐美文學(xué)研究中的辯證思維模式。全球化的視角將我們從僵化的決定論的泥潭中拯救出來,把我們放在一個多棱鏡的鏡面下,在這里,任何一種決定論都被多棱鏡顯示為破碎的影像,唯有辯證的思維方式才能立足,這是我們在歐美文學(xué)研究中,打破傳統(tǒng)思維定式,創(chuàng)新突破的最好契機(jī)。
四、全球化對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的沖擊
全球化對于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的沖擊是巨大的,這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首先,在全球化世界中,任何一個民族的價值體系和審美觀念都被置于比較的文化語境下。全球化讓人們之間的聯(lián)系越來越廣泛,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可能在全球范圍內(nèi)產(chǎn)生越來越深廣的影響。各民族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會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共存,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都走向多元化。人們的審美觸須向異質(zhì)文化伸展,因為人們需要借助異質(zhì)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為我們這樣的訴求提供了可能。由于與其他國家交流的深入,我們發(fā)現(xiàn),每一個國家被認(rèn)定為經(jīng)典的作品都不同。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經(jīng)典?經(jīng)典是否具有被世界各國各民族所接受的價值共性?為什么我們國家的經(jīng)典名著中的許多作品在歐美國家卻不受關(guān)注?其實,當(dāng)我們在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的時候,我們就已經(jīng)走上了質(zhì)疑經(jīng)典的道路,走上了對于多元價值觀的探索之路。
艾略特給“經(jīng)典”下過定義,他認(rèn)為,“假如我們能找到這樣一個詞,它能最充分地表現(xiàn)我所說的‘經(jīng)典’的含義,那就是‘成熟’。我將對下面兩種經(jīng)典作品加以區(qū)別:其一是普遍的經(jīng)典作品,例如維吉爾的作品;其二是那種相對于本國語言中其他文學(xué)而言的經(jīng)典作品,或者是按照某一特定時期的人生觀而言的經(jīng)典作品。”[6]
在艾略特的這種分類中,前者是普遍性意義上的經(jīng)典,而后者只是相對意義上的經(jīng)典。全球化的文化語境給了普遍性意義的經(jīng)典以更大的生存空間,因為其普遍性更能為其他國家的人民所接受。同時,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也使得艾略特所言的第二類經(jīng)典受到時間和空間的挑戰(zhàn)。時代不同了,人們的觀念變化了,某一歷史時期的經(jīng)典在另一歷史時期未必便是經(jīng)典,這就是時間的挑戰(zhàn)。一個國家的經(jīng)典,放在世界文學(xué)的平臺上,放在其他國家的文化語境下,就未必仍然是經(jīng)典了,這是空間的挑戰(zhàn)。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biāo)項目為“外國文學(xué)經(jīng)典生成與傳播研究”。這個題目寓意豐富,它標(biāo)志著我們對于外國文學(xué)經(jīng)典的研究由靜態(tài)轉(zhuǎn)向動態(tài)。靜態(tài)研究通常以文本為基礎(chǔ),對作品中表現(xiàn)的合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價值觀念大加宣揚稱贊。很多“紅色經(jīng)典”就是在這種靜態(tài)研究的背景下誕生的。而對外國文學(xué)經(jīng)典生成和傳播的研究,則是通過對經(jīng)典形成過程的分析,綜合考慮經(jīng)典文本生成過程中的諸多因素,把經(jīng)典放在歷史的天平上來測量其價值的。這種研究的成果最終將能夠區(qū)分哪些是艾略特所說的“普遍的經(jīng)典作品”,哪些是“按照某一特定時期的人生觀而言的經(jīng)典作品。”
中國學(xué)術(shù)界對外國文學(xué)經(jīng)典的理解正經(jīng)歷著另外一種考驗。判斷經(jīng)典的標(biāo)準(zhǔn)從意識形態(tài)決定論的樊籬下解放出來,并沒有因此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所有的問題。我們還面臨著普遍主義價值觀念的考驗。曹順慶先生將這種普遍主義的價值觀概括為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他指出“在西化即為現(xiàn)代化的時代,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被視為一種普遍主義價值。世界文化秩序的建構(gòu)是以這種普遍主義的信仰為基礎(chǔ)的。這種信仰認(rèn)為:自由主義可以提供一個價值中立的基礎(chǔ),讓所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在此基礎(chǔ)上交往和共存,在自由主義價值觀被相信并被理解為就是‘普遍價值’的時代,人們以自由主義來確立世界交往和共存的原則,并‘無差別的’評判世界文化關(guān)系。”[7]
新時期,我們確立經(jīng)典的標(biāo)準(zhǔn)是不完備的。當(dāng)經(jīng)典的標(biāo)準(zhǔn)被置于比較文化語境下考察時,我們就已經(jīng)在認(rèn)識文學(xué)經(jīng)典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我們還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從以前的用意識形態(tài)決定什么是經(jīng)典,走向以“普遍價值”代替意識形態(tài)決定論的做法。這兩個極端是我們在研究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時必須避免的。全球化時代為我們認(rèn)識經(jīng)典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幫助我們走出狹小的認(rèn)識空間,但同時,也使我們更容易再次走錯方向,把西方的價值觀念當(dāng)成是普遍性的價值觀念,這些是我們在認(rèn)識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時要留意避免的。
全球化語境下,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遭遇了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和讀圖時代。首先,網(wǎng)絡(luò)的發(fā)達(dá),使寫作不再神圣化,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網(wǎng)絡(luò)作家,針對時下人們最關(guān)心的問題發(fā)表見解。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讓人們無法靜下心來,細(xì)品名著。這樣,習(xí)慣于通過閱讀外國名著來充實心靈的人們,開始青睞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提供的快餐食品。我們不再從名著中找尋真理,而是試圖從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中找到問題的答案,或者讓自己的情緒得到宣泄。心靈雞湯式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是全球化時代科技高度發(fā)展的產(chǎn)物,它帶給我們許多便利而又同時也遮蔽了歐美文學(xué)名著本應(yīng)該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此外,網(wǎng)絡(luò)時代,人們更傾向于通過電視、電影娛樂,而不是讀名著。二流的文學(xué)作品也可以借助影視的影響,成為流行,經(jīng)典受到冷落,地位被動搖。讀圖時代,我們可以瞬間掌握世界上發(fā)生的重大事件,了解全球信息,這是高度全球化發(fā)展的結(jié)果。讀圖時代,也使我們可以用較短的時間,了解更多的名著,但是讀圖并不等于讀書。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是值得細(xì)細(xì)品味的,通過看電影、電視無法真正走近它、理解它。
[1]劉建軍.關(guān)于文化、文明及其比較研究等問題[J]東北師大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2(2):11.
[2]馬馳.新馬克思主義文論[M].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65.
[3]伽達(dá)默爾.美學(xué)與解釋學(xué)[A].伽達(dá)默爾集[C].鄧安慶,等譯.上海:遠(yuǎn)東出版社,2003:473.
[4]費希特.全部知識學(xué)的基礎(chǔ)[M].王玖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79.
[5]約翰·湯姆林森.全球化與文化[M].郭英劍,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
[6]T.S.艾略特.艾略特詩學(xué)文集[M].王恩衷,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190.
[7]曹順慶.跨越異質(zhì)文化[M].濟(jì)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