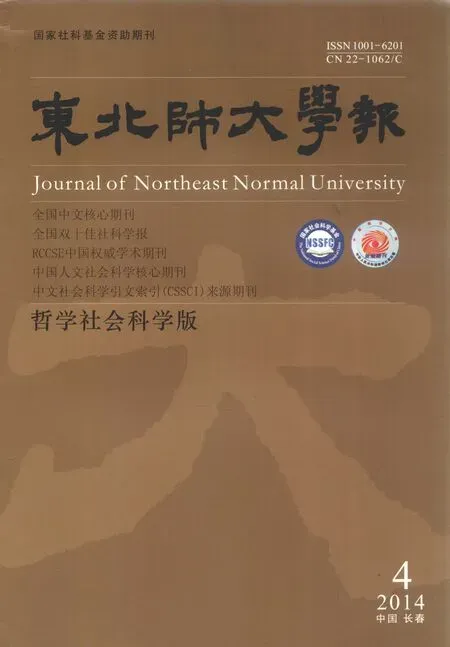組織邊界扭曲:原因及其識別
于尚艷,付才輝
仔細觀察大量的經驗現象和研究,發現兩種與TCE相悖的情況非常普遍:按TCE的預測,低專用性的交易本該采取“市場式治理結構”,但卻出現了“企業式治理結構”;高專用性的交易本該采取“企業式治理結構”,但卻出現了“市場式治理結構”。簡言之,本該“外包(buy)”的卻“自制(make)”了、本該“自制”的卻“外包”了。對于這一相悖的現象,支持TCE的文獻(尤其是經驗研究)將其視為大樣本中的不顯著事件忽略掉了;反對TCE的文獻(尤其企業邊界的能力理論)借機從根本上就否認了其理論。若正視這一相悖的現象,并承認TCE作為一個理論基準是正確的,那么就會出現一個極為要緊的問題:究竟是什么原因扭曲了在TCE看來是最優的交易治理結構?換言之,組織的邊界為什么會被扭曲?
有學者認為上述與TCE預測相悖的現象源于TCE所隱含的分析對象是出資人控制的企業而非代理人控制的企業。但他們的研究看似解釋了“原本該‘外包’的卻‘自制’了”,卻不能解釋“原本該‘自制’的卻‘外包’了”這一相同性質的相悖現象。本文認為,保護專用性租金免受敲竹杠的治理合約若由代理人來設計的話就可能扭曲對委托人來講是最優的治理合約。
一、問題的性質:異質的互聯合約
商業生活中存在這樣一種常見的經濟情景:老板(委托人)委托經理(代理人)去向供應商、經銷商、雇員以及投資者等采購、銷售、雇傭、融資帶有專用性的原材料、商品、勞動力、資本等。由于原材料等采購標的存在專用性,經理需要設計治理合約來防范交易對手敲竹杠的機會主義行為;由于信息不對稱,老板也需要設計激勵合約來克服經理的道德風險。
一個交易生成一張合約,交易之間的互動就會導致合約之間的互聯,合約之間的互聯可能會改變各自合約的內容,也即改變了博弈的結構[1-2]。
前面情景中問題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異質合約之間的互聯:股東和經理之間交易形成的是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的激勵合約;經理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形成的是保護專用性租金防止敲竹杠的治理合約。同質的互聯合約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分析,但遺憾的是,不完全合同與完全合同之間的互聯問題尚未得到關注。現實中存在與TCE相悖的現象意味著異質的互聯合約可能會產生沖突,這不同于同質的互聯合約能產生“以合約治理合約”的功效。
二、委托人設計的治理合約
這里,將治理合約定義為“保護專用性租金防止敲竹杠的微觀制度安排”。采購商獲得的專用性租金是其采取了保護措施以防患供應商敲竹杠的結果[3]。按標準假定,所獲得的專用性租金份額是租金保護措施的增函數且邊際功效遞減。由此可以得到治理結構的簡要形式。
要獲得特定控制必須對專用性投資及其產生的專用性租金做出明確規定,也即改善合約的信息結構,但得為之耗費信息費用。要獲得剩余控制必須耗費治理費用,在標的產權結構不明晰的情況下甚至可能需要動用私人暴力和社會資本來獲得剩余控制。信息費用與治理費用之和等于交易費用。按標準假定,交易費用是治理合約結構的增函數且邊際交易費用遞增。
這里,暗含的假定是交易雙方在交易期間的認知理性以及交易的復雜性相對穩定,因此就可以用治理合約設計的交易費用(信息費用與治理費用之和)及其收益(保護的專用性租金)之間的權衡來內生解釋治理合約的結構(特定控制與剩余控制)。
那么,委托人如何設計治理合約?
采購商通過治理合約的設計能夠主動控制專用性租金的獲取但得為之付出交易費用,其面臨的問題是一個不帶約束的優化問題。根據基本假定,在理論上可以得到治理合約結構的內點解、設計治理合約的交易費用、采購商獲得的專用性投資產生的專用性租金的份額和專用性水平。
進一步的分析發現,治理合約安排對效率的改進不是普遍的,其依賴于締約的信息空間與權力結構。信息空間影響治理合約設計中的特定控制及其邊際信息費用;權力結構影響治理合約設計中的剩余控制及其邊際治理費用。采購商在較差的信息空間與權力結構中締約所耗費的高額邊際交易費用會嚴重阻礙治理合約對專用性水平的效率改進。然而,信息空間與權力結構的好壞又取決于交易制度環境的差異。
最優治理合約設計的基本原則即治理合約的契約替代率必須等于特定控制與剩余控制邊際交易費用的比率,否則可以調整治理合約的結構來節約交易費用。
三、代理人設計的治理合約
采購商若委托一個代理人來與供應商交易,此時由代理人來設計與供應商交易的治理合約會產生什么后果?對此的研究思路是,先將治理合約設置成科斯式的“make or buy”經典二元離散分布,然后再用內生專用性的思維將其拓展到連續的情況。在前者的情況下,得到的結論是:當代理人的行動選擇及其績效是可觀察和可證實時,委托人給代理人的報酬可以直接依代理人的行動而定,從而激勵相容約束成為多余,由代理人來設計與供應商的治理合約不會存在扭曲;當代理人的行動不可觀察時(信息不對稱),激勵合約不能夠依存于代理人的行動選擇。給定依存于行動績效的激勵合約,代理人會選擇其行動來最大化其收益:在不對稱信息下由風險厭惡的代理人來設計與供應商交易的治理合約可能就會扭曲對委托人而言是最優的治理合約選擇。換言之,對委托人來講原本該選擇“自制”的代理人卻選擇了“外包”、原本該“外包”的卻選擇了“自制”。
“自制—外包”是治理合約經典的科斯式二元劃分,本文認為,在不對稱信息下由風險厭惡的代理人來選擇治理合約的話就可能扭曲對委托人來講是最優的治理行為選擇。這一結論的新奇之處有三點:第一,其鏈接了不完全合同(治理合約)與完全合同(激勵合約)在互聯合約中的關系,這一點被已有文獻忽視了;第二,異質的互聯合約可能會產生效率損失,這一點不同于已有文獻中同質的互聯合約會帶來效率改進的觀點;第三,組織(企業)的邊界由代理人設計的話就可能會被扭曲。
基于“自制—外包”的二元比較分析盡管在理論上能夠說明問題,但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會陷入科斯當年所面臨的“引而不用”的尷尬境地。在基本假設中可以看到在“自制—外包”兩個治理合約分布的極端狀態下,專用性水平都相同且處于社會最優水平,唯一的決策依據是各自交易費用的直接比較,即選擇費用相對較小的形式。姑且不論交易費用能否準確測量,事實上這種直接比較不成立:未被選中的治理合約的交易費用根本無法被觀察到。而用內生專用性的思維可以識別代理人設計的治理合約可能存在的扭曲。
用內生專用性的思維將其拓展到連續的情況。若委托人能夠觀察到代理人的行動時,委托人可以通過激勵合約控制代理人的行動,也即代理人的激勵相容約束不起作用,此時委托人的最優化決策實際上是一個帕累托最優的激勵合約:代理人獲得的固定薪酬等于保留工資加上行動的成本,代理人不承擔風險是因為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最優的行動水平出現在行動的邊際期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處。
若委托人不能夠觀察到代理人的行動時,給定激勵合約,代理人會選擇能夠最大化其確定性等價收益的行動。對比兩種情況可發現:在不對稱信息下由風險厭惡的代理人來設計與供應商交易的治理合約扭曲了對委托人來講是最優的治理合約選擇。顯然,行動本身委托人不可觀察,也就無法測度,由此也帶來了委托人的期望收益或代理人的行動績效損失。這再一次從委托人收益的角度表明了在不對稱信息下,若由風險厭惡的代理人來設計與供應商交易的治理合約,將扭曲對委托人來講是最優的治理合約選擇。由委托人的支付函數的結構可以看到,可以利用支付值、治理合約安排、交易費用、專用性租金及其分配、專用性投資、專用性等變量來間接識別可能存在的扭曲。根據已有經驗,這些變量之中只有專用性的信息相對容易獲取,因此,內生專用性成為最為便利的識別工具。
[1]D.Kreps,J.Milgrom Roberts &R.Wilson.R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27(2):245-252.
[2]J.McMillan & C.Woodruff.Private Order under Dysfunctional Public Order[J].Michigan Law Review,2000,98(8):2421-2458.
[3]張鳳超,付才輝.專用性的內生化——一個制度視角的解釋[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7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