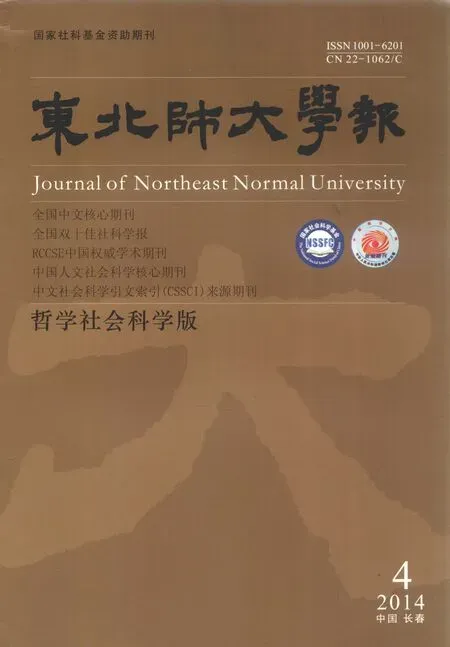美學視閾中的綜合藝術教育
張 波,張 群
綜合藝術教育的繁榮與發展已成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大重要景觀。在綜合藝術教育日益繁盛的時代,對其進行哲學澄清,既是藝術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哲學具體化、現實化的最重途徑。讓綜合藝術具有哲學性,使其能夠與美學進行形而上學照面,能夠使綜合藝術教育的實踐主題、價值追求與形上意境得到本質的提升,從而能夠真正將綜合藝術教育與人性的生成與完善結合起來。綜合藝術教育作為具有兼容性、豐富性和代表性的藝術教育形式,與人生命的雙重性、矛盾性、開放性與未完成性是內在契合的。以美學的視閾來詮釋綜合藝術教育,能夠將其歷史性、社會性、文化性與多元性特質與現代人的素質養成和自由個性培養有機結合起來。
一、直指世界觀構成的綜合藝術教育
綜合藝術教育觀念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蓋蒂藝術中心。目前,“綜合藝術教育”這一教育模式遍布于美國各個學校使其中小學藝術教育實踐活動邁上了新的臺階,從而使得綜合藝術教育也成為當代教育學與哲學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在教育實踐環節中,綜合藝術教育模式利用藝術創作、藝術史、藝術批評和美學四個學科的互動互補關系,將藝術教育建構成一門交叉性的人文學科,從而提高藝術教育效應與受教育者的綜合人文素養。在此意義,綜合藝術教育使“美就是人類經驗的組成部分”[1]成為可能。
綜合藝術教育的提出與實踐,首先是對藝術教育理論創新與拓展。“教育并非是成熟的結果,而是一種文化的發明。”[2]138綜合藝術教育的理論包括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美學前提、教育理論前提和藝術教育理論前提,是一種均衡的藝術課程。綜合藝術教育采用綜合教育方法,其教學方法和課程計劃不僅僅局限于青少年,而是普遍適用于藝術教育基礎之中[3]。它以多學科為基礎,其實踐核心是將藝術批評、藝術史、美學和藝術創作融入課堂教學。因此,綜合藝術教育是追求一種均衡的藝術課程,對來自藝術史、藝術批評、藝術創造與美學這四門學科的內容給予了同等的重視。
這樣的藝術教育形式,更為當代人世界觀的建構開創一條別樣的路徑。我們知道,一種全面的教育能培養個人全面思考的能力,使個人通過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通過綜合藝術教育使受眾熟知各藝術學科的各個方面,能夠用藝術媒介來表達思想,能夠讀懂藝術中的內在價值、評論藝術、了解藝術史以及美學中的基本概念。綜合藝術教育給予受眾是一種自我解放的手段,是一種在其他文化形式中不可能獲得的內在自由。
二、建構“審美生活”的綜合藝術教育
“美”是人生命與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維度。“美學之父”德國哲學家鮑姆加登首先對美的本質進行了哲學反思,在學科的意義上強化美的形而上學意義,也提出了建構審美生活的必要性。盡管13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認為“美的事物是那些讓人心曠神怡的東西”[4],但是,這種知覺與美關系的闡釋還沒有真正確立建構審美生活的自覺意識。對此,英國藝術教育家里德的觀點極具啟發性,“美學,或稱知覺科學,涉及感性知覺與形式組合兩個活動階段,而藝術也許包含著比情感價值更大的東西。在探討美的觀念時,我們曾引入了一些僅同藝術史有關的見解;藝術的目的旨在傳達感受。它與美的特質,即通過一定形式傳達的感受常常混在一起。無論我們怎樣界定美感,我們務必先從理論上加以證明。抽象的美感僅僅是藝術活動的基礎。藝術活動的闡述者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活動容易受到各種生活激流的影響。”[5]
建構審美生活的藝術教育體系是當代藝術教育中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在上世紀中期藝術教育的轉型期是巴肯明確提出教育改革應該包括“審美的生活”。而后諸多的學者從藝術教育的人文主義本質、藝術教育提升審美經驗的獨特意義,以及反思藝術教育本質方面推動了巴肯教育理念的實踐與創新。弗爾德曼認為,當時的藝術教育領域過分重視藝術表演的發展,忽視了學生其他方面的創造性潛能,如對藝術的欣賞、批評與反思。艾斯納批評了以藝術創作為中心的藝術教育,他認為藝術教育包括三個學習領域,即創作、批評與歷史領域。L.謝普曼強調藝術必須成為學校課程表上的一門基礎課程。藝術教育的對象是面向全體學生。她認為對藝術品的審美反應與藝術創造同等重要;審美反應不僅針對“學校藝術”,也針對傳統藝術杰作乃至現代的各種藝術形式[2]20。
質言之,如果在藝術教育中僅以美學的方式對審美經驗與藝術評價進行自然的批判性反思不可能真正建構“審美生活”。而綜合藝術教育則通過培養受眾對藝術的深層次理解、強化藝術與生活的結合、轉換思考藝術的思維方式、確立體驗與評價藝術品的批判性原則、反思藝術存在與表現形式、提升藝術創作與藝術欣賞的視野與技巧、體驗藝術發展史的輝煌與曲折等方式,將美學的抽象反思與藝術的鮮活及感性結合起來,使之成為生命與生活的現實內涵。綜合藝術教育不單是某種特殊的教育手段與方式,而是建構“審美生活”的生活實踐。這樣的教育,使人現實的“感性活動”[6]不僅錘煉了創作與欣賞藝術的人的身體,而且建構了人的現實的形上生活。
三、綜合藝術教育的“美學”內涵
美學研究的抽象化與藝術教育的具體化使得人們在藝術教育中更關注藝術史和藝術評介。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美學反映了藝術與生活的結合,美學審視著我們思考藝術的方式,美學檢驗的是概念性問題,是源自人們言行方式的問題”[7]10。美學側重兩個方面:其一,審美價值與人們用以解釋、評論某藝術品的標準;其二,藝術品獲取意義與內涵的途徑。但是,我們也更應該關注藝術品通過直接再現真實的世界獲取意義。甚至可以這樣認為:第一,藝術的本質、藝術體驗以及人們用來談論藝術的基本概念都是理解“我們是誰”、“我們有什么樣的價值觀”等問題的一部分;第二,考察藝術信仰能夠增強人們對單個藝術品的敏感性,使人更具辨別力,更好地選取某種藝術來欣賞、保留與創造;第三,藝術教育的普遍價值在于以美學視閾分析藝術本質、形成適用于視覺、造型及觸覺藝術的闡釋與評價原則[8]。
因此,綜合藝術教育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在于拓展藝術教育的內涵,更是以具體化的形式與感性的方式培養學生的美學潛質。首先,綜合藝術教育以助學生提高理解特定藝術作品和藝術整體能力的方式,使學生在困惑與爭論中獲得具體的美學體驗。其次,當藝術作品、談論藝術史、藝術評論真正回歸到生活世界之中時,任何在綜合藝術教育中所提出與探討的問題就自然會超越對藝術的直觀理解,將對人生命的本性與本質及其與世界之間關系的思考和藝術勾連起來。再次,綜合藝術教育在教育中力求將美學與受眾經驗聯系起來的方式,既是認真對待受眾的藝術理解力的重要方式,還能在受眾的藝術體驗中直觀和表征其世界觀[7]257。
在一個藝術教育與藝術本身都深刻變化的時代,將價值觀念的教育與價值體系的建構貫穿于綜合藝術教育中就是一種必然。從藝術教育與藝術本身變化的特點上講,其變化是多樣化、非連續性,甚至是碎片化與解構性的。帕森斯與布洛克將這種變化稱為“后現代主義”。而且,當今時代充斥著其他文化和傳統的信息,藝術家與大眾不能自動地形成相互理解,而藝術教育的目的也就是為了促進這種理解,藝術教育要更具有反省性和哲理性。拉爾夫·史密斯所講,“人們從藝術中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一種理解,對世界的理解,一種與自我認識或心理洞察不同的東西。在美術博物館待上幾個小時,我們再走出來,會發現眼前的世界不同于原先看到的世界。我們看到了過去沒有看到的東西,而且開始以一種新的眼光觀看。這些表明我們學到了知識。……‘一件物品或事件是如何以藝術品特有的方式起作用的事實,向我們證明,這種作用方式可以通過某種指涉功能,造成一種全新的觀看世界和創造世界的方式。’……藝術造就一個最高級的善,對于這種善,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去追求和培養。既然古德曼認為藝術品向我們提高什么的過程不僅需要時間,而且需要訓練和培養,我們就有理由認為,正規學校的教學理應把這種訓練和培養包括進去。”[7]60
我們知道,在多元化與全球化的時代,多元與平等、差異與尊重、民族與世界等之間的矛盾沖突越發具體與現實。因此,如何看待不同群體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不同藝術形式與作品的社會內容與功能如何體現特定群體的價值等問題就成亟待解決的問題[7]52-53。如果我們想要回答此問題,我們有意識地進行探究,那就是美學研究,因此美學研究也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問題是如何思考某種藝術形式,我們可以說美學自然地產生于藝術和生活中。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美學家,美學課程就是要努力持續地追蹤這些問題,并且給予足夠的理性嚴謹。
四、結 語
藝術哲學是與多種藝術課程相聯系的,與藝術創造、藝術批評、藝術歷史,以及對藝術作品的概括性理解相聯系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把美學與其他課程的學習相聯系,藝術教育學習的各種課程是復雜地聯系在一起的,而它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則最為清楚地表現于美學。我們希望學生們既能接觸藝術,自由自在地喜歡藝術,但也能夠擁有審美的眼光去理解藝術,學習其有價值的東西。在對綜合藝術教育的思考與實踐中,美學占有特殊的位置,而美一直是美學的中心題目,而對于美的分析則被認作是美學的主要題目,美學像藝術一樣難以被準確定性,因為它是隨著藝術家的實踐而變化的。當新的意義出現時,它們不是取代舊的意義,更多的是與之共存。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著豐富的審美文化傳統,我們要建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美學體系,當然也需要吸收國外先進的美學成果,同時,針對本國的藝術教育實踐的研究,弘揚我國民族優良的審美文化,當然,我們在這些方面的研究還不足。
當前,我國藝術教育研究中對美學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筆者認為要做到兩個必須:首先,必須要在美的哲學方面下功夫,沒有哲學基礎,就不能講清任何美學問題。美學的發展不能停留在對審美文化研究的層次,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和內在規律,所以,從美學的實際出發,以哲學為指導,美學研究才會有新的突破;其次,必須要注意理論聯系實際。在藝術教育中,美學研究作為一門科學,在特定的歷史條件決定下,不能局限于精神范圍之內,而要必須發揮自己在實際生活中應有的社會作用,要引起社會對其的重視,要能夠更好地生存與發展。
[1][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190.
[2]R.A.Smith.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9.
[3]Dobbs,Stephen M.Learning in and through art:aguide to 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M].U.S.A:The J.Paul Getty Trust Press,1998:4.
[4]R.A.Smith and A.Simpson.Aesthetics and Arts Education[M].Urbana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onois,1991:18.
[5][英]H.里德.藝術的真諦[M].王柯平,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7.
[6]涂良川.馬克思“感性活動”的形上意義[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31-34.
[7][美]帕森斯·布洛克.美學與藝術教育[M].李中澤,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8]王偉.當代美國藝術教育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