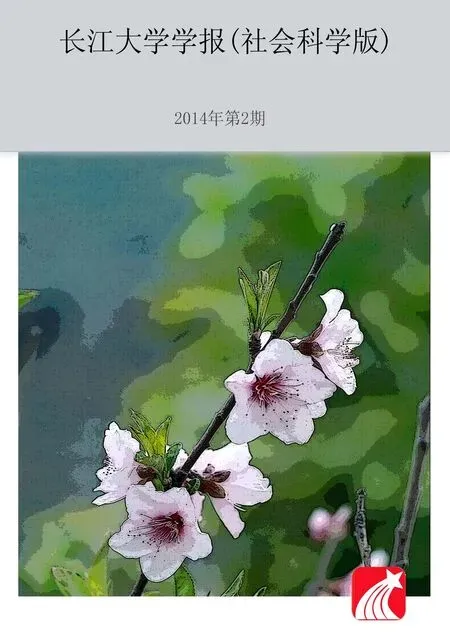生態女性主義視域下的《又來了,愛情》
蘇鳳美
(綏化學院 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綏化 152061)
國內外學者指出,是小說解構了男性中心地位,吶喊出社會第二性即女性的心聲,倡導女性和自然才是人類走向未來的本源。《又來了,愛情》正是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告訴人們,男性與女性,男性與自然之間,不應該是統治與從屬的關系,而應該和諧相處,唇齒相依,只有提高女性與自然的地位,人類社會的發展才有未來。
一、父權社會下女性與自然的命運
當代西方科學割裂了人類與自然的依存關系,將世間萬物分為各個等級,認為人類高于自然,自然界的一切都要為人類的利益服務。這一觀念,恰恰與西方傳統的社會價值觀不謀而合。在等級森嚴的二元社會中,男性占統治地位,是第一性,而女性和自然則在社會發展中占從屬地位,毫無話語權。正如王文惠所說,“社會的權利話語是以性別、財富、社會地位來決定每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女性被排斥在社會文化之外,被剝奪了平等的社會地位。”[1]格里芬甚至認為,女人與自然在男權社會中同樣處于附屬地位,她們與生俱來的消極被動,逆來順受以及不求回報的奉獻等特性,都驚人地相似,然而,正因如此,她們常常受制于男性,失掉了話語權,成為了社會中的“他者”。[2](P37)
在《又來了,愛情》中,朱莉出生于19世紀的拉丁美洲法屬殖民地,是一個香蕉園主與其黑人情婦所生的私生女。在父親的資助下,朱莉學習了繪畫和音樂,極富才情。然而,在當時的社會里,朱莉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作為靠山,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來自男性勢力的重壓,使她幾度被遺棄,腹中的胎兒也慘遭夭折。冷酷的社會現實,使得朱莉不得不隱居在密林深處,以作曲、繪畫或教書為生,在大自然中尋找心靈的慰藉。大自然雕琢了她的藝術氣質,喚醒了她被父權社會摧殘的意志,重新點燃了她的生命之光。這也印證了Starhawk的觀點,對大自然的信仰,成就了女性生存與抗爭的動力,只有對女性與大自然的尊重,才能讓人類擺脫等級社會的枷鎖。[3](P89)最終,50多歲的印刷商對她張開了懷抱,然而等級森嚴的社會現實,卻將朱莉排斥在正常的社交生活之外。朱莉在她的日記中寫道:“我在每個場合都被人排斥在外,如果有人向我伸出手,我會向他伸出手,我知道我的手會伸入云霧里,就像山里下大雨時我的池塘上濺起的水霧一樣。”[4](P82)鎮上的居民無時無刻不以挑剔的目光審視她,詛咒她。朱莉不甘接受這樣的窘境,不甘墮入婚姻的囚籠,成為男性社會中喪失自我的玩偶,最終投入了一池碧水。她用如此慘烈的方式,控訴了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摧殘,也最終從男性勢力的重壓下解脫出來。
然而,男性社會的侵略性和破壞力還不止于此,他們將與女性密切相關的,為女性提供抗爭的勇氣和人生信仰的自然也破壞殆盡。生態女性主義認為,“自然化的女人”和“女人化的自然界”都被驅逐到了服從與被利用的邊緣化的位置,成為了男性社會的犧牲品。[5]一個世紀之后,朱莉已經成為女編劇薩拉筆下的傳奇人物,并受到人們的熱情追捧,貝爾河的統治者們在(白人男性)利益的驅使下,決定修建新的旅館,百年前朱莉的樂土和精神家園,如今滿目瘡痍,殘敗的橄欖樹,笨重的卡車,遍地的水泥板,無不昭示著男權文化對女性、自然的踐踏與毫無節制的掠奪。
二、男性、女性與自然和諧相處
在父權制社會中,男性與女性、自然之間二元化身份的認定,似乎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生態女性主義并不認同這種固化千年的二元思維模式。她們認為,“男性對女性的尊重將促進男女關系的和諧,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人類對自然的尊重將促進自然與人類的和諧共處,反之,則是女性的反抗斗爭,自然的怒吼。”[6]換言之,不論是人與自然還是兩性關系,亦或種族之間,都應當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并在和諧統一中發展進步。
萊辛重視女性的內心體驗。她一方面反思著父權社會對女性和自然的壓抑,另一方面,則尋求著男性與女性、自然和諧相處的方法。萊辛認為,要摒棄二元對立的男性中心主義觀點,首先就需要男性認識到,女性有與其相同或相似的情感需求,意識到女性與自然不是男性占有欲甚至掠奪欲支配下的犧牲品,男性與女性應該共同努力創造一個男女平等,與自然和諧相處,可持續發展的物質與精神上的生態家園。
在《又來了,愛情》中,萊辛通過女作家薩拉表明了其生態女性主義觀點。薩拉是朱莉在當代的延續,二人雖然相隔一個世紀,所經歷過的生活和年齡段也各不相同,但是她們在父權社會所遭受的苦楚和內心的煎熬卻驚人地相似。薩拉認為,朱莉就是自己的靈魂,就是不能被世人所允許存在的另一個自己。薩拉早已將激情化作一泓池水,不敢再去放任愛與被愛的欲望。她拒絕了年輕英俊的男主角的愛慕,決絕地避開了導演亨利(一個有婦之夫)的追求。薩拉在欲愛不能的困境中掙扎吶喊,“可以肯定地說,在以往的幾次戀愛中,她從未感受過這種絕對的、滲透性的需求,欲望難以滿足的空虛感吞噬了她的軀體,似乎她的生命本身被壓抑了。是誰感受到這種高度的需求,高度的依戀,是誰必須孤苦無依地躺在那兒,等待那溫暖的手臂的擁抱和升華到戀愛狀態的幸福時刻?”[4](P332)
薩拉將朱莉搬上舞臺,塑造了一個富有才情,敢愛敢恨的奇女子形象,贊美了她對父權社會的不屈服和對自由、平靜生活的向往,不過作為第一性的男性勢力似乎并不買賬。史密斯(薩拉的第一個追求者)說,他喜歡朱莉的音樂,傾心于她的才華,但他對朱莉“冷冰冰的”智慧以及在日記中揭露的父權對女性與自然的壓抑與摧殘,卻無比地反感。不僅如此,男性統治者只是把女性和自然當作他們可以肆意侵害的私有財產,就像亨利本來有自己的家庭,卻放任自己對薩拉的愛情,就像貝爾河的男性決策者們將朱莉從前賴以生存的密林、碧水改造成喧鬧的,毫無靈性的露天劇場。在這樣的暴行中,女性與自然逐漸地被驅逐到了絕望的邊緣。
小說的最后,薩拉經過幾番愛情的蕩滌,終于悟透了女性與男性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相處之道,詮釋了平等、和諧的生態女性主義理想。男性勢力的代表,薩拉的弟弟,最終也在妻子的激烈反抗下,一改往日的盛氣凌人,不再將女性看作他的私人財產,看作毫無話語權的他者。一家人從激烈的矛盾沖突中解放出來,取而代之的是溫馨和睦、平等互愛的和諧場景。
在《又來了,愛情》中,萊辛并沒有簡單地渲染朱莉和薩拉在父權社會中所遭受的種種摧殘與不幸,沒有以極端的女權主義意識倡導女性與自然優于男性勢力的思想。她試圖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告訴人們,男性和女性應該在精神層面上達到相互的理解與包容,應該在平等和對話的基礎上,與自然建立起一種和諧共生的生態模式。萊辛小說中蘊含的生態主義思想,為女性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
參考文獻:
[1]王文惠,曾敏.追尋生命和諧的精神家園——《又來了,愛情》的生態倫理啟迪[J].外語教學,2012(1).
[2](美)蘇珊·格里芬.女性與自然:內心的呼喊[M].舊金山:HarperandRow,1978.
[3]Starhawk.The Earth Path[M].New York:HarperCollins,2005.
[4](英)多麗絲·萊辛.又來了,愛情[M].瞿世鏡,楊晴,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5]孟鑫.國內學者對西方女權主義七個流派的評介[J].教學與研究,2001(3).
[6]陳偉華.生態女性主義的倫理:一種新的倫理秩序[J].湖北社會科學,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