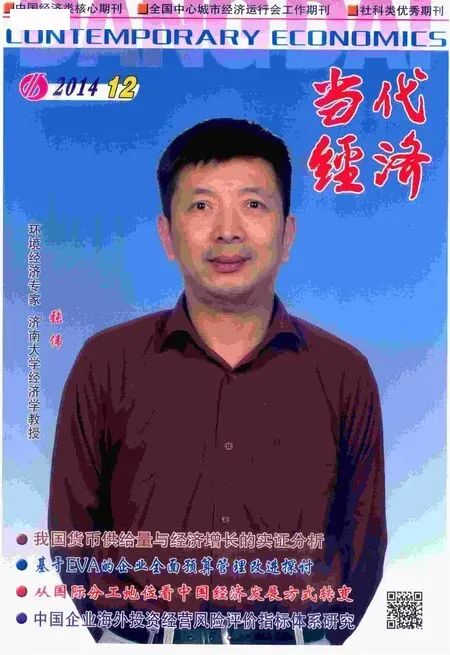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問題研究
○高 欣 張啟文 胡 畔
(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近幾十年以來,隨著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鄉二元結構也在不斷加深,“三農”問題越發嚴重,特別是加入WTO后受到了國際農產品市場的強力沖擊,競爭力低下的中國農業在國際市場上很難找到立足之地。這些都說明我國農業發展急需改變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由勞動密集型為主走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發展道路,農業生產走向規模化和專業化將是必然的趨勢。農村資金大量外流的現實情況是不合時宜的,要使得更多的資金留在農村,甚至讓更多的社會資金進入農村就必須大力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加大對農村的信貸投放。然而現實中農戶卻很難從金融機構中獲得長期的、額度較大的貸款,其原因在于缺少有效的抵押物以及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所以很多學者研究認為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會是個有利的嘗試。
一、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存在的問題
1、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效力有缺陷
對于“四荒”土地承包經營權,《擔保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和《物權法》盡管在表述上不完全相同,但都明確了其抵押的合法性。然而,對于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否設定抵押,法律法規未作明確規定。一方面,《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條關于“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經營權可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之規定,與第四十九條規定的非家庭承包經營權流轉模式相比,多了“轉包和互換”,但少了“入股和抵押”模式,從法規條文表述差異上可以看出,立法機關對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處分方式采取了審慎態度。《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條并未明確將抵押列舉為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式,抵押能否作為流轉的“其他方式”,存在不確定性,在現有法律框架下,以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經營權設定抵押依舊存在無效的可能。
2、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虛置
財產所有權主體明確是進行市場交易的基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明晰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農村土地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礎。從我國現行立法規定中可以看出,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可以是鄉(鎮)集體經濟組織,也可以是村集體,甚至可以是村小組。其結果是導致土地所有權主體實質上的虛置,也必然對農村土地市場的發展造成重大障礙。特別是國家依然保留了對集體土地的征用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以及管理權,擁有比所有權人更大的控制權,這使得農村土地權利擁有者之間的關系變得不穩定,阻礙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
3、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式不明確
現行法律法規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規定,限制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有效流轉。一是《物權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有權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轉包、互換、轉讓等方式流轉”,確認了轉包、互換、轉讓三種流轉方式;《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第四十二條規定“承包方之間為發展農業經濟,可以自愿聯合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從事農業合作生產”,明確了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入股五種流轉方式。上述兩部法律所規定的流轉方式并不一致,按照法律適用原則,新法優先于舊法適用,應適用《物權法》;按照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原則,應適用((農村土地承包法》。這種立法上的不一致,導致農村土地管理部門和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上產生混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設計的缺失,不利于對土地流轉雙方當事人權利的保護。
二、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可行性分析
1、現實需求
一方面,中國加入WTO后,加速了與世界普遍的經濟規則接軌,正在快速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過渡,而目前實行的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按人口均分土地,導致家庭承包經營的土地零碎分散,規模化經營難以形成,浪費了土地資源和生產成本,在市場競爭中能力較低,一旦遇有風險即造成重大損失。另一方面,《土地承包法》構建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的基本框架,確立了土地與農民的承包經營權關系,但目前在農村,農民以家庭方式獲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在其財產中占有絕對比例,除此之外難以提供有效財產設定抵押向金融機構獲得信貸資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融資功能的弱化,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在簡單生產結構和低收入水平。
2、法律依據
《民法通則》、《農業法》都有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規定,但這兩部法律都沒有涉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更沒有涉及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擔保法》雖然規定了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經發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溝、荒灘等地的上地使用權可以抵押。但畢竟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同于土地使用權。因此,該規定并不能成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法律依據。首部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是《農村土地承包法》,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農村土地,經依法登記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或者林權證等證書的,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讓、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轉。”可見,該規定和《擔保法》第三十四條第(六)款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直接法律依據。從《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條來看,用于抵押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應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土地承包經營權須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農村土地,這是相對家庭承包方式而言;第二,經依法登記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或者林權證等證書。《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其他方式流轉。”
三、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對策建議
1、明確土地產權主體
根據法律規定,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是農民集體,包括鄉(鎮)農民集體、村民小組農民集體及村民委員會農民集體三個層級,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多元化導致了所有權主體的虛位,在此基礎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自然也缺乏明確的利益主體,真正的權利主體難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律法規范圍內自由支配其所有物,依法行使所有權,土地作為重要財產的價值未能有效發揮,由此帶來的是農村土地所有權制度的整體失效。因此明確土地產權,就是要明確土地所有權的主體代表,這關鍵問題就是明確集體所有權的主體,改變鄉(鎮)農民集體、村民小組農民集體及村民委員會,名為三級所有實為多元分化的怪圈。具體說來,要明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是村民委員會。
2、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原則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應當遵循“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一是依法。要嚴格按照《物權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規定的原則和程序流轉,土地承包方作為土地流轉的主體,依法決定是否流轉,以法律規定的方式流轉,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犯承包方權益。二是自愿。土地是農民的生存和發展基本保障,除非農民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就業機會,并自愿離開自己的土地的時,才鼓勵其土地流轉。農民是土地流轉的主體,必須從程序和實體上予以充分尊重和肯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強令或采取其他方式逼迫農民違背自己意愿,做出土地流轉決定。土地是否流轉、以何種方式流轉都該由農戶自己說了算,三是有償。實現有價值形態的土地流轉,充分體現了農村土地經營主體的利益調節和自主意識,使市場經濟手段真正成為調節的主導。
3、嚴把貸款準入關口
一是在立法未予明確前,僅限于以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荒地土地承包經營權,承包人與發包的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必須簽訂承包合同,依法取得承包經營權證。二是設立農村承包經營權抵押,必須經過發包方的同意。村集體發包的土地等承包經營權抵押,必須首先征得村委會或集體經濟組織的同意,由村委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主持。三是嚴格限定借款人范圍。規定在承包土地上從事養殖、種植、加工,形成規模經營及流轉價值的承包人以及直接承包集體經營項目的承包人,可以以其承包經營權抵押申請貸款,且必須確有實際經營活動和真實的融資需求,自有投資資金比例不低于30%。
[1]王宇紅、孫柏璋:“包容性增長”理念視閾下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金融制度的架構[J].調研世界,2011(1).
[2]王艷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及其限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1).
[3]葉敏: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可行性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1(15).
[4]馬浩青、俞凱:對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探討[J].法制與社會,2011(14).
[5]張鶴華:完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融資的思考和建議[J].現代營銷(學苑版),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