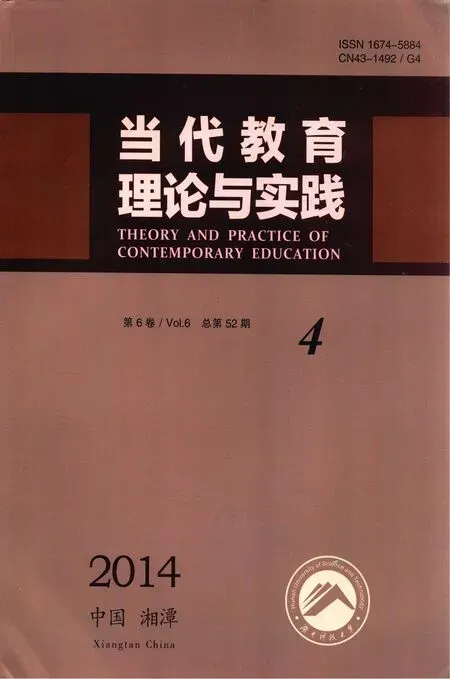“善惡皆是”還是“善惡皆非”①——《雙城記》中德法奇太太的雙重身份
董 梅
(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湘潭 411201)
“善惡皆是”還是“善惡皆非”①
——《雙城記》中德法奇太太的雙重身份
董 梅
(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湘潭 411201)
《雙城記》是現實主義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巨著,小說形象生動地刻畫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徳法奇太太就是其中一位。徳法奇太太雖然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但在整篇故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文學評論家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對此部小說進行過大量研究,對其評價也是褒貶不一。無意在德法奇太太是善是惡上做出絕對性判斷,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分析德法奇太太的性格是如何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逐漸由善變惡以及社會環境是如何影響她雙重身份的形成。
善惡;雙重身份;德法奇太太;《雙城記》
1 引言
查爾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代表人物之一。《雙城記》是狄更斯一部知名度極高的小說,國內外學者對此部小說做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評論家對這部小說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人物身上所體現出的人道主義,狄更斯對于革命的態度以及其對善的頌揚和對惡的抨擊。關于這部小說主題和技巧的研究非常多,對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探討也不少。其中,分析德法奇太太人物形象的評論不在少數,但是大部分關于德法奇太太形象的評論集中在她在復仇行動中殘酷惡毒的一面,對德法奇太太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形成的雙重身份很少提及。本文試圖闡明隨著故事的展開德法奇太太一反她有同情心、勇敢正義的形象變得惡毒殘暴的深層原因,以此來試圖揭示德法奇太太由善變惡的內在原因。
在小說《雙重記》中,德法奇太太被描述為一個具有雙重身份的女人,她的雙重身份可以在以下幾個轉變中得以體現。第一,一開始,德法奇太太同情受壓迫者并領導他們對抗貴族階級,從這一層面講,她是一個勇敢的女英雄。然而,由于德法奇太太對貴族階級不可消除的仇恨,她變為了一個惡毒的復仇者。第二,在小說的一開始,德法奇太太是一個受迫害者,但是當革命爆發,她的角色即由一個受壓迫者轉變為一個冷血的壓迫者。第三,德法奇太太是埃弗雷蒙侯爵兄弟罪惡的受害者。她扭曲的人格即是由于她不幸的童年及悲慘的生活經歷造成的。當暴亂發生,德法奇太太即由一個受害者搖身一變為一個加害人。因此,德法奇太太互相沖突的雙重身份是當時社會環境影響的直接結果。
2 德法奇太太作為女英雄和復仇者
約翰·杜威在《人性與行為》一書中認為:“人性存在且活動于環境之中,是在環境中塑造出來的,具有‘可變性’和‘可塑性’。”人生活在一個社會環境里,受到其周圍環境(包括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的限定。因此,杜威界定的人性的定義是:“……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制度機構和文化傳統不斷地把生物原料塑造成一定的人的模樣。”他認為,“一切善與惡都是與客觀力量結合而成的習慣。它們是個人特性中的某些要素與外部世界提供的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1]杜威排斥將人視為身、心二元對立的組合體,而人性也不是非善即惡的絕對先天性,而是隨環境、習慣、心智等因素相互活動的歷程,由經驗不斷的累積而成。高廣孚在《杜威教育思想》一書中指出,“如果將人性固定化,無異在變化的“實在”(reality)中,尋覓一成不變的”確然“(certainity),這是不可能的。”[2]杜威認為:“人性存在且活動于環境之中,所謂‘于其中’者,非如銀錢之置于盒中,而若物之生長于土壤日光中。”[1]換言之,人性是在環境之演變過程中,逐漸被塑造而成。因此杜威反對傳統的性善或性惡論,肯定人性的可變性(alterability)和可塑性(malleability)。
德法奇太太作為女英雄和復仇者的雙重身份正是由于法國大革命期間動蕩的社會環境所致。她人性中作為勇敢女英雄的“善”與作為殘暴復仇者的“惡”都是當時動蕩客觀環境的結果。德法奇太太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性人物,她首先被描述為一個勇敢的女英雄,隨后被描述為一個惡毒的復仇者。她本性中善與惡的兩面性正體現出“人性是在環境中塑造出來的,具有‘可變性’和‘可塑性’”的論斷。
在小說的前幾章里,我們看到她總是安靜地坐在她和丈夫經營的酒鋪里編織衣物。然而,她這種假裝的被動掩蓋了她對復仇不間斷的欲望。當革命爆發,她由一個勇敢的女英雄轉變為了一個惡毒的復仇者。德法奇太太成長在動蕩不安的革命時期,遭受慘痛的個人悲劇,童年的創傷對德法奇太太的個性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法國大革命爆發前,法國社會危機四伏,階級矛盾重重。貴族階級蠻橫無理,殘酷剝削、欺壓百姓,底層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貴族階級的通知地位搖搖欲墜。德法奇太太正是這一動蕩時期的受害者之一。一方面,作為一名貴族階級殘暴統治洗的受害者,德法奇太太遭受了巨大的不幸,她對殘酷殺害她家人的貴族階級懷有著極深的仇恨。在這種長期的仇恨在動蕩的環境中滋長為一股反叛的力量,促使德法奇太太在動亂時期敢于領導群眾起義攻打巴士底獄,推翻統治階級。在這一層面上,德法奇太太是個勇敢的女英雄。法國貴族階級的殘暴統治和德法奇太太童年的不幸遭遇使德法奇太太成為率領法國大革命的女英雄。另一方面,埃德蒙兄弟對德法奇太太家人的殘酷殺害使德法奇太太從小就對貴族階級懷有不可磨滅的仇恨。在暴亂發生時,德法奇太太毫不猶豫地將敵對階級的頭砍下。為了滿足她復仇的欲望,她不分善惡,甚至要傷害包括達奈在內的所有貴族階級,還意欲殺害露西和曼內特醫生。此時的德法奇太太性格已經在仇恨之火中扭曲。
作為一名受壓迫者,德法奇太太同情受壓迫者,并聯合他們一起反抗貴族階級的壓迫。盡管她銘記她家人悲慘的命運,仇恨也根植于她內心深處,她對底層階級的人民的態度很友好。比如,她為一個底層階級家的孩子慘死在侯爵的馬車車輪下的景象感到難過;她為馬奈特醫生不公正的囚禁感到憤怒和同情。當侯爵的“馬車橫沖直撞地穿過大街”并軋死一個孩子,侯爵不但沒有擔心孩子的生死,反而擔心他的馬是否受傷時,德法奇太太對貴族階級的仇恨和她對底層階級人民的同情達到了極致。“他扔出一個金幣”以補償被軋死孩子的父親。見到這一幕,德法奇太太勇敢地將金幣扔回了馬車,以此來作為一種反抗。當德法奇為革命進程的緩慢而感到灰心喪氣時,德法奇太太的耐心和遠見使德法奇自愧不如而附和她的決心。她清楚地明白“仇恨和報應需要時間;這是規則……盡管革命需要很長時間,但是革命即將到來……革命熱情不會消退,也不會停止……革命的步伐總是在前進…… 我一心相信,我們將看到革命的勝利。”[3]聽到這些,德法奇“像個在老師面前溫順而專心的小學生,微微低頭在她面前,”[3]同時大聲夸贊道:“一個了不起的女人,一個強悍的女人,一個偉大的女人,一個非常偉大的女人!”[3]因此,在革命爆發前,狄更斯欣賞德法奇太太非凡的勇氣,堅強的個性,過人的智慧以及非凡的領導和組織的能力。
隨著革命進程加快,德法奇太太變得越來越殘忍和惡毒。“釋放一只老虎和一個惡魔。”[2]她叫嚷道,而當她將一把裝好子彈的手槍藏在胸前,一炳鋒利的匕首藏于腰間準備復仇的時候,老虎和惡魔正是她的化身了。德法奇作為領導者的角色很快被德法奇太太取代,她一言不發而警惕地編織物此時變為了恐怖的中心載體。
德法奇太太不再是一個“從童年時代起就被滲透了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公正感和對一個階級懷有根深蒂固的仇恨的女人,一旦機遇來臨,她就變為了一只母老虎。她已沒有了任何憐憫之情。”[3]比如,在謀殺巴士底獄的總督De Launay的事件中,狄更斯將德法奇太太描述為一個冷血和惡毒的魔鬼。在對德法奇太太后來的描寫中,狄更斯甚至控訴她如此“瘋狂的行為”。狄更斯認為她殘忍野蠻,她的行為違背了道德準則。在1789年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遠在安托內,一陣喧鬧從一群人中涌起,赤裸的手臂像冬天寒風中的樹干一樣揮舞著。每個人都手握著武器:手槍、樹干、鐵棒、刀子、斧頭以及其他任何可以用來當作武器的東西。而當時,德法奇太太正走在許多女人的前面,她呼喊道:“這個地方被占領后我們就可以殺死他們了。”[4]德法奇太太成為了一個無情的復仇者,她的心腸在飽受苦難火焰的煎熬中變得無比堅硬,不帶一點同情心。
3 德法奇太太作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
18世紀的法國,女性雖然在公共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女性地位極低。科林·瓊斯在闡述法國大革命期間女性地位時,詳細探討了當時女性的不平等地位。“雅各賓派把女性俱樂部視為左翼組織,主張女性應該留在家中培養有教養的愛國者。拿破侖認可這一觀點,并在《法典》中將女性歸于次要地位。”[5]1789年的《人權宣言》表面標榜著人人平等,但在現實中女性權利卻被排除在男性權利之外,所謂的人人平等只限于男性,法律政治和經濟知識男人的領域,與女人無關,女人只限于性貞潔,服從和撫育子女的私人領域。18世紀末制定的為遭到毆打、遺棄的婦女改善法律地位的自由離婚法,以對女性不利的方式加以修訂。
德法奇太太作為一名當時底層階級的女性,受到雙重壓迫。一方面,德法奇太太出生于社會地位最底層的佃戶人家,另一方面,德法奇太太生活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時期,因此,她不可避免地受到雙重壓迫。一個人所受的壓迫越大,他的逆反心理就會更強烈,反叛手段也會更為殘忍;并且革命推翻壓迫階級以后,新的統治階級同樣會采取不公正的手段對待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變為了壓迫者。德法奇太太作為一名受到雙重壓迫的女性,卑微的社會地位以及內心對貴族階級的仇恨使她走上復仇之路。當革命爆發,她變為了一個野蠻的禽獸,不惜一切走上復仇之路。她殘忍到甚至意欲謀殺無辜的露西。從這一方面看,德法奇太太成為了她手下受害者的壓迫者。
德法奇太太出生于一個佃戶人家,她的姐姐被玷污,家人遭到迫害;她在童年時就失去了她的父親、哥哥、姐姐以及姐夫。她的姐姐被強奸后被折磨致死,她的哥哥被埃德蒙兄弟中的弟弟殺害。不幸的童年使德法奇太太精神上遭受巨大創傷。她出生在社會等級中的最底層,她的家人是受到貴族階級壓迫的普通民眾。她對埃德蒙兄弟有著不可調解的仇恨,因此,她決心為她家人報仇。
無辜的人比如曼內特醫生和露西差點成為她殘暴行動下的受害者。當德法奇太太前往曼內特的住所,意欲殺害露西和她的女兒時,狄更斯通過多次重復“靜靜地,德法奇太太沿著街道,越來越靠近”[3]的措辭,渲染緊張和恐怖的氣氛,以此來暗示德法奇太太已然成為一臺機器,一心只想為她姐姐的悲慘遭遇報仇雪恨。這種恐怖氣氛的描述為讀者對于后來德法奇太太對曼內特、露西和露西的孩子的仇恨預先做好了心理準備。當德法奇對曼內特家庭表現出仁慈之心,想要把露西和曼內特醫生從特雷澤定罪中拯救出來時,德法奇太太仍然頑固地決心殺害曼內特醫生和露西,此時的德法奇太太已然成了一個禽獸般的角色。德法奇太太不能將達奈和他侯爵叔叔兩類人區分開來,正如侯爵不能將底層階級的人看作是有自身價值的個體區分開來一樣。他們都僅僅以階級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人,只是機械地將周圍的人歸結為不同的階級。最后,德法奇太太成為了一名迫害無辜者的壓迫者。作為一名出生于社會底層階級的女性,德法奇太太由一名受壓迫者向壓迫者身份的轉換正是由于雙重壓迫的結果。
4 德法奇太太作為受害者和加害人
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愛爾維修倫理學認為,人是一個能夠感受外物作用的有機體,趨樂避苦和自愛利己是人的永恒本性,人的所有欲望、感情和精神都來自自愛心。愛爾維修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認為利益是判斷道德的標準,利益不僅決定人的道德觀念,也決定人對道德行為的評價。他斷言:“無論在道德上或認識問題上,都只是利益宰制著我們的一切判斷。個人利益決定著個人的道德判斷,社會利益決定著社會的道德判斷。”[6]他認為人的本性談不上善惡,它是后天的產物,是由于環境和教育的結果。“我們在人與人之間所見到的精神上的差異,是由于他們所處的不同環境,由于他們所受的不同教育所致。”[6]他提出了“人是環境的產物”或“人的觀念是環境的產物”的著名命題。
根據愛爾維修利己本性的觀點,不論是作為受害者時領導受壓迫民眾起義反抗的德法奇太太,還是作為加害人時無情殺害無辜敵對階級的德法奇太太,都是由于人趨樂避苦和自愛利己的本性所致。作為社會的底層階級,德法奇太太的家人受到貴族階級的殘酷迫害。因此,德法奇太太領導受壓迫的底層人民奮起反抗,成為革命階級。然而,她錯誤地將所有貴族階級歸為敵人,不加區分地視整個貴族階級為敵對方。她甚至意欲殺害無辜者達奈。暴亂發生時,她變成了一頭嗜血的野獸,領導婦女們反抗統治階級,毫不留情且不加區分地將貴族階級的頭砍下。不論是同情貧苦民眾的“善”的德法奇太太,還是殘忍復仇的“惡”的德法奇太太,都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
德法奇太太是埃德蒙兄弟罪惡事件的受害者。她的家人受到埃德蒙兄弟的迫害。仇恨深深地根植于她內心,在她成長過程中,她不惜一切地想要復仇,即便她的復仇行動過于極端,并且她的復仇行動意味著給像達奈,馬奈特醫生和露西這樣無辜的人帶來傷害。因此,當暴亂發生,德法奇太太復仇的機會來臨時,她甚至意欲殺害馬奈特醫生和露西。此時她由一個受害者變為了一個加害者。
作為一個埃德蒙兄弟罪行的受害者,德法奇太太從小就對貴族階級懷有極大的仇恨。對貴族階級強烈的仇恨一直伴隨著她,這種仇恨滲透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不知疲倦地將她意圖復仇的目標人物的名字編織在她無時無刻不在編織的編織物里。她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記錄貴族階級的罪惡:“她以她自己獨特的針法和符號編織著,這些符號對她來說再清楚不過了……相比消除德法奇太太編織的標記名字上的一個字母,一個活在世上最懦弱的膽小鬼結束自己的生命要容易得多。”[3]
在某種程度上,盡管編織在記錄貴族階級的罪行上是很好的方式,但是德法奇太太卻因此變成了一個機器般的人物,一心只想報仇雪恨。她心中飽含仇恨,一心將復仇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因此她是當時社會的受害者。在德法奇太太成長為一個成年人的過程中,她的家庭悲劇對她個性的形成與塑造有很大影響。在小說的最后章節中,雖然德法奇太太在斬首她的敵人中獲得樂趣,雖然她復仇的欲望得到滿足,她仍然是當時社會的受害者,因為她性格的悲劇是當時時代環境的產物。
由于德法奇太太不幸的童年遭遇,當她長大,她的個性體現了革命的性質;暴力和仇恨交織,在她心中沸騰,她等待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就算她的行為意味著給無辜者帶來災難,她一心想要革命的真正目的是報復達奈。“決不!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謝天謝地我可以來這兒阻止你——我會阻止你!”[3]德法奇太太說,“畜生,別擋我的路,否則我會將你碎尸萬段。”[3]一步步地,德法奇太太轉換成了另一重身份,即,一個加害人。
小說通過對于洛內,弗隆和后來弗隆女婿可怕而又生動的慘死以及德法奇太太對此幸災樂禍場面的描寫,革命暴力和恐怖的一面進一步突顯。在描述一群人追蹤洛內的腳步的情景時,狄更斯將德法奇太太刻畫為冷酷無情的形象,她與他保持著“固定的近距離”(狄更斯重復了五次這個短語),以便當洛內被打倒時她可以第一個砍下他的頭顱。當群眾們抓捕住監獄長,并押著他進行判決時,德法奇太太走在這位失意的監獄長旁邊。當監獄長被人從后面突襲,倒地而死時,德法奇太太用腳踩在他的脖子上,并毫不猶豫地砍下了他的腦袋。從德法奇太太毫不留情地砍下監獄長腦袋這一行為可以看出,德法奇太太變為了一個殘忍惡毒,冷酷無情,心胸狹隘的加害人。因此,德法奇太太作為受害者和加害人的雙重身份正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
5 結語
國內外對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做過大量研究,評論家們對于德法奇太太的形象也有著各自不同的見解。本文通過實例分析,揭示了德法奇太太是一個具有雙重身份的人物,她不能被簡單地貼上好或惡的標簽。她有雙重身份:她既是一個勇敢的女英雄,又是一個惡毒的復仇者;她既是一個被壓迫者又是一個復仇者;她既是一個受害者又是一個加害人。
德法奇太太身份的逐步轉變是隨著革命推進和社會條件演化的結果。盡管在小說的前部分,德法奇太太同情被壓迫者,并且她被刻畫為一個勇敢的女英雄,她也不能被簡單地貼標簽為一個仁慈的女人。同樣地,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德法奇太太被刻畫為一個一心只想滿足她復仇欲望的禽獸般的女人,她也不能被簡單地貼標簽為一個惡毒的女人。
卡爾·馬克思稱,“人類道德,文化和宗教價值觀不是由任何與生俱來的善惡觀念引起的,而是在一個特定系統的需求下形成的。”[7]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惡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缺陷,而是腐朽社會的產物。此外,社會對個人性格的形成有塑造性影響。德法奇太太的性格特征,不論好的特質還是惡的特質,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她個人的意志。不管是作為一個勇敢的女英雄還是作為一個惡毒的復仇者,不管是作為一個被壓迫者還是一個壓迫者,不管是作為一個受害者還是一個加害人,德法奇太太的身份和個性都受制于她所在的社會和特定的歷史時期。因此,我們可以做出結論,正像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一樣,德法奇太太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惡的一面,她既不是絕對的善,也不是絕對的惡。
作者狄更斯也注意到,德法奇太太的惡并不是她與生俱來的缺陷,這種惡是由于貴族階級的壓迫和她所遭遇到的個人悲劇造成的。正像貴族階級的壓迫使德法奇太太成為了一個被壓迫者一樣,德法奇太太的壓迫也使她成為了她手下受害者的壓迫者。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應承認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比如,狄更斯對于德法奇太太的觀點并不是完全正確的。當狄更斯對德法奇太太做出評價時,他僅僅將眼光集中在社會道德和人道主義層面上,他并沒有關心其他方面比如社會大背景對德法奇太太性格造成的影響。
[1]高廣孚.杜威教育思想[M].密歇根:水牛圖書,1976.
[2]Dewey,John.Human Nature and Conduct[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2.
[3](英)查爾斯·狄更斯.雙城記[M].王 勛,紀 飛,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2009.
[4]何 畏.從《雙城記》看狄根斯的人道主義思想[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03.
[5]科林·瓊斯.劍橋插圖法國史[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6]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十八世紀法國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7]Wood.W.Allen.Karl Marx[M].London:Routledge,2012.
(責任校對 王小飛)
I106
A
1674-5884(2014)04-0145-04
2014-01-21
董 梅(1989-),女,湖南益陽人,碩士生,主要從事外國語言文學(英美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