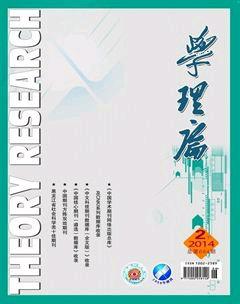國內對發展主義的研究進展
張瑾
摘 要:產生于西方工業文明時期的發展主義強調經濟增長,忽視人、社會、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協調發展,進入后工業文明時期眾多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發展主義在中國既占據神壇之位又飽受質疑。通過梳理目前國內相關研究的類別和進展,提出國內對發展主義研究存在界定模糊、結合國內發展理論不足、國家發展戰略分析和社會變遷闡釋不夠深入等問題,但以發展主義學說研究農村社會的視角具有開創性意義,值得深入探索。
關鍵詞:發展主義;發展研究;國家;社會;農村研究
中圖分類號:C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6-0042-03
20世紀90年代國際上同時興起三大浪潮:新自由主義、對發展的反思和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棄置二戰后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角色,開啟了市場主導經濟政治發展的新篇章,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家中的勝利。當強調“市場萬歲”的新自由主義突破國家和政治的界限時,就出現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化的全球化。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全球化,抑或是它們取而代之的強調國家作用的各種理論學說,唯一不變的就是“發展”這個宗旨。發展被神圣化、信仰化,甚至成為一種“主義”,被奉為人類生存的圭臬。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統統是發展的代稱,GDP、資本、利潤全部是發展的符號,而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人性異化卻無疑成為發展的代價。因此,在各國紛紛追求高速發展之際,西方一些學者踏上了反思發展的征程。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主義愈加現形,經濟迅猛發展,精神文明遠遠滯后、生態環境日漸破壞。在西方社會開始反思發展的影響下,國內學者也開始審視中國發展中遇到的社會問題。本文旨在對相關研究進行梳理,以更好把握國內對發展主義的研究進展。
一、發展主義的概念界定
早在1999年《讀書》雜志刊登了許寶強《發展主義的迷思》一文,這是國內最先涉及發展主義概念的文章。“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信念。”[1]將發展主義定義為一種意識形態,他指出發展主義是源于西方特定時期經濟增長產生的思維定式,它忽視了復雜的文化、社群及偶然性因素,排斥了本土人們的生計與文化實踐,將發展鎖定在工業、技術與生產上。
《當代西方社會發展理論新詞典》對發展主義的解釋為“特指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一種經濟發展思想。1949年拉美經委會領導人普雷維什發表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重要論著,為發展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2]這一解釋追溯了“發展主義”這一術語最初正式使用在何種語境下,這一語境即六七十年代拉美諸國在普雷維什“中心—外圍”理論下采取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葉敬忠等在《發展主義研究評述》中把發展主義劃分為拉美型、東亞型和西方型三類,這一概念代表拉美型發展主義[3]。
黃平在《關于“發展主義”的筆記》中談了“23點”,思考了西方中心論、經濟增長論、線性進步觀等理論問題和失業與勞動力市場、資源、人口、貧困等社會問題[4]。在這一基礎上,他給出了定義:“發展主義嚴格地說應該是‘開發主義,指的是一種源起于西歐北美特定的制度環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擴張成為一種為國際組織所鼓吹、為后發社會所尊奉的現代性話語和意識形態。”[5]這一界定體現了發展主義的行動性、實踐性,國家和地區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都是在“開發主義”思想指導下完成的。
周穗明認為發展主義“是繼戰后‘馬歇爾計劃之后西方陣營的第三世界發展戰略,也是包括‘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以及種種關于高科技、工業化、國家干預或市場機制等不同版本的發展學說的總稱。”[6]這里涵蓋發展理論、發展主義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論。并且他通過比較發展主義與新發展主義,指出發展主義在哲學、理論、觀念等層面存在的種種缺陷,提出發展應尊重文化差異、堅持多元文化主義,走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另類發展道路。
雷龍乾從哲學層面描述了發展主義的特征,認為“人本主義或人本主義強調以人為本的實踐價值觀,是發展主義哲學的價值旨歸;理性主義或科學主義追求認識的客觀有效性,是發展主義哲學的思維原則;而經濟主義或資本主義反映經濟發展、資本增值的自發機理,促成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精神氣質和文化格局。”[7]這一對發展主義形而上學的理解為反思發展主義的哲學層面提供了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盡管學者對發展主義的理解有幾點認同:源于西方工業化,是特定時期的產物;把經濟增長奉為社會進步的標尺;有多種學說;“新發展主義”是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和解構。但因涉及領域之廣,其概念仍相對模糊。只有對概念認識上統一,才能深入研究理論問題。
二、對發展主義的理論研究
劉森林和陳向義探討了馬克思主義與發展主義的關系。二者對馬克思主義是否屬于發展主義有不同的觀點,但對當今發展主義帶來的社會問題具有共識。劉森林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代替“弱發展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重建發展理念的新方案[8];陳向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不會導致發展主義的實踐的”,但“當前中國也確實存在著朝向發展主義的趨勢”,因此他強調要堅定落實科學發展觀,避免真正陷入發展主義的陷阱[9]。
相較于劉森林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張光君和彭新武走得更遠。張光君認為,唯發展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增長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也將發展等同于進步,仍然沉醉于人類中心主義和技術樂觀主義不能自拔,實質上仍然是一種欠缺全面性、協調性和科學性的發展模式”[10][11]。彭新武不僅指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弊病,而且提出建議一種以“人—自然”系統為基礎的生態文明價值觀,“在這種文明觀念中,人類真正積極的生存方式的首要特征應是基于自然整體及其生態平衡尊重的可持續性,而不是物質財富的無限增長”[12]。
從發展的價值目標角度質疑發展話語,鄧萬春指出“發展主義傾向則把財富的增長看作衡量發展的基本尺度……其結果就是隔斷經濟增長與文化、社會和政治的聯系,使發展的價值功利化、物化”。因而批判發展主義重要的是正確定位發展的價值目標,只有在“尊重、自由、公正、以人為本等更為全面、深層的價值訴求”下才能更好地引領發展實踐[13]。
上述學者關于馬克思主義、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與發展主義之間的關系的論述對探索中國發展理論、警惕西方發展主義理論侵蝕具有重要意義。但當前理論探索處于起步階段,理論分析的現實性仍不夠突出。
三、對發展主義的國家戰略研究
我國的發展要警惕西方權力的滲入,因此要認真對待地方與權力關系的問題。本土知識是“一種可以通過‘徹底解釋獲得的可以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知識”;權力問題也不是簡單的“支配—抵抗”,而是具有多樣關系的發展干預綜合體[14]。此外,在有限時空內尋求快速發展使我國面臨很多困境。西方社會經歷了現代取代傳統、后現代超越現代的自然發展過程,而我國的發展是在有限的時空環境內容納了西方社會兩個世紀的社會變遷,加之內部人口眾多、外部國際資本主義的擴張,我國的時空條件受到嚴重的擠壓。認識到“時空壓縮”的現實性才能找到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超越進化”或許是應對困境的出路[15]。
郁建興等人認為我國是發展主義、經濟國家主義、地方政商合作和國家合作主義的綜合體,而重構國家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超越現今的發展型國家模式是新世紀的要求[16]。碎片化、二元化的社會政策體系急需轉型,他強調通過政策轉型實現國家發展模式轉型[17]。李學文等人則追溯了國家發展、稅收制度與地方政府收入的政策演變及三者間的互動關系,指出將土地作為發展主義核心要素的經濟增長模式取得了顯著經濟成績,但也帶來了種種社會問題[18]。該文章在針對農村土地的社會斗爭、抵抗行動層出不窮的當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發展、另一種發展與發展之外》一文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發展模式進行了反思。文章指出,撤點并校并非發揮教育的功能,是規模、效益等經濟學考慮,是發展主義的邏輯在作祟;中國成為高端奢侈品的消費大國是發展戰略中經濟增長高于一切的原則所致[19]。發展主義在中國已經現其原型,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警惕,更要尋求發展之外的本土模式。
分析國家戰略的發展主義文章傾向于論述中國模式和國家轉型。快速工業化、高速現代化使國內的發展也進入了瓶頸期,探討國家轉型、尋求突破唯經濟論的發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當前的研究仍較為宏觀和淺顯,指導國家如何轉型、如何包容性發展的建議將成為未來的研究方向。
四、對發展主義的社會變遷研究
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有助于扭轉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國家公共治理體制,從未實現對當前發展主義模式的突破。當前的任務不僅是要突破發展模式,而且要在公共治理體制取得創新性進展,因此需要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以達到真正解放思想、尋求發展新出路的目標[20]。何子英追溯了西方福利國家的起源與形成,指出盡管社會結構、歷史背景存在差異,我國不能照搬西方福利國家模式,但我們要積極學習“福利主義共識”,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間尋求平衡點,實現國家發展模式的真正轉型[21]。
早期的發展主義是“高積累、低消費”,而發展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必將呈現消費主義的特征。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發展是“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戰略,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全球化下消費主義沖擊,形成一個發展主義與消費主義的二元悖論[22]。高積累與高消費并存的讓我國的發展局面更加復雜化。
關注發展中的社會成員是研究社會變遷的另一視角。鄧萬春探討了國家社會動員能力的變化,認為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后,國家對資源控制能力下降導致社會動員的實際能力減弱;然而在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主義倡導下,社會動員逐漸向效率優先的方向發展[23]。鄭杭生則對社會成員是否“有感發展”進行了研究,指出當前國家社會的格局是“國富民弱”“無感增長”,所謂的快發展、高增長都是“發展的幻象”,發展的成果并沒有惠及普通百姓。要實現廣大人民“有感增長”,必須突破舊式現代性的發展主義,尋求一種以人為本、民生為重的“新型現代性”理論范式[24]。
無論是公眾參與、消費主義還是社會動員“有感增長”,所有這些對社會變遷的研究都指明一點:人民是發展的主體,也是發展的目的;發展主義也許能帶來一時的“幻象”,但不會帶來永恒的利益,只有關注人們生活的發展才能可持續。當前對社會層面的發展主義分析不夠深入、力度不足,這一方向的研究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五、對發展主義的農村問題研究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農村改革不是單純的制度變遷而是帶有濃厚的社會動員色彩,是一種繼承于毛時代的“國家動員式發展主義”[25]。但當今我國農村經過公社化、集體化和三十多年改革洗禮已經不是概念意義上與“現代”相對的“傳統”狀態,而是一種復雜的、混合的不發達狀態。當前的新農村建設應該既包含現代化的發展主義話語,也包含后現代化的反思、批判話語。只有這樣才能既實現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產業化、農民增收,又保證農村社會文化、傳統價值等地方性知識的保留、傳承與發揚[26]。
潘澤全研究了發展主義道路下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狀態問題,中國現代化戰略下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表現出對農民工群體的排斥和抗拒[27]。農民工社會政策調整發生在城鄉二元結構框架中,而這一政策體現的是國家城市空間保護的理性邏輯和現代城市主義的發展主義邏輯,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社會排斥和不平等待遇。關注發展主義語境中弱勢群體能否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項重大議題,對保證國家持續發展、促進社會良性運轉以及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8][29]。
葉敬忠對發展主義侵蝕農村社會的思考也充分體現了人文主義關懷。“被上樓”農民、失地農民“失去庭院的農村”,所有這些景象都是發展主義的惡果[30]。農村中小學“撤點并校”的始作俑者亦是發展主義,所謂“村不辦小學、鄉不辦中學”的規劃,正是以調整表征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策略。其結果不是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是農村家庭教育負擔的加重、交通安全隱患的增加和輟學兒童的增多[31]。
朱曉陽通過對滇池東岸某村莊的田野研究,論述了更為復雜的農民、國家與發展主義間的關系。他認為發展主義是當前中國的核心價值觀,無論是國家還是農民都接受了這種價值觀,成了“發展主義的囊中物”。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是抵抗而是“更激進”地推進,他們并沒有堅持所謂的“傳統”,而是與政府協力共同打造發展主義知識話語,為的是“從這些政治和經濟的生態約束中獲得更多的土地、水利、糧食和能降低生存風險的空間”。并警惕在關注發展主義帶來的生態惡化時,不能忽視農民的參與行動[32]。
反思發展、批判發展主義是大多數學者以發展主義視角研究中國問題的出發點。發展主義不是普世理論,它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經驗。走出歷史、面對現實,非西方國家面臨的“發展問題”并不是走當今發達國家的老路子,而是回歸自我、尊重民眾。正如埃斯科瓦爾在其《遭遇發展》一書中所說,文化差異才是我們這個時代關鍵的政治實事之一;我們尋求的是基于本土的發展“替代方案”;我們追求的是一個五彩斑斕的、充斥混雜文化的后發展時代。中國的農村、農民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識、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有權利掌握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當前的生存狀態,任何地區、任何個人都不應該成為發展主義的犧牲品。面對強大的發展主義浪潮,學者的反思與批判看似蒼白無力,也許真正能夠對抗這頭怪獸的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那些源于鄉土、發于底層的草根運動可能會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
參考文獻:
[1]許寶強.發展主義的迷思[J].讀書,1999(07):18-24.
[2]龐元正,丁冬紅.當代西方社會發展理論新詞典[M].長春:吉林出版社,2001(10).
[3]葉敬忠,孫睿昕.發展主義研究評述[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2):57-65.
[4]黃平.關于“發展主義”的筆記[J].天涯,2000(01):37-39.
[5]黃平.發展主義在中國[J].科學中國人,2003(09):50-52.
[6]周穗明.西方新發展主義理論述評[J].國外社會科學,2003,(05):44-52.
[7]雷龍乾.西方發展主義哲學的緣起與發展[C].第五期中國現代化研究論壇論文集,2007.
[8]劉森林.透視唯物史觀中的發展主義[J].河北學刊,2005(03):111-115.
[9]陳向義.馬克思主義與發展主義的關系探析[J].哲學研究,2007(05):15-18.
[10]張光君.唯發展主義的思想迷誤與邏輯悖謬[J].前沿,2010(19):147-154.
[11]張光君.唯發展主義再批判[J].理論月刊,2009,(06):38-42.
[12]彭新武.“可持續發展”的合理定位[J].社會科學研究,2002(02):35-40.
[13]鄧萬春.發展的價值目標批判及新趨向[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4):1-5.
[14]朱曉陽,譚穎.對中國“發展”和“發展干預”研究的反思[J].社會學研究,2010(04):175-198,245-246.
[15]景天魁.社會發展的時空結構[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16]郁建興,石德金.超越發展型國家與中國的國家轉型[J].學術月刊,2008(04):5-12.
[17]郁建興,何子英.走向社會政策時代:從發展主義到發展型社會政策體系建設[J].社會科學,2010(7):19-26,187-188.
[18]李學文,盧新海.地方政府與預算外收入: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問題[J].世界經濟,2012(08):134-160.
[19]葉敬忠.發展、另一種發展與發展之外[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1):5-8.
[20]郁建興.解放思想才能構建和諧社會[J].哲學研究,2008(05):3-9,127.
[21]何子英.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模式及其對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啟示[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02):160-169.
[22]申端鋒.發展主義與消費主義的二元悖論[J].讀書,2006(06):23-26.
[23]鄧萬春.社會動員:能力與方向[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1):65-72.
[24]鄭杭生,黃家亮.從社會成員“無感增長”轉向“有感發展”——中國社會轉型新命題及其破解[J].社會科學家,2012(01):7-11.
[25]鄧萬春.制度變遷,還是動員式改革——社會動員視野下的中國農村改革反思[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1):5-10.
[26]鄧萬春,景天魁.現代化與后現代化:雙重的新農村建設[J].探索,2012(01):142-146.
[27]潘澤泉.現代化與發展主義語境中的農民工發展困境[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5):42-48.
[28]潘澤泉.中國農民工社會政策調整的實踐邏輯——秩序理性、結構性不平等與政策轉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05):55-66.
[29]潘澤泉.國家調整農民工政策的過程分析: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J].理論與改革,2008(05):59-61.
[30]葉敬忠.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社會宏觀背景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4):5-21.
[31]葉敬忠,孟英華.土地增減掛鉤及其發展主義邏輯[J].農業經濟問題,2012(10):43-50,111.
[32]朱曉陽.黑地·病地·失地——滇池小村的地志與斯科特進路的問題[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2):2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