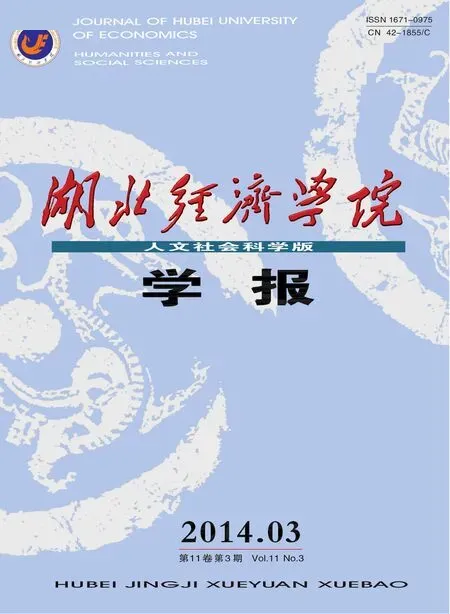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文化整合問題的研究
楊西春
(梧州學院 工商管理系,廣西 梧州 543002)
一、引言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舉世矚目,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以后,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我國企業為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參與更廣泛的國際競爭,將跨國并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開展了一系列大手筆的跨國并購活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比較典型的案例有:2004年1月TCL收購了法國湯姆遜公司(Thomson)的電視業務,2004年12月,聯想宣布并購IBM的全球PC業務,2010年3月,吉利集團以18億美元收購福特旗下的沃爾沃轎車100%的股權以及相關資產,2012年12月,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151億美元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然而,不得不承認,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之路充滿坎坷,失敗的案例層出不窮。總的來看,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水平不高,跨國并購整合的能力也比較低,跨國并購活動中正遭文化沖突的嚴峻挑戰。
二、我國企業在跨國并購活動中的文化沖突表現
(一)國家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
不同的民族文化撫育了不同的民族群體,并造就了其成員特定的價值取向。因此,企業文化往往會被國家和民族文化特色打上鮮明的烙印。國家與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必然會帶來企業文化層面的巨大差異。Weber(1996)等認為,民族文化的差異是決定企業跨國并購后整合能否成功的關鍵變量。我國長期受封建統治思想的影響,在民族文化上不僅強調上下有別、尊卑有序,而且還注重維護上級的絕對權威,強調執行力,推崇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有著極強的領袖崇拜及森嚴的等級觀念,從而形成了比較鮮明的集權式的層級管理制度,體現的主要是“人治”[1]。而歐美等西方國家強調理性思維,崇尚競爭,講求效率,強調人人平等,強調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實行的往往是分權式的管理模式。在TCL并購法國湯姆遜電視和阿爾卡特的手機部門后,由于法方的管理者和員工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文化認同感缺乏,無法爭取理解二者的差異,最終導致雙方的業務整合無法有序開展[2]。
(二)企業文化方面的偏見和差異
中外企業成長經歷和外部環境各不相同,作為一種亞文化的企業文化之間必然有很大的差異。來自不同母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者和員工,往往都不愿或者難以接受“他文化”。我國企業并購的多為歐美成熟企業,它們通常都具有較長的發展歷史,形成的企業文化在員工層面的認同度比較高。而這些員工對我國企業的形象往往存在偏見,固執地以為廉價的產品和落后的管理就是我國企業的群像。于是,一旦我國企業收購了這些公司,它們的員工便會對我國企業通常普遍持一種懷疑的態度和偏見,甚至會聯合工會、媒體、投資者等對我國企業在海外的并購行為進行聯合抵制。我國企業文化缺乏國際認同度,處于劣勢地位。尤其是,國內企業的一些習慣性做法,在國外通常是不被接受的。例如,TCL收購湯姆遜之后,又一次在公司內召開部門經理會議,在會議的座位安排上,依照國內慣例業績好的部門代表自然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而業績不好的部門代表則被安排在了靠后的位置,沒想到,此舉最后被湯姆遜指責為“土匪文化”[3]。
(三)管理方式上的差異
歐美等發達國家企業追求的是制度效益,強調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因此,在管理上十分注重制度、規范、調理的建設與有效執行,人們也以遵守法律和規章為榮,從而實現了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如工作崗位的職務分析、績效的考核等都有完整的書面形式和方案。我國企業制度建設不完善,往往是武斷的“一言堂”式的領導風格,管理者長官意志比較濃厚,主觀隨意性很強,過于看重人情,執行制度時過于靈活而缺乏嚴謹的作風,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4]。比如,在國內企業,員工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邊界并不清晰,這樣導致加班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而在國外,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十分強調尊重員工的個人生活,關注員工的工作情緒,基本上不存在加班現象。據說,在并購湯姆遜的初期,TCL的董事長李東升就曾經遭遇到這樣的事情:他計劃在周六召開董事局會議,便在周五晚上趕到法國。而在法國的文化中,周末是休息的日子,而工作是永遠不能打擾員工的私生活的。李東升到了法國之后才發現法方董事會的人員手機全部關機,根本就找不到他們的人。
(四)人事制度方面的差異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遵循“以人為本、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在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上,強調政治素質、個人資歷、人際關系,注重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在薪酬方面偏重于考察企業員工的資歷、經歷和學歷,缺乏科學的工作分析、職位設計、績效管理等評估體系,沒有形成科學規范的薪酬體系。而歐美企業奉行嚴格、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在人才選拔和任用時,有較為嚴格明確的職責、職權、職務解析,往往把“能力”放在第一位,量才使用,能夠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在薪酬方面,歐美企業與從事的工作性質相掛鉤,當員工工作職位發生變化時,其報酬亦會相應及時予以調整[5]。
三、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文化整合的策略選擇
(一)做好文化評估,重視文化差異
我國企業跨國并購過程中,并購雙方往往主要調查研究財務、法律和運作等因素,只花比較少的時間和精力處理文化差異問題,而導致并購失敗的原因很可能恰恰就是并購雙方忽視的無法融合的企業文化差異。在跨國并購行為中,并購雙方其實不僅存在著企業文化的差異,而且還將面臨著迥異的民族文化。因此,我國企業在開始并購的準備過程中,必須要對被并購方的歷史、文化和傳統進行詳細調查了解。不僅要從企業文化層面了解并購對象與自己的差異,還要了解東道國與本國在價值觀等方面存在什么異同之處,使企業了解并購可能產生的主要沖突和負面影響,加大整合成功的可能性,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6]。思科公司在并購中,就曾在并購團隊中安排有“文化警察”這一職位,由其專門負責對并購對象的企業文化進行調查,評估思科文化與其兼容的可能性。如果發現雙方文化不能兼容,就會毫不猶豫地放棄。被譽為全球第一“CEO”的杰克·韋爾奇,在決定并購前優先考慮并購雙方的文化能否融合,如果差異太大,就迅速放棄。思科和通用的做法值得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時借鑒。
(二)主動吸收國外的先進企業文化,進行整合創新
當前,我國企業進行跨國并購的多數是在歐美國家具有較長發展歷史、文化底蘊十分深厚和成熟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員工也在過去的工作中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企業文化形成了較高的認同度和自豪感。如吉利并購“沃爾沃”時,吉利僅有13年的歷史,“沃爾沃”卻有83年的歷史;聯想并購IBM的全球PC業務時,聯想只有20年的歷史,IBM具有上百年的歷史;具有這樣悠久歷史的企業文化必有其優質的一面,因此,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時一定要以大局為重,尊重對方的文化,容忍對方企業不同文化的存在,并注意吸收國外企業文化中的先進因素,通過提升和完善自身的企業文化來促成文化的“同化”,做到中西合璧,優勢互補,互相整合,提煉創新,不能盲目自大,推行“文化強勢”[7]。臺灣明基收購德國西門子手機業務后,向西門子手機業務部門灌輸明基文化,形成文化輸入,但在西門子相對強勢的企業文化影響之下,并購活動最終以失敗告終。
(三)建設一支文化整合能力突出的團隊
對于被并購方來說,并購行為是一場大變革,在企業中會引起較大的震動。要想實現文化整合,盡快消除并購后的文化真空現象,首當其沖的就是必須建設一支具文化整合能力突出的團隊。具體來講,可以考慮選擇一些符合企業文化整合要求、可以領導兩個企業員工的人在新公司擔任重要職位,建立具有一支國際視野,掌握國際管理經驗,擁有的文化整合能力的高級人才隊伍管理新的全球化企業。如果國內缺乏具有國際化思維和膽識的人才,不妨考慮從國外聘請。我國企業在跨國并購初期,可以考慮保留被并購企業高層經理,既有利于整合工作的開展和企業經營的正常進行,又有利于保持人心的穩定。麥肯錫公司的一項調查發現,有將近85%的并購方在當時留用了并購前的原主管[8]。如聯想任命原IBM的副總裁沃德為新公司的CEO,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國際化管理團隊,應該說是一種非常成功的做法。
(四)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
跨國并購的雙方來自于不同國家,它們不僅面臨著企業文化的沖突,還會面臨著不同國家文化的差異,雙方員工的價值觀肯定難以完全同化,因此跨文化溝通是跨國并購文化整合的重要環節。通過有效的溝通活動,可以幫助雙方充分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和感情因素,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處。我國企業在跨國并購后要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可以通過開通網絡論壇、進行不定期的面談、舉辦討論會、主題party等方式,搭建企業與員工、員工與管理人員,以及員工與員工之間的溝通平臺,方便他們在價值觀、情感、管理方式、經營信息等方面進行有效溝通,增強了解和新人,促使并購雙方員工對新企業文化的認同,從而為新企業建立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提高團隊的協作能力和凝聚力。
(五)加強跨文化培訓
培訓是實現跨文化整合的基本手段,能夠促使并購企業正確認識彼此之間的國家文化和企業文化,消除雙方因為文化差異而造成的障礙和沖突,有效推動新企業的文化整合。關于跨文化培訓的內容可以設定為:語言學習、文化認識、文化敏感性訓練、跨文化溝通、文化沖突處理等。關于跨文化培訓的執行可以選擇外包給專業的培訓機構,如培訓咨詢企業或者大學,也可以選擇由企業的內部培訓機構來執行[9]。此外,企業還可以考慮通過設立公司內部網站,專門向員工介紹并購雙方的國家和民族文化,并提供有關經營文化課程等。
[1]魯俊杰,劉釗.跨國并購文化整合障礙與對策[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2,(3):26-27.
[2]段世佳.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文化整合的若干思考 [J].現代商業,2008,(17):81.
[3]馮鵬程,馬曼.從TCL并購看企業海外并購文化整合[J].我國外資,2010,(3):49-50.
[4]徐永超.淺談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文化整合[J].時代金融,2011,(9):114.
[5]單寶.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文化整合模式及路徑選擇[J].統計與決策,2008,(5):165.
[6]王國平.我國跨國并購企業文化整合策略 [J].企業活力,2009,(10):56-57.
[7] 李征征.企業海外并購中文化整合問題研究[J].才智,2011,(5):34.
[8]宋亞非.跨國并購中文化整合視角的研究與借鑒[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67-68.
[9]李曉燕.我國企業跨國并購中的文化整合策略研究[J].China’s Foreign Trade,2010,(2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