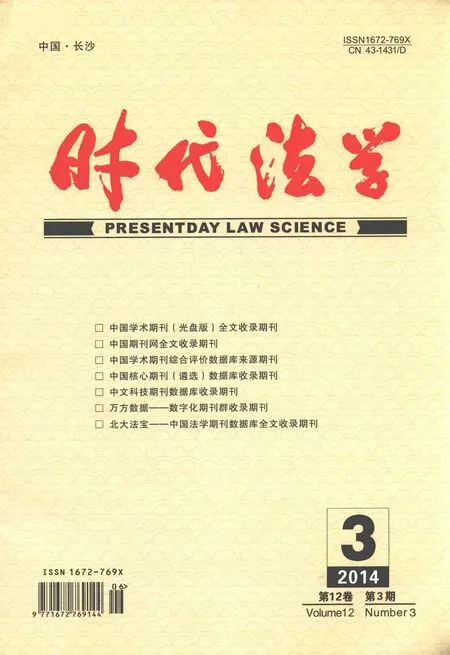三官立而政體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舉
——康有為司法理念評議*
江玉橋,謝費斯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三官立而政體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舉
——康有為司法理念評議*
江玉橋,謝費斯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以清末中國司法現狀為依據,抨擊清末司法腐敗,引入西方三權分立制度,呼吁司法改革與司法獨立,力圖轉變清末司法固有模式。雖然結果不盡如人意,但其司法理念對清末的司法改革具有深遠影響,其思想和實踐經驗對于現代司法改革也仍具有啟示性作用。
司法改革;司法獨立;康有為
“中國的變革和現代化,肇端于19世紀西方列強四處擴張以建立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樣一個背景。”*[美]R.沃拉.中國:前現代化的陣痛[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1.清末時期,封建制度的各種弊端進一步暴露,君主專制的加強,吏治的日益腐敗,刑獄的嚴酷黑暗,激化了社會矛盾。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伴隨著戰爭失敗的是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特權被西方帝國主義強行奪取,中國司法主權的完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中國開始被迫融入國際社會交往之中。在民族危難之際,一部分地主階級的開明人士以及后來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為“匡時濟世”、救亡圖存,要求進行社會改革,試圖通過變法以圖強。他們一方面從刑獄的黑暗和收回領事裁判權來闡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及緊迫性,另一方面通過將西方先進的司法制度引入中國,希望改變行政與司法一體的現狀,以二者的分離作為改革的核心,通過司法改革保證司法獨立,從而重塑中國司法制度。康有為作為其中的杰出代表,身體力行,為中國的司法改革做出了重大貢獻。
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西樵山人、明夷、游存叟、更甡,出生于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因而又被人稱為“康南海”。康有為出身于廣東望族,家中世代為儒,自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康有為信奉孔家學說,并希望通過自身努力使儒家學說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潮流,成為國教。他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書法家和學者。著有《新學偽經考》、《康子篇》、《孔子改制考》等,將孔子的言論與資本主義相結合。1898年領導“公車上書”,成為戊戌變法的主要領導人,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1927年康有為卒于青島,他的學生梁啟超寫挽聯悼念恩師:“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西狩獲麟,微言遽絕,正恐天之將喪,不僅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
一、 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
出于歷史和社會原因,君主專制在清朝空前強化,與此相適應的,清王朝對社會的控制也達到頂峰,而這些與清朝的法律體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央,法律控制的職能部門是三法司,也即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為六部之一的刑部,其職責是“掌天下刑罰之政令,以贊上正萬民。凡律例輕重之適,聽斷出入之孚,決宥緩速之宜,贓罰追貸之數,各司以達于部。尚書侍郎率其屬以定議,大事上之,小事則行,以肅邦犯。”*光緒會典(卷五三)[A].引自陳茂同.歷代職官沿革史[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19.大理寺是審讞平反刑獄的官署。凡斬、絞罪案,必須在經刑部審理、都察院參劾之后,送大理寺復核。都察院是國家最高檢察機關,職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清史稿·職官志[A].引自陳茂同.歷代職官沿革史[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05.,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為正、副長官。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史中,司法權始終是與行政權合二為一的,地方各級政府既是行政機關又是審判機關。“今夫獄治于州縣,定于府廳,覆于司道,成于撫按,而后聞之上,覆之法司,而獄治決”,“刑名之執掌,系重且嚴矣”*皇朝經世文編(卷九三)[A].引自沈大明.《大清律例》與清代的社會控制[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0.。然而,真正享有最高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仍是皇帝,換言之,清朝皇帝是最大的法官,他掌握著全國的最高立法權與司法權并通過上述機構對全國進行有效的控制。這種司法與行政統一的制度,初時的確加強和鞏固了清王朝統治,但隨著世界格局的改變,這一制度對中國的影響弊遠大于利。正是由于認識到了這一點,康有為率先提出了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一)批判現有體制,闡明司法改革的必要性
如果說鴉片戰爭的失敗讓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睜眼開世界,那么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的戰敗則讓他們認識到洋務派所鼓吹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是空中樓閣,他們開始將目光投向了腐朽的清王朝統治本身。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應廢除君主專制制度,并就此與保守派展開了激烈論辯。首先,在康有為看來,注重君臣有別、等級森嚴的傳統君主專制制度,其弊端在清政府身上則表現為“壅塞”或“不通”*龔郭清.論戊戌變法前康有為對君主專制政制的批判[J].安徽史學,2003,(3).,而正是這種“壅塞”或“不通”,致使以皇帝為首的當權者居廟堂之高,對于處江湖之遠的百姓基本生活情況一無所知,更別提了解民眾苦難和世上瘡痍。同時,對于西方世界全無了解的中國最高統治者也沒有判斷中西基本情勢的依據,無法對比中外力量,導致在戰爭中一再受辱。換言之,康有為認為,這種“上尊下媚”的朝堂之風,使得中國在面對“中塞外侮”的情形時缺乏反抗之力。所以,康有為認為,面對近代西方的沖擊,“尊卑太過”的傳統君主專制制度,使中國“終難自強”*姜義華,吳根梁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77.。其次,康有為認為,當皇帝的利益成為一國最高利益時,其給國家和人民生活帶來的傷害必然是極大的,且愚民往往是這種君主專制制度的目標,從而導致對社會政治生活造成的極具毀壞性的影響。康有為說:“秦、漢以后,既不獨智以為養,又不范禮以為教,時君世主,以政刑為治,均自尊大,以便其私,天下學士士大夫相與樹立一義其上者,砥節行,講義理,以虛言扶名義而已,民生之用益寡矣”*姜義華,吳根梁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2.。再次,康有為指出,專制君主往往“隔絕才賢,威臨臣下,以不見不動為尊,以忌諱壅塞而樂”,這就使得因循守舊成為從政的宗旨為朝堂官員所奉行。在這樣的君主專制制度下,刑獄黑暗、司法腐敗的現象大量存在。在我國,監獄自古有之,但清朝刑獄之黑暗可謂是歷代之最。清朝的監獄分為中央監獄和地方監獄,在監獄管理方面嚴格甚至到了嚴苛的地步,由于歷史的慣性和現實的特點,清朝監獄集歷代監獄黑暗殘暴之大成,惡劣的生存條件、私刑的濫用、殘酷不法的獄吏使得清朝的監獄無異于人間地獄。
康有為作為維新派的代表人物,通過對清政府刑獄制度的鞭撻,深刻揭露了清朝司法審判的腐敗。清政府的司法審判制度在康有為看來是小民有冤,呼號莫達,獄吏肆威,刑迫索賄,即使不死,也毀體破家,其凄慘酷毒,一言以蔽之“非人生所忍言也”。西方各國則與此相反,“刑去繯首,獄囚頗潔,略乞苦境”,因此,中國的司法審判制度應加以改革,“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變之之法,富國為先”*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二)[M].神州國光出版,1953.200.。
基于上述原因,康有為認為,中國的司法改革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康有為認為中國應該主動打開國門,嘗試主動接受國際交流原則,借鑒西方先進的法律文化。其次,他主張對司法進行全面的變革,建立健全司法體制。最后,他號召成立相應的改革機關,如在制度局中附設法律局,自主進行司法改革。
(二)收回領事裁判權,論證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不難看出,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的中國自然談不上司法獨立,但至少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司法主權是完整的。鴉片戰爭后,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西方列強攫取了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所謂領事裁判權,即指在一國家內,對于這個國家來說的外國人在當地犯罪,能夠不受這個國家的法律約束,而有外國派來的領事官審理牽涉該外國人的案件。領事裁判權作為一種治外法權存在,侵犯了一國的屬地優越權。
領事裁判權問題幾乎貫穿整個中國近代史,赫德曾就領事裁判權問題說道“領事裁判權是各項條約的中心觀念。”也正是由于這一制度,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的各類侵略活動似乎都師出有名,以至于對其他條約特權的行使也有了保證。領事裁判權制度對中國的司法主權完整帶來了嚴重損害,百害而無一利,它使得中國的司法主權不再完整,外國人即便在中國侵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也仍可以逍遙法外,中國“實業不振,溯其原因”,也“半由于此”*童蒙正.收回海關管理權之步驟及辦法[J].銀行周刊(第6卷),1.。 它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社會性質的一個重要表現。作為西方列強的一種非法特權,領事裁判權早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出現了。隨著帝國主義國家的侵華,為了更好地在攫取權力的同時規避中國法律,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了領事裁判權制度。他們先是指責中國官吏腐敗,司法制度不良。再來認為中國法律野蠻,刑罰“過于嚴酷不合人道,此種制度目的純為威嚇,缺少感化之意。”*孫曉樓,趙頤年.領事裁判權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161.三是對中國的連坐制度不滿,批評中國司法不公,實行地域保護。中國當局“不予外人以法律中故殺與誤殺有別之利益者”,并且在通商過程中,一國商人中只要有一人犯罪就可能殃及全國,導致清政府與該國停止通商。然而即便當時中國的司法相較于西方各國確有落后,也并不至于影響到中國執法公正的問題,因而這些理由明顯是有些穿鑿附會、生拉硬扯了。這些理由無非是西方列強為能在中國順利建立領事裁判權而找的借口。領事裁判權的出讓后果是相當嚴重的,然而當時的清政府并沒有意識到其有可能導致的結果,事實上,受中國傳統的息訟主義影響,清政府甚至將訴訟當成一種累贅,當時作為清朝談判大臣的耆英得意洋洋的認為,領事裁判權這一條款的訂立,有“杜絕釁端,永遠息爭相好起見,兩無偏枯,亦兩無窒礙” 的好處,被稱為“通曉夷務”耆英尚且如此,當時清朝士大夫們這種普遍的無知心理可見一斑。
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上書光緒帝稱:“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實為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不同故也。今宜采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舶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湯志鈞.康有為政論集(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1.214-215.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認為倘若不希望中國的司法主權遭到進一步破壞,那么進行司法改革就是迫在眉睫的了。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吾國法律,與萬國異,故治外法權,不能收復。且吾舊律,民法與刑法不分,商律與海律未備,尤非所以與萬國交通也。今國會未開,宜早派大臣及專門之士,妥為輯定,臣前所亟亟請開法律局為此也。請附于制度局并設之。”*湯志鈞.康有為政論集(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1.352.
二、 欲行新法,非立三權未可行也
在西方政治理論家中,康有為最為看重法國17世紀哲學家、法學家孟德斯鳩。因為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國家學說和法學思想等曾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依據和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在戊戌維新變法運動中,康有為變革中國政治的理論支柱之一便是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康有為吸收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認為在中國要改變行政制約司法的現狀而實現司法獨立,必須對國家機構的運行機制進行改革。因此,康有為大膽的提出在中國進行司法改革,仿效西方推行三權分立體制,促進司法制度的變革,保證司法獨立,法官獨立。康有為的三權分立思想雖然比較零亂,但卻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提出以三權分立思想并要求付諸實踐的思想家。以今視昔,康有為對孟德斯鳩的學習和理解也許是片面甚至是淺顯的,然而在康有為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下,在中國推行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依靠傳統的今文經學顯然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學習西方的先進理論,借鑒日本的經驗并結合中國自身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和運用。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等人在國家機構改革方面的進行了多種嘗試,雖收效甚微但卻不能否認其進步意義,尤其是通過對司法機構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司法權的獨立,然而由于當時的司法改革并不成熟,這時的“獨立性”是相對的。換言之,戊戌變法時期司法獨立改革的相關活動,并未將司法權從行政權中分化并脫離出來,至于對建立司法權與行政權、立法權的相互制約機制方面懈怠或者說根本無暇顧及。
(一)引入三權分立制度,倡導司法獨立
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以圖變法強國,雖無奈以失敗告終,但其制度變革主張在中國轟動一時,也使中華法系大一統局面再難以維系。在司法獨立這一問題上,康有為主要從“三權分立”與“法官獨立”兩個角度對其加以闡釋,他寄希望于引進西方三權分立制度來促使中國司法獨立。康有為認為,“政體之善”幫助西方各國和日本走向富強,而“三權分立”體制則是使西方各國和日本國力強盛的根本原因。他盛贊日本“變法之始,即知此義,定三權之官,無互用之害……蓋得泰西立政之本”。康有為認為,“今欲行新法,非立三權未可行也”*郭志祥.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司法獨立研究(上)[J].環球法律評論,2002,(1).,“三官立而政體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舉”*郭志祥.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司法獨立研究(上)[J].環球法律評論,2002,(1).。“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后政體備”*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二)[M].神州國光出版社,1953.199.。他提倡在保障君主立憲的同時,將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授予三個不同部門,各部門相互獨立,互相制約。在此基礎上,康有為就這一制度具體闡述道“凡民之身命財產權利,皆公之國所當力為保護,勿使喪失者也。保護之官有六:一曰司法以防奸宄;一曰警察以防盜賊。中國在古既有司寇,而后世大理司隸法曹賊曹,皆分設二官,而各國以司法當為獨立,稗其不撓,而警察必付地方官,令其便于行政也。”*康有為.官制議[M].香港:香港廣智書局,光緒三十六年六月.3.
作為中國第一個提出“三權分立”思想的人,康有為對于司法獨立的構想具有獨創性和先進性,但其做法在當時無異于與虎謀皮。畢竟,在清末時期以皇權為核心的君主專制體制早已根深蒂固,皇帝是國家的最高集權者,同時掌握著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項大權。即便是清末的仿行立憲,也不過是清王朝為維護自身統治、緩和激化的國內外矛盾的形式之舉,正如主張立憲的清末重臣載澤在《奏請宣布立憲密折》中闡述立憲的好處時所言,“一曰,皇位永固。立憲之國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負責任,由大臣代負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議會與之反對,或經議院彈劾,不過政府各大臣辭職,別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遷,君位萬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漸輕。今日化外人之侮我,雖由我國勢之弱,亦由我政體之殊,故謂為專制……一旦改行憲政,鄙我者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策……”*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9.173-175.。更何況是由當時毫無一兵一卒、力量薄弱的新興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依靠一個沒有任何實權的光緒帝而施行的戊戌變法。另外,康有為以“君主立憲”為根本,主張三權分立下的司法獨立的改革基調根本不能對該時期下的司法體制有所觸動,不難看出,康有為對與司法改革的建議在當時無異于以卵擊石。實際上,面對在中國早已根深蒂固的君主專制統治,無論形式如何,司法獨立改革都舉步維艱,任何形式的司法獨立都不可能徹底。
盡管康有為“三權分立”的思想并不完善與成熟,但是康有為從孟德斯鳩的理論出發,一定程度上結合中國的國情,勇于實踐,率先在中國倡導并著手實踐“三權分立”,所以稱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系統闡述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并要求在中國付諸實踐的思想家是當之無愧的。
(二)實現“三權分立”的關鍵:法官獨立
“三權分立”的關鍵在于司法獨立,而法官獨立又在司法獨立中居于重要地位。在論述孟子的《盡心上》的部分小節時,康有為曾說“此明司法官之獨立,而法律各有權限,不得避貴也。各國律皆有議貴之條,此據亂世法也。……故明法司可執天子父,而天子不能禁也。拘父猶不能亂法,況其他乎?此章專明司法獨立之權,而行政不得亂法,托舜發之。竊負而逃,乃極言孝子之意,明終不能恃天子之勢,而行壓制,亂法律。不必泥也。”*汪學群.康有為《孟子微》發微——兼論以西學補充印證[EB/OL].(2010-06-28).[2011-11-01].http://jds.cass.cn/Item/8346.aspx.
康有為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首先需要將法官與行政官分離。他認為,司法、行政二官必須分離,主謀議政的心思雖靈明,使它主持施行則無用;主持行動的手足雖敏捷,使它主謀議則無所知。兩者各有其特殊功能,不能兼用,也不能互換。按照這種理論觀察當時的中國社會,不難發現中國遍地都是行政之官,但卻缺少獨立的司法之吏,造成了“有肢體面無心思,不能成人;有行政而無議政,不能成國”的怪現狀。同時,康有為注意到,在變法前與中國境遇相似的日本,在變法后開始飛速發展。康有為認為只是因為日本從變法開始,便應用孟德斯鳩學說,定三權之官,議立法之制,通變宜民,政通人和,可謂學得了西方立政的根本。依據孟德斯鳩的學說,參照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對照中國時下政體存在的問題,康有為認為“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權,未可行也”不失為一個解決方法。把定三權變政體,作為政治變革的中心任務,這分明是試圖用資產階級創立的分權政治體制來取代封建專制主義的一統政治體制,從而進一步變革司法體制,將司法權從行政權中獨立出來。這說明康有為學習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抓住了根本的,是走在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前列的。
其次,康有為認為應該看重對法官的培養。康有為一向認為購船置械,可謂之變器,不可謂之變事;設郵便、開礦務,可謂之變事,不可謂之變政;改官制,變選舉,可謂之變政,不可謂之變法。所以,他把“改定國憲”稱之為“變法之全體”*倪學新.論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的議會思想[J].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1999,(1).。因為只有改定國憲才能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范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所謂“改定國憲”就是指的立憲法。在此基礎上,康有為認為法官的地位在發揮法律作用中十分重要,他提出應精選“司法之刑曹”,“厚俸祿養廉,以勸吏恥”。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既然是康有為變革中國政體的主要理論武器,而作為三權中重要的司法權,司法權作為一種判斷權,其主要職能就是直接滿足一定的主要目標所具有的功能,即排除法律運行中的障礙,以維護法律的價值,因此改革司法權在康有為的變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康有為力主保障法官地位獨立,主張專職審判人員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機關干預,并提出通過提高法官的待遇來確保司法公正。
三、 司法改革與清末中國現實的沖突
盡管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代表為中國的司法變革做出了種種設想,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倘若從實際的效果來看,我們對清末中國的司法改革的成績可以說不能有絲毫樂觀的估計。在司法改革的進程中始終存在名與實的矛盾和沖突。
首先,中國的司法權可以說始終未能擺脫對行政權的依賴及受行政權的控制。畢竟,中國封建社會實行行政司法合二為一的傳統由來已久,雖然康有為提出司法獨立的理念,但始終未能形成司法權與行政權相互制衡的合理關系,相反,行政權制衡并約束司法權的現象也并未因其理念的提出而被打破。自古以來,中國就有行政控制或干預司法的傳統,作為最高統治者,皇帝一方面掌握著最高行政權,另一方面又享有包括司法權在內的一切大權,這就導致皇權在司法領域的肆意橫行,而皇帝的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一旦對司法進行干預就必然是不可反抗、不容駁斥的。此外,縱然清政府在中央設置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這三個司法機關,同時在地方司法審判機關審級森嚴,具體分為四個級別,州縣為第一審級,府為第二審級,按察使為第三審級,總督巡撫為第四審級,但行政權對于司法的干預也屢見不鮮,行政官員同時行使著司法權力的現象似乎已成慣例。事實上,這一傳統中國古已有之,無論是漢朝的“地方司法機關由郡縣長官兼任”*趙增祥,徐世虹注.漢書·刑法志注釋[M].高潮審訂.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前言”第4頁.,還是宋初“大理寺長官不設專職,由其他官員兼允”*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宋史·刑法志注釋[M].北京:群眾出版社,1979.“前言”第11頁.,均是行政綁架司法的最好例證。上至中央下到地方,行政干預司法儼然成為了一種為歷代所繼承的司法傳統。這種行政“綁架”司法的傳統不但造成中國負責司法的官員缺乏專業性,也致使司法觀念難以轉變,從而阻礙司法獨立改革的進程。在這種司法傳統理念面前,康有為所提出的司法獨立與法官獨立無疑是具有先進意義的。但是,要轉變傳統思想并非易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僅靠康有為等維新派的呼吁和一個無實權的皇帝的推行難以撼動延續千年的司法體制,即便制度上或者說名義上推行了相關制度,實際中的傳統理念也難以改變。
其次,帝國主義不會允許中國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當時,帝國主義已經攫取了領事裁判權,中國司法主權的完整性已不在,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事實上,為改進、收回領事裁判權,清政府也曾積極做出謀劃和努力,但效果不佳。相比中國,在光緒二十年鄰國日本便與英國簽訂了有關收回領事裁判權事宜的條約,約定“開放日本全國”,“外國人受日本司法權之支配”, 5年后實行,自實施之日起,“領事裁判權全歸消滅”*國務院法制局編:《日本廢止領事裁判沿革志略》,1920年印行,第18-19頁。。分析清政府在收回領事裁判權上失敗的原因,雖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帝國主義不愿放棄,但最主要原因還在于清政府自身。較之日本,清政府受傳統思維影響更甚,加之在外交上的失敗和廢約意識的淡漠,都使得清政府在收回領事裁判權一事上受制。此外,導致這一結果也與清政府在國際交往中始終采取“馭外”之道,而對于近代國際交流原則的一無所知有關。在相當長時間,清政府沒有廢約的打算和籌劃,與日本比較,相距不啻天壤之遙*李育民.晚清改進、收回領事裁判權的謀劃及努力[J].近代史研究,2009,(1).。面對帝國主義的阻攔,清政府自身的消極懈怠,使得康有為等人對于司法獨立的呼吁在時代大背景下顯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即便在制度上確立了一些司法獨立的原則,也仍然掩蓋不了實踐中司法權被帝國主義的一再侵蝕。
最后,在司法理念上的不成熟,使得司法改革缺乏思想理論作為支撐。司法獨立原則要求法官審理案件只服從于法律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涉,要求司法權與行政權和立法權相獨立。司法獨立原則起源于西方的三權分立學說,相比于西方對于司法理念的深刻理解,近代中國對司法獨立的認識就顯得有些幼稚了。首先,康有為等人在提出的“司法獨立”時,中國并沒有形成法律至上的思想基礎,因而基本上只是徒有其表,并不具有深刻性和革命性。暫不提康有為等人本身就是一直受傳統中華文化熏陶,對于“司法獨立”思想大都深受皇權至上的傳統和觀念的影響,單就西方學說在鴉片戰爭之前也甚少被中國人關注,到戊戌變法時思想積淀不足這一點,也足以致使新興的資產階級維新派自身對于司法獨立認識的重要性不足,革命性不強。同時,康有為等人是為了維護和鞏固清王朝的統治秩序才提出司法獨立思想的,即便他們提出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制度,也并非出于想擺脫專制皇權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維新派所提出的司法改革必然是理論上要求獨立,實踐中則充斥著對于皇權的妥協,同時具備徹底性和革命性是不可能的。此外,康有為雖然提倡“三權立,然后政體備”*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二)[M].神州國光社,1953.199.,但其前提條件是君主立憲,正如他所說“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中國史學會.戊戌變法(二)[M].神州國光社,1953.236-237.。總之,縱然他們有關于“三權分立”的思考,卻依然沒有真正的將司法權、行政權、立法權放在同一層次去理解,也缺乏將三者置于同一地位進行考量。其次,由于司法理念不成熟,康有為提出的司法獨立思想并不系統,過于片面。維新派的司法獨立思想過于強調將司法權從行政權中解放出來,注重“三權分立”角度上的司法獨立,反而忽略了法律至上這一真正的司法獨立精神。換言之,它主要追求分權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卻并未勾畫與之相應的權力制衡機制。總而言之,清末康有為等人所提出的司法獨立思想并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在進步性和完備性方面都有所欠缺。清末這種先天不足的司法獨立思想是導致相關制度的設計和踐行后天畸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康有為司法理念的影響及啟示
康有為身處晚清時期,封建的儒學、理學等對他影響極深,但他能夠突破這些舊學的束縛,積極地將眼光投向西方,將西方的先進思想與傳統文化進行糅合,并積極踐行司法改革,以其不屈不饒的精神多次向光緒帝上書,通過對其司法理念的闡明,促使光緒帝進行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建立資產階級政體的嘗試,推動了中國近代國家體制的近代化,無論對當時還是后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他所提出的司法理念對于現代中國的司法體制的建設仍有可借鑒之處。
(一)康有為司法理念的影響
康有為站在歷史發展的潮頭,站在在龔自珍、魏源、洋務派以及早期改良派的肩膀上,進一步完善了君主立憲方案,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操作性。他不僅僅將這一制度單純的停留在理論的勾勒、設計和輿論的宣傳上,更是將其付諸實踐,領導了戊戌變法并成為其精神支柱。康有為推動了近代中國歷史上建立資產階級政體的第一次變革,開啟了中國近代國家體制近代化的開端,在當時及此后產生的廣泛影響更是不可低估的*李玉琳.論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思想及實現[J].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6,(2).。由此,對于康有為所進行的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應充分肯定其進步意義,對于其對司法理念的發展貢獻也應給予高度評價。作為一股新興力量,相較于清末保守勢力的強大,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想與之對抗無異于以卵擊石。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等人選擇依靠當時較為開明的光緒帝作為維新變法的領導者,雖說效果不盡如人意,但也可以說是一種比較符合實際的做法。康有為等人通過制度局的設立,為今后議院的建立做準備,從而一步步實現新興資產階級和開明地主官紳的政治愿望,以此來推行維新變法,而主張“三權分立”及“司法獨立”思想在當時是具有實踐意義的。但從總體來說,出于時代、社會等原因的限制,對于司法改革的理念探討更多地集中在宏觀上而忽略了微觀上的具體設計。換言之,浮于表面的多,深及內涵的少;急功近利的多,循序漸進的少;闡明理論多,攻于實踐的少;激進強烈的多,漸進溫和的少;贊美西方的多,重視國情的少*康有為對光緒皇帝的一段話可為佐證:“變法的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采擇,但待推行耳。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士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三年之期,心態之急可見一斑。。
盡管由于自身和時代的原因,康有為的司法改革思想或多或少收到了限制,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理論對于當時尚未完全開化的中國推行司法改革,建立自己的司法體制有著重大作用和深遠影響。早在戊戌變法前,康有為就對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進行了理論上的論證。在他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中,他指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而“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姜義華,吳根梁編校.康有為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7.280.537.。同時,他對于中國重合的機構設置也持反對意見,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姜義華,吳根梁編校.康有為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7.280.537.。
(二)康有為司法理念對我國司法建設的啟示
康有為以他的司法理念和戊戌變法中的實踐,改變了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了近代政治的發展進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其理論及實踐活動對后來者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示。即使在今天,我們還可以通過對他司法理念的研究,加深對近代中國司法建設的歷史困境和艱難歷程的理解,也對今天的司法建設起到重要的啟示作用。歷史有其相似性,總結歷史上司法改革的經驗教訓,在我們面對今天的的司法公正與腐敗問題時無疑會有所幫助,揚其之長避其之短,只有長于總結,才能為日后的提升做好準備。
首先,面對多元的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儒家的仁者愛人、中庸思想,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亦或是法家的“以法治國”(與現代意義的法學固然有所區別),都讓炎黃子孫受益匪淺,其思想意蘊之深刻,至今仍頗具影響。然而任何一種文化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適當揚棄是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方法之一。面對那些已然落后于時代發展的傳統文化,我們應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實踐中發展完善它,使其仍為我可用。例如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相比于現代法學中的“以法治國”,二者的區別在于人治與法治孰輕孰重,這就需要我們去完善它了。至于傳統文化中那些完全不能與時代相溶的部分,我們應毫不猶豫的拋棄它,比如承襲千年的封建等級制度,其與現代的平等觀念格格不入,完全可以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司法改革之所以失敗,其關鍵就在于忽視了文化建設在改革中的所起的作用,對于傳統的文化缺乏理智的判斷、主動的反思與有選擇的繼承。于今天而言,中國豐富的傳統文化不應是司法改革道路上的阻礙,而應是改革路上的助推器,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放眼當下,在面對傳統文化時,我們需要特別注意摒棄其消極影響,有效的進行揚棄。尤其是已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和無處不在的人情風更是我們必須拋棄的。
其次,康有為所處的清朝,中央權力在太平天國運動后越來越弱化,而地方的勢力卻空前的擴大,國內政治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同時帝國主義列強還在大肆瓜分中國成為其殖民地。法律至上的觀念并沒有成為當時人們的信念,甚至在少數精英階層里,真正統一的司法理念也從未出現過,相反由于觀點不一致而導致的爭論卻從未停歇。司法改革失敗一方面是由當時動蕩的時局造成的,另一方面改革失敗又更加劇了時局的不穩定,這種惡性循環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由此可知,司法建設若想成功,穩定的社會環境必不可少。現如今正處于社會轉型關鍵期的中國,各階層不斷分化組合,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對于社會的穩定而言無疑是一枚定時炸彈。我們在司法建設中要注重的穩定不能僅僅只是形式上的穩定,更應是觸及到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深入到文化、經濟和政治中的穩定。也只有這樣的平衡和穩定,才是司法建設所必需的真正、長久的穩定。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Brings Prosperity—The Appraisal of Kang Youwei’s Judicial Concept
JIANG Yu-qiao, XIE Fei-si
(Lawschoolof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Based on Chinese justice statu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Chinese reformers, Kang Youwei, who criticized judicial corruption and introduced Separation of Powers to China. He called for independence of judicature and tried his best to shift judicial mod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results were not satisfactory, his concept of judicatur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judicial refor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the modern judicial reform still have a revelatory effect.
judicial reform; independence of judicature; Kang Youwei
2014-03-16
國家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相關研究成果。
江玉橋,男,武漢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學;謝費斯,女,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協管秘書。
D909.92
:A
:1672-769X(2014)03-003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