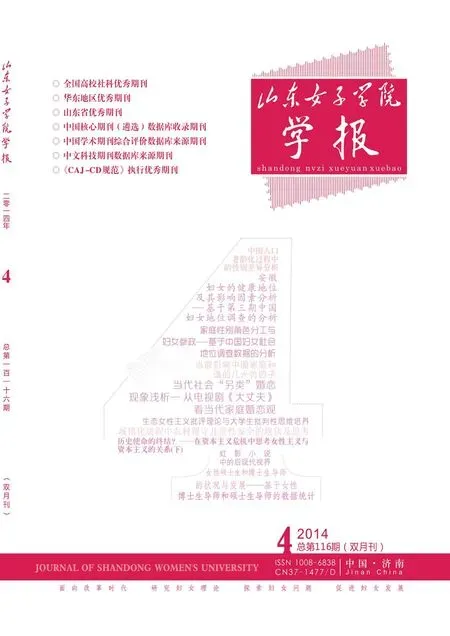虹影小說中的后現代視界
張守華
(山東女子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虹影是當代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就她的小說而言,在國內能見到的除《鶴止步》是寫男同性戀外,其他皆以有著不同的職業和婚姻狀況的中國女性為主角。她運用反本質主義和多維視角的敘述方式講述了一個又一個不同于男性作家宏大歷史文本中的“歷史”,向男權話語統治提出質疑,向讀者揭示出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二元對立”[1](P58)的復雜世界,體現出歷史背景的非深度性、敘述視角的非中心性和對權力話語的解構等后現代主義特征。
一、歷史背景的非深度性
在虹影看來,任何隱秘的歷史都會被面向大眾的歷史所掩蓋,翻過歷史的非正式記錄才能看見歷史的原貌。這種對傳統敘事的不信任導致了虹影小說文本對歷史的模糊化,從而達到解構傳統歷史的目的。但是解構并不是銷毀,歷史也無法銷毀,解構的目的在于重建,重構在“大歷史”中消失的底層人物、邊緣人物、女性的歷史。
小說《上海王》描寫大革命時期的上海,主人公——申曲名角筱月桂由一個鄉下插秧女成長為上海灘名副其實的“上海王”的不凡經歷。作者通過中國傳統的“命相說”將筱月桂與上海洪門的興衰聯系在一起,而洪門的興衰榮辱又與近代中國政治的風云變幻息息相關。在這個文本中明顯地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筱月桂奮斗的1925年的上海的風物人情。那些大事件只是幾個在任何歷史教科書中都可以查到的名詞。同樣,在《上海之死》中,著名演員、美國情報人員于堇也是一邊回憶自己的人生路一邊執行一個后來改變二戰戰爭局面的任務:竊取日本的軍事情報。她的身上凝結著上海的軍閥之爭、國際大戰盟國和協約國之爭。在她縱身躍下高樓的剎那,我們看見的是一個美麗生命的終結,她的人生之所以感動我們不僅因為她挽救了中國,更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一個渴望愛卻無愛的傳統意義上的弱女人。正是這個弱者,這個處于戰爭邊緣的女人改變了歷史。作者將歷史名詞的內容巧妙地演繹成為一位民族女英雄的傳記。我們可以相信,歷史不只是男人創造的,可是在正史中我們卻看不到女人的記錄,虹影在她的小說中做到了對女性歷史的重建。
關注小人物的生死情愛掙扎是虹影書寫視角與男性宏大歷史敘事塑造英雄的正義血性的最大不同。瑪格麗特·尤瑟納爾說:“她們把戰爭作為背景,個體的感情和生存遭遇才是她們關注的焦點。在我看來,這是她們共同的女性立場使然。歷來戰爭都是男性的,女性從未真正置身其中,她們被驅逐于戰爭歷史外,要么成為男性的欲望對象,要么等待男性的啟蒙和拯救,如果個別女性想要走上戰場,她們得‘通過忘卻,抹煞性別’”[2]。所以,歷史背景的模糊化也是作者人文關懷的需要。在小說文本故事中的人物表現出后現代文學理論所說的“零散化的共時性存在”[1](P47),因為歷史本來就不是一個人的,這些小人物,沒有在歷史中留下足跡,他們是歷史的過客。我們無法為小人物一一作傳,這是文字的無力,歷史的蒼白。可是我們可以不再沉默,我們可以重建歷史的另一半——女人的歷史。虹影的小說“穿透了宏大的歷史迷霧,用個人想象和經驗返回到歷史情境,又在對歷史的書寫中走進個人的情感世界。”[3]
二、敘事視角的非中心性
虹影以一種平和的心態看待人類文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其所秉持的態度也更加寬容,視野也更加開闊。在虹影的文本中,我們看不到非友即敵、非男即女、非好即壞的“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也沒有把事物都歸納說出現象背后的本質的深度。因為在作者看來,人類生活在這個非單向度的歷史空間中,思維不應該是一種思路,歷史的本質在不同的人那里也有不同的表達。所以,她只是一個敘述者,一個享受文本歡樂的作家,那些關于歷史的定義應該交由歷史去評論,她只給讀者提供一種現象或者自己的創作感受,甚至作者的思想都是讀者產生評價的參考。
在重寫筆記小說系列中,她將明清的筆記體小說框架拿到現代,用當代的人情世故重新演繹,將多視角的思考融入一個個生動的故事。《白色的藍鳥》中,女大夫盛年年通過自己的報復懲罰了背叛者沈立,也拯救了被痛苦折磨的邏輯學家。對背叛的懲罰不是傳統的兩敗俱傷,而是讓自己扳回一點損失又同時重重打擊叛逃者。她將作品中的主體選作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通過文本對這個屬于人的世界做出自己獨特的陳述。在她的戰爭描寫中我們看見不是很壞的“敵人”,如《垂榴之夏》中的緣子眼中的日本軍醫并不是傳說中的那么壞,日本軍醫的“聲音不兇,反而溫暖人”。《鶴止步》中寫白色恐怖時期特務大本營上海極斯菲爾路76號中發生的兩個小混混男人間的感情。盡管我們對汪偽特務機構的兇殘早有耳聞,但是在這里我們沒有看見特務如何殘害“正義人士”,而是通過作者細膩的心理描寫看見非正常感情的掙扎,甚至這種掙扎到最后都會感動我們,就像小說的名字所表達的:“鶴欲飛,升起的腿卻突然靜止不動”的凄美。消解了二元對立,故事敘述變得豐富和悲憫,這也是虹影超乎尋常的人文關懷之處。
后現代主義反主體性觀認為:非神圣主體的個體將那種集體性的烏托邦還原為個體性的自我存在。他只是自然地、寬容地看待事物標準和爭端,沒有超越歷史的觀點。任何標準都不可能具有先驗絕對性,任何結論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獲得,而需要人這一存在主體自身不斷地去發掘和把握[5](P51)。虹影在她的作品中對這一點進行了很好的探索。筱月桂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海王”以后仍是孤獨的,她不是神圣的王者,她只是一個渴望親情愛情的女人,甚至甘心做小妾。她是一個報復心很強的人,甚至想法殺掉自己的舅父母,但是對表弟并沒有一起憎恨,因為父母的仇與表弟無關。同時,她又是一個全心愛自己孩子的母親,為了成全女兒,她舍棄自己的愛人。她站在最高的上海國際飯店樓頂,內心涌動著沒有親人的悲涼。
虹影小說文本中的多種文化狀態的表述瓦解了傳統敘述的權威性。“她以一種中國作家普遍缺乏的全球化意識,即在全球化的歷史場景中表現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4]《女子有行》寫一個在未來時間里穿行上海、紐約、布拉格的中國女人的生動冒險。在這三部曲里,我們看見這三個國際移民城市里紛擾的民族宗教種族糾紛。作為一個海外華人,深知離散人群的艱辛生存狀態,不僅要對抗基本的生存問題還要面對排外者的歧視甚至敵對目光。作者以一種全球化的視野審視這些行為,肯定這種行為的原因是出于生存的恐慌:“每一個人的出現都是在消解另一個人的存在”,然而,這種趨勢能阻擋得住嗎?宗教能救贖人迷途的心靈嗎?顯然不能。作者透過女主人公的冒險向讀者說明:國際移民勢不可擋,任何阻擋都會造成傷害,看看我們是要建立一個豐富多彩的生存空間還是要建立一個國際難民營,和平共處是在經歷了這一系列災難后唯一處理民族、種族、宗教糾紛的做法。
三、敘述話語的解構性
歷史的模糊化和多元敘述是作家解構權力話語的文本需要,這種解構體現在文本中就是女性話語的重建。后現代主義理論認為,話語即權力,文本寫作的目的不單單是為了講述一個有趣的故事,文本的目的是要表達一種聲音。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就是虹影小說中所要表達的后現代女性主義世界觀的有力工具,虹影的小說無論從寫作背景還是文本結構的安排都體現著作者渴望發出聲音的需要。
在虹影看來:“男權社會幾千年,把女人的社會角色固定在閨幃、臥房、產房、廚房里,而女人也把自己的角色固定化了,認為外面的世界本來就是男人的世界。一句話,被男人奴役慣了,就甘于自我奴役。因此,女人的苦惱男人要負很大的責任。”[5]虹影從傳統的女性形象入手,講明女性的深重痛苦:大多數女性在最初都對男人抱有幻想,因此她們也承受著傳統的不公和男人的傷害。在《上海王》和自傳體小說《饑餓的女兒》中,每個女人都有一段隱痛,這種隱痛來自男人,來自男人控制的社會。筱月桂在鄉下田里插秧,螞蟥吸在腿上,怎么也打不掉,她希望有人來幫她對付那個吸血的家伙,可是沒有人。六六不明白為什么別人都不理她,家里人也不喜歡她,她孤獨的童年希望有人陪伴,可是沒有,她懵懂的青春需要別人指點,可是沒有人,只是因為她是個為人和社會所不恥的私生女。所以在得知自己身世的真相時她痛苦地選擇逃離,流浪在尋找一個能容納她的家和愛她的人的路上。這些女性,在最初都是寄希望于這個社會和這個社會的當權者——男人,她們承受著這種希望破滅后的無助和痛苦。
與一些女性作家寫女性對男性的反叛流于極端女權主義或者通過自我放縱掙脫壓抑不同,虹影在讓我們認識到女性經歷的重重傷害和磨難的原因后,她邁過“寶貝們”的膚淺身體反抗,從女性的話語權入手重構女性獨立的道路。她筆下的女性有著后現代女性主義的特點:女性是自由的、獨立的,女性應該自己拿主意,自己來塑造自己的角色,而不是等待男人的安排。《孔雀的呼喊》中的后現代女性柳璀在美國讀書期間,有朋友質疑她不找情人,而柳璀自己的看法是:她看不起男女之間這種隨便的關系,倒不是講究道德,而是這種關系把堂堂正正的人弄得卑賤齷齪。柳璀既沒有“新”到只顧一己快活,也沒有“舊”到一切無所適從,喪失思考判斷能力。在《我們互相消失》中,女教師尹修竹同時愛上兩個男人, 這抉擇對女性來說是那么困難,因為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卻沒有這種特權。修竹偏不做“白馬與黑馬”的選擇,因為二者舍去哪一個都會心痛,她把選擇權放給同樣愛她的男人,她勇敢地說:“別害怕!我已經聽夠了你們倆人間來回倒賬,誰欠誰的?——別以為我是你們可以切開,可以分的財產,錯了,我早就明白我應該成為自己!——愛情不應該被綁架,不管以什么理由”。女性重新定義生存的這個社會,自己的感情和身體應該忠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成為誰的附屬物。她否定了女性身心內外的神話——男人的救贖和宗教的救贖,在她看來女性的自我救贖才是有效的,才是及時脫離苦海的“捷徑”,這無疑是對男性創造的神話的有力還擊。
掩卷沉思,虹影的小說給我們帶來文本閱讀快樂的同時,也以她獨特的后現代敘述視角和敘述方式給我們展示了觀察世界、理解世界尤其是女性世界的寬闊思維方式。她的小說正像“孔雀的叫喊”,立足于小人物,書寫草民的歷史,發出女性的聲音,深沉而悲涼,震撼而頗具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 張廣利,楊明光.后現代女權理論與女性發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36.
[3] 李鳳青.試論虹影小說的女性歷史敘事[J].批評與闡釋·當代文壇,2007,(1):102.
[4] 虹影.女子有行:序言[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5] 虹影.我與卡夫卡的愛情[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6.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