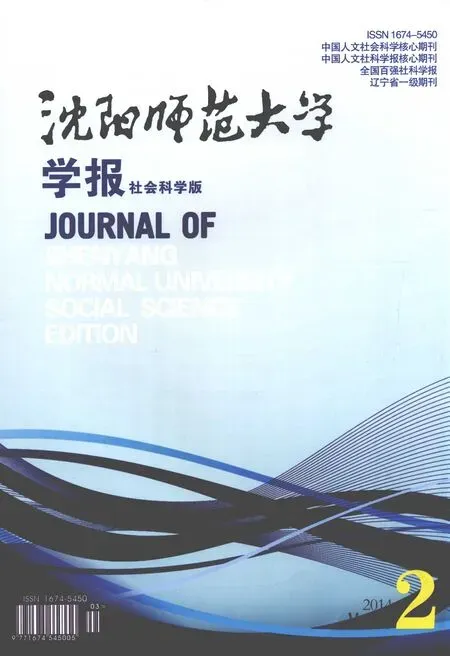高校文學理論教學向原典閱讀的回歸
宋曉云
(新疆師范大學文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4)
文學理論(亦稱文學概論)教學在我國高校的語言文學專業教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通常被安排在大一到大二學年階段,以期通過對文學理論課程的學習,促使大學生能夠盡早自如地面對古今中外文學史的學習,能夠獨立地分析和闡釋變化紛繁的文學現象。遺憾的是這一教學理想,未能夠經受得住學習實際效果的檢測,文學理論教學正面對一個進退皆難的窘迫狀況。本文擬對當前我國高校文學理論教學所面臨的困境及原因進行一定的描述和研究。
一、當前文學理論教學的困境
“文學概論”課程作為一個老品牌,在當下高校文科課程里面,卻遭遇著尷尬局面。此種局面,在學生和教師兩個方面都有鮮明表現。
一是學生厭學。相較于其他語言文學課程,大多數學生在學習文學理論課程時,常常顯得很吃力,或者說是有力無處使。層出不窮的理論范疇、概念術語會令他們生出目不暇接的恐慌無措感,雖然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苦背苦記,但從中所獲得的顯在益處卻非常有限。學生們往往在課程考試結束之后不久,通過死記硬背而獲得的文論知識,很快即被拋諸腦后,就算能夠記住,卻又不知如何用它來破解文學閱讀中所遇到的難題,致使其無形中對文學理論生出敬畏之心,乃至于敬而遠之。此種學習結果導致的一個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就是學生“在大四報考研究生方向時,與文學史課程相比,年年報考文藝學方向的極少,甚至幾乎沒有”[1]33。
二是教師厭教。俗話說“教學相長”,教與學本就相輔相成,而當教師花費大量的精力與心血之后,發現自己所設定的教學目標始終被偏離、構建的教學理想始終被遠離、自己所執教的課程始終處于一個不受歡迎的境地、學生的學習熱情始終“冷冷清清”時,他們往往也會心灰意懶,消極怠工。在教學過程中,“一些教師偷梁換柱將文學理論置換到美學、文化、產業的視域中,文學理論無限越界而名存實亡;一些教師‘照書念’,機械死板、氣氛壓抑、實踐缺席,造成學生‘困與乏’;一些教師將文學理論課固化到自己研究領域抑或相反天馬行空、漫無邊界地逃避規范教學……”[2]。在這種“教”與“學”皆對自己充滿鄙視的厭棄氛圍中,文學理論教學只能厚著臉皮行走于一條被動的、缺少鮮花與掌聲的“任務式”道路,越發顯得寂寥而尷尬。
二、文學理論教學被“厭棄”的原因
探究文學理論教學遭受冷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教學時間安排不合理
正如前文所言及,我國各高校一般在大一至大二階段就安排學生學習文學理論,這也就意味著大一階段時,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實踐即已開始。如此安排的初衷,是為了讓學生們通過對文學理論中相關知識的學習,能夠站在理論的高度,從理性的視域,以高屋建瓴式的眼光分析、闡釋古今中外文學、文學史學習中的各種現象。因為,文學理論盡管出于對文學發展歷史規律的提煉、概括與總結,但它最終還是必須回歸文學實際,對之行使指導權。可事實是,文學理論是一門極具系統性、概括性、綜合性、抽象思辨性特點的課程,它對于學習者知識的系統性、閱讀的廣博性、思維的縝密性等充滿期待。而大一的學生剛從中學階段那種重視個案訓練的天地中脫離出來,很難立刻從“文本有機整體的破碎化”[3]的思維習慣中華麗轉身,去運用“抽象的理論思維,重理性,重共性”地駕馭“一環扣一環又逐層上升的文學系列概念和原理”[1]33,去運用抽象的理性思維,故而,學生們在學習中由于找不到輕松學習文學理論的方法途徑,尋而不得其門,學而不得要領,忍不住會對之生出畏懼、厭棄之心。
(二)課程名稱與教材本身的缺陷
當前各高校所設置的文學理論課程,一般多稱為“文學概論”,所使用的教材卻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是“文學概論”一名,看似內容涵蓋量很大,“‘概論’這名字容易叫讀者感到自己滿足;‘概論’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著別的——其實什么都只有一點兒!”[4]。再者,不同學校使用的文學理論教材并不完全相同,而各不同版本的教材,自身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不同的編寫者在編撰教材時,往往帶有濃厚的個人學術研究之色彩,各人根據各自學術所長,讓教材淪為其學術著作的另一個衍生物,“各有各的體系,各有各的觀點,教材之間體系框架大相徑庭,”“眾語喧嘩,難成統一,不同學校的學生對文學理論的認知不統一,似乎文學理論這一學科是隨意的,沒有規范性,這樣必然會消解學科的科學性”[1]34。這種各部教材各守陣地、各表觀點、各用概念的不可通約性、兼容性狀況,不僅增加了教師“教”的難度,也增加了學生“學”的難度。總之,不同教材的不可兼容、通約性,進一步加大了文學理論教學的不受歡迎度,令教與學都不能將不同教材的同類知識進行有效置換。近些年,一些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者們意識到這種問題,并在教材編寫的過程中努力糾偏,但這樣的糾偏任務很難一朝一夕完成。
(三)原典閱讀的缺乏
“原典”,意為某一領域的經典要籍,本文所說的“文學理論原典”,指的是文學理論領域的經典要籍,它是文學理論最開始、最本源性的文獻,是未經修飾、詮釋、解讀的觀點、學說,如原典《文心雕龍》則指劉勰的原著《文心雕龍》,而不是指我們那些經過后人(如黃侃、王元化等)闡釋過的《文心雕龍》。對于文學理論的學習而言,閱讀理論原典既重要又必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有學者批評文學理論教學中的一種錯誤認識:“搞文藝理論的人常常容易產生一種誤解,以為搞理論吆,就是從理論到理論,搞‘純理論’,看專業書也只看理論書。其實,搞文藝理論,應該下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文藝創作,廣泛涉獵各種形式、各種風格和流派的作品,加以比較和分析,特別要注意文藝領域出現的新人新作和新事物新經驗。”[5]如果說,只看理論書是一種極端,那么現如今不看理論書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們生活的當下,是一個眾聲喧嘩,全民追求娛樂的時代,人們十分看重娛樂性、消遣性的閱讀,進而拒絕嚴肅的、抽象的、思辨色彩濃郁的閱讀對象。這樣的時代性潮流也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在校大學生的閱讀選擇,他們習慣去碰觸輕松的閱讀對象,而對那些充滿抽象概念的文學理論著述自發地敬而遠之。況且,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人天生就具有按照快樂原則行事、追求自我滿足的無意識心理。所以,高校圖書館、資料室中的小說、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借閱率高居不下,此類圖書資料磨損嚴重,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修補、重購,另一方面卻是理論類著述長期遭遇束之高閣的命運而“滿面塵灰煙火色”。
三、亟需回歸原典閱讀的文學理論教學
雖然“在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建立以后,在中文系的學科建設中,文學史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傳統”[6],孫席珍在《怎樣研究文學》中就指出:“文學史是一切理論和批評的基礎,沒有文學史便沒有理論和批評,所以世界任何國家的大學里都把它定為初級生(Freshm an)的必修科。”[7]16因此,無論是從高校學科的設置,課時的安排,還是學生自我的興趣層面來說,文學原典閱讀都是高校文科學生爭相努力的目標。反觀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原典閱讀,長期處于冷清的狀態。長期的害怕讀、不愿讀,造成的結果就是不會讀,或者說讀不好。長此以往,文學理論教學將會更加惡性循環。如果說文學史學習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基礎,那么文學理論則是文學史的靈魂與升華。孫席珍在強調文學的重要性的同時,還明確指出“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藝批評,都應該懂得一些”[7]16。
在文學理論教學過程中,理論原典長時間保持一種對學生的閱讀生活不介入的隔離狀態,遠離了學生的知識視野,遠離了學生的接觸范圍,使其與學生之間生出了一種難以克服的“陌生化”和“阻拒性”的鴻溝。文學理論原典就在這樣的冷靜對峙中愈加成為高校文科學生更加不愿意去攀越的高峰,而文學理論也在這樣的冷靜對峙之下愈加成為高校文科學生“喜怒憂懼愛憎欲”百般糾結卻又經常“求不得”善果的一門課程。
四、文學理論教學中原典閱讀的原則
在向原典閱讀回歸時,應該注意遵守一些原則。
第一,宏觀性原則。此原則要求教師自己首先必須在熟諳古今中外各種文學理論原典,并對其進行認真廣泛的閱讀的基礎上,能夠以宏觀的眼光,指導學生對于文學理論原典的閱讀。既不將自己置于拘禁于某時期段的某一類型的文學理論原典之中,也不把自己限制在某一民族、某一國度的文學理論原典的天地,而是能夠用宏闊的眼光與胸襟,積極有效地指導、幫助學生閱讀各種理論原典,以免于局限學生的閱讀選擇與發現、思考問題的心胸和眼光。說到底,就是教學中教師能夠以自己對于理論原典的“昭昭”掌握,來確保學生對于理論原典閱讀的宏闊了解。
第二,適當性原則。雖然說,熟悉古今中外文學理論原典,對于教師與學生而言,都是重要而必要的,但并不意味著回歸原典的閱讀就必須面面俱到,不分主次、不分詳略地進行一鍋雜燴式的閱讀,而應該是有主次、有詳略、有緩急、有選擇地進行閱讀。因此,如何更好地保證理論原典的閱讀效果并進而保證學習效果,就需要教師與學生在教與學時,能夠進行溝通交流,在彼此了解各自知識基礎與儲備的基礎上,適當地選取原典要籍進行閱讀。換言之,宏觀性儲備就是為了更好地進行適當性選取。
第三,連續性原則。這一原則主要是為了保證學生的閱讀時間。可以說,文學理論原典是架構整個文理論教學的鋼筋鐵骨,而閱讀文學理論原典,讓理論原典毫無障礙地介入文學理論的教學過程,通過它能夠成功地銜接起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消減彼此對于文學理論課程的厭棄心理。但閱讀原典,既不是硬性將之塞入教師的教學過程,也不是斷續無章法地迫使學生去追逐之,至少應該盡量保證學生閱讀時間的連續性。理論原典的閱讀,需要精讀,需要細讀,需要通過對它們的反復誦讀,來把握其內核要旨,感知其文脈義理。故不能隨意分割學生對于原典閱讀的時間,而應給予其一個富有詩意的時間,避免因時間分割而致使閱讀的平面化,確保其在連續的時間之流內讀出深度,真正實現“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8],讓他們能夠由教師提取式地對概念、范疇的講解,變為借助自我的連續閱讀深潛入直觀感悟的世界。
第四,實踐性原則。文學理論來自于文學活動實踐經驗,其原典則是對這些實踐經驗從理論的高度加以概括與總結,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對它的全面閱讀、了解、掌握,能幫助解決文學理論教學當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閱讀它們就是為讓學生們在通曉經典要籍的基礎上,能夠最終養成良好的創新能力以及人文素質,將掌握的原典知識回歸于實踐,所以,閱讀理論原典是似無功利的功利性舉措,其終極目標指向仍然是學習者的實踐操控能力的培養,是經由閱讀理論性要籍而提升學習者自身素質與能力的功利之舉。因而,理論原典的閱讀,需要遵從實踐性原則,將通過理論原典閱讀所掌握知識隨時與文學閱讀實踐相結合,以之鑿實自己對于文學問題、文學現象的理解與把握,真正能夠處理和解決面對文學時的實際問題。
綜上,為了更好地破解當前文學理論教學的難題,文學理論教學就必須向文學理論原典閱讀回歸。只有回歸原典閱讀,才能夠減少學生學習理論課程時因不熟悉而生出的“初相會”般的緊張陌生感;才能夠避免學生在學習文學理論課程中只會忐忑地等待老師拋售出的那些枯燥而陌生的概念時的痛苦感;才能因對于學習對象的了解與熟悉而充滿自信,逐漸學會從全局的高度審視充滿普泛魅力的理論課程。所以回歸理論原典閱讀,是文學理論教學中當之無愧的不二選擇。只是在原典閱讀回歸中,作為“教”的教師與作為“學”者的學生,在努力提升自身的元知識累時,更應該適當掌握一些方法,遵守一些原則,既能夠有宏遠的積淀眼光與胸襟,也要有能夠學會對閱讀對象進行有目的地選擇,并能夠長時間地關注、學習之,并敢于將文學理論知識投入文學閱讀實踐,從而更好地“教學相長”、學以致用,化枯燥的灌輸為積極的吸納,變僵化的背誦為靈活的運用,盤活文學理論這局進退不得的教學“死棋”。
[1]凌建英,宗志平.“文學理論”課程的本科教學思考[J].中國大學教學,2008(6):33-34.
[2]殷學明,姜晶.《文學理論》教學中經典文本閱讀與人文素質和創新能力培養[J].牡丹江大學學報,2008(10):129.
[3]周朔.對師范院校中文系文學理論教學的思考[J].河南教育(中旬),2011(2):26.
[4]朱自清.經典常談[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3.
[5]徐緝熙.當前文藝理論教學同實踐嚴重脫節[J].文藝理論研究,1981(1):163.
[6]謝泳.從文學史到文藝學——1949年后文學教育重心的轉移及影響 [J].文藝研究,2007(9):40.
[7]華北文藝社編.怎樣研究文學[M].北平:人文書店,民國二十四年:16.
[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M].北京:中華書局,1993:3.
【責任編輯 曹 萌】